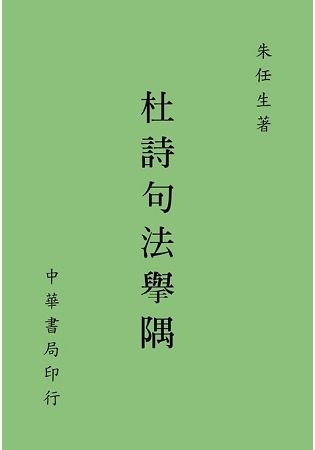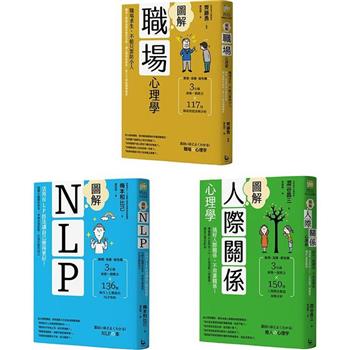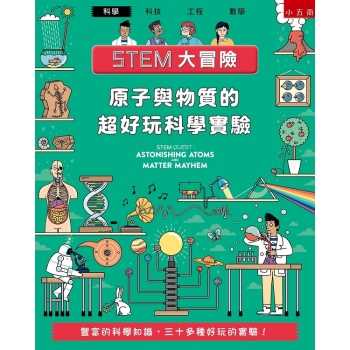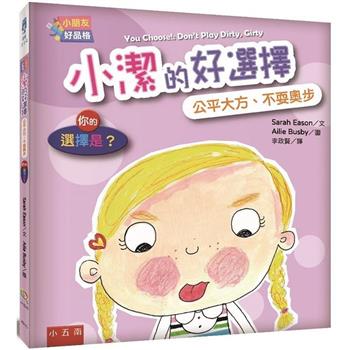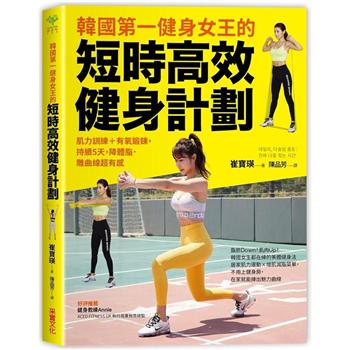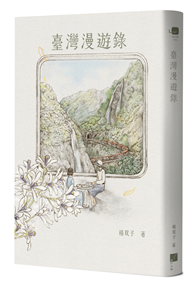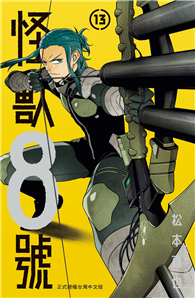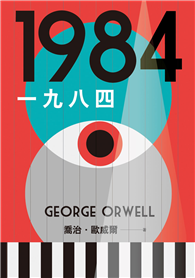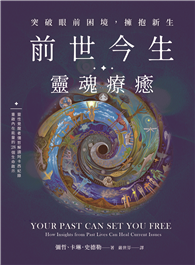(例言)
一、杜詩周情孔思,海涵地負,奄有古今之長。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故讀杜詩者,當求之於精神氣體之間,始能窺其雄奇偉壯之致,沉鬱頓挫之妙。若祇於韻味風格觀之,自無以識其深純宏遠也。
二、子美讀破萬卷,下筆有神。昔人謂子美長於學,太白長虞才,故格律森嚴,最精句法,而子美亦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今觀其集中,如「遣詞必中律。」「覓句新知律。」「晚節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詩律羣公問。」等語,足見此老對於句律之講求。是以學者,必須先探其鑄詞之精妙,而後乃識其篇章之美善也。
三、當今詩學衰微,士子科目繁多,精力分散,已不能專注於詩。是以根柢淺薄,領悟不深。講授之方,不得不先由淺易,以次漸進於探微。任生濫竽上庠,主講杜詩,略知甘苦。爰就杜公詩句,別擇分類,輯為專冊,以便諸生參證比析,進而啟導性靈,知循軌度,於初學或不無小補。
四、一篇之中,必須有警策之句,始能動人心魄。唐代以詩鳴者甚眾。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為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然縱觀各人集中,平凡處甚多,豈皆句句如是。由此可見人以詩傳,賴有佳句。蓋全篇雖善,難於悉記;而一二勝語偉詞,易於記誦,故能流傳及遠也。
五、自宋人論詩,始有「字眼」之說。所謂「眼」者,句中精要之字也。陳無己曰: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嚴滄浪曰;詩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足證古人學詩、於造句、用字之重視。杜詩對句用字,故極高妙,人所共知。及其單句用字,亦復精審邃密,而又變化多端,令人無從想象。本編所錄,於對句則摘其相似者,分類比列,以資互證,而辨其異同;於單句則擇其屢用之字,各自彙列,以便比較,而知其變化。此外尚有少數罕用之字,而極生新穩恰者,亦擇由摘錄,以資啟發。
六、鍊字之法,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以意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朴字見色。杜公用字之法,大抵如此。又詩用倒字、倒句,乃覺勁健。杜公亦偶有之。足資取法。
七、工部詩不拘一格,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事,一切物,一切意,無非詩者。是以狀景抒情,無施不善。其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為自得之言。茲分類彙錄其警句,以見一班。
八、杜詩中偶有拙句、累句,讀者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昔黃山谷謂「子美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而朱子則謂「杜甫夔以前詩佳,夔以後詩、自出規模,不可學。」又曰:「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只當意處便押一箇韻。人多說杜子美夔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戲耳。」黃與朱所見不同,學者善自別擇可也。
九、詩人玉屑所載,詩體名目繁多。如「拗句」、「借對」、「扇對」、「偷春格」、「五平五仄體」等,杜集中亦有之。惟除「拗句」外,其餘均較少見。茲分別摘出,以明體式。
十、杜公用韻,皆係常用之字。而生新穩恰,創始之處甚多。茲擇其屢用之字,分別平仄,列舉若干。其重韻而義不同者,亦附於後,以玆參證。
十一、鍾嶸詩品曰:「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於吟咏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事;「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是詩固不以用事為高也。自「顏延謝莊,尤為繁密」,篇章遂以故事相夸。工部集中,亦可概見。黃山谷曰: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又曰:「子美無意用事,真意至而事自至耳。」此誠篤論。蓋子美博極羣書,左右逢源。初非有意蒐尋故事,以炫淵博。乃至神來意至,故不覺百家諸子之言,皆為吾所用耳。陸放翁曰:「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少陵之意益遠矣。」此論甚確。學者應該深味放翁之說,而又能識少陵用事之妙,斯無差矣。茲摘錄少陵用事詩句若干則,分為四類:一曰融化。用其事而隱其語,或用其意,而易其詞,乍讀之,渾然不覺,似非用事。如水中著鹽,飲水乃之鹽味,是也。杜詩中此類語句甚多。無不鑪錘驅馬,出於自然。四曰翻用。反其意而用之,彌見新穎。此類詩句較少。
十二、東坡譏文選編次無法,去取失當。自屬確論。然集中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唐時有文選學。故老杜亦喜文選。如「熟精文選理」「續兒讀文選」是也。朱子曰:「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又曰: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由此可知老杜得力於文選者不少。故亦勉其子須精選理也。士子學詩,非博覽無以廣其趣,非專攻無以致其詞,而於文選,尤應加之意焉。
十三、唐宋以來,評論杜詩之作,更僕難數。茲擇其與本編各類有關者,摘錄於各該類之後,以便參考。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杜詩句法舉隅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75 |
總論 |
$ 450 |
總論 |
$ 450 |
中國古典文學 |
$ 450 |
中國古典文學 |
$ 45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杜詩句法舉隅
唐詩人(詩聖)杜甫用韻,皆是常用字,卻能字字妙用,甚至創出新意,黃山谷曰:「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使人讀來不感到生澀,即刻能心領神會,又覺得精切。較之漢魏多所瑰麗奇文,倍覺樸實珍貴。本書作者以其多年於大學院校教授之經驗,從杜公詩作中擇其具代表性詩句,分門別類為「鍊字、遣詞、押韻、用事」四大篇章,希望有志學詩者能從中獲得啟發,參得作詩之精髓。
本書特色
本書作者以其多年於大學院校教授之經驗,從杜公詩作中擇其具代表性詩句,分門別類為「鍊字、遣詞、押韻、用事」四大篇章,希望有志學詩者能從中獲得啟發,參得作詩之精髓。
作者簡介:
朱任生,1905年生。曾任國立安徽大學、臺灣東吳大學、私立輔仁大學等校教授。著有《古文法纂要》、《詩論分類纂要》、《姚曾論文精要類征》、《杜詩句法舉隅》(中華書局出版),並有詩詞集《虛白室詩集》,收錄五十餘年間所創之詩作。
TOP
章節試閱
(例言)
一、杜詩周情孔思,海涵地負,奄有古今之長。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故讀杜詩者,當求之於精神氣體之間,始能窺其雄奇偉壯之致,沉鬱頓挫之妙。若祇於韻味風格觀之,自無以識其深純宏遠也。
二、子美讀破萬卷,下筆有神。昔人謂子美長於學,太白長虞才,故格律森嚴,最精句法,而子美亦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今觀其集中,如「遣詞必中律。」「覓句新知律。」「晚節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詩律羣公問。」等語,足見此老對於句律之講求。是以學者,必須先探其鑄詞之精...
一、杜詩周情孔思,海涵地負,奄有古今之長。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故讀杜詩者,當求之於精神氣體之間,始能窺其雄奇偉壯之致,沉鬱頓挫之妙。若祇於韻味風格觀之,自無以識其深純宏遠也。
二、子美讀破萬卷,下筆有神。昔人謂子美長於學,太白長虞才,故格律森嚴,最精句法,而子美亦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今觀其集中,如「遣詞必中律。」「覓句新知律。」「晚節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詩律羣公問。」等語,足見此老對於句律之講求。是以學者,必須先探其鑄詞之精...
»看全部
TOP
目錄
壹、鍊字
一、字眼範例
二、實字相對
三、活字相對
四、疊字
五、顏色字
六、屢用字
貳、遣詞
一、類別
抒情語
狀情語
比類語
含蓄語
偉麗語
靜逸語
邊塞語
虛字語(以上繫對句)
發端語
收結語
論詩語
忠愛語
經濟語
勗勉語
二、體式
拗句
倒裝句
假借句
當對句
扇對
實字活用
五平五仄
實裝句
三折句
偷春格
附錄重句
參、押韻
一、平韻
二、仄韻
三、重韻
肆、用事
一、融化
二、精切
三、代敘
四、翻用
一、字眼範例
二、實字相對
三、活字相對
四、疊字
五、顏色字
六、屢用字
貳、遣詞
一、類別
抒情語
狀情語
比類語
含蓄語
偉麗語
靜逸語
邊塞語
虛字語(以上繫對句)
發端語
收結語
論詩語
忠愛語
經濟語
勗勉語
二、體式
拗句
倒裝句
假借句
當對句
扇對
實字活用
五平五仄
實裝句
三折句
偷春格
附錄重句
參、押韻
一、平韻
二、仄韻
三、重韻
肆、用事
一、融化
二、精切
三、代敘
四、翻用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朱任生著
- 出版社: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10-29 ISBN/ISSN:978957859550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28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