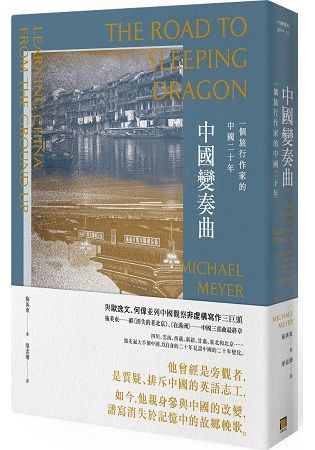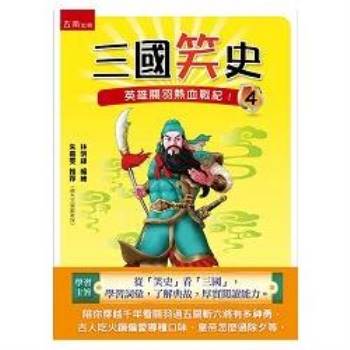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誰能夠同時為西方和中國讀者解讀中國?」
――林語堂(《吾國與吾民》作者、中國著名學者、翻譯家)
◎梅英東的非虛構寫作與「中國三部曲」
說起外國記者的「中國觀察」,何偉(Peter Hessler)、歐逸文(Evan Osnos)與梅英東向來並稱非虛構寫作的三巨頭。何偉用腳行遍中國,講述中國不為人知的真實面;歐逸文眼明手利,寫進中國政治面的最深處;而梅英東相較之下倒像閒雲野鶴,他的書中即便提及北京雲深不知處的秘辛,卻是點到為止,留給讀者相當多的想像空間;最重要的是,梅英東將生命最精華的二十年投入中國、成為中國女婿,以自身的二十年觀察中國的二十年變化。
從首善之都的拆遷老屋談中國快速發展與文化保留的取捨命題,寫出《消失的老北京》;接著以《在滿洲》雙線並陳妻子家族的東北農村生活以及更廣闊的近代滿洲史,交揉討論農村轉型與土地人情的關係;梅英東在「中國三部曲」最終章要談的,表面是回憶自身的二十年中國體驗,實際上則是對比變遷速度過大的中國現況,帶領讀者重新認識改變之前的中國。
◎長達二十年的震撼教育──重新認識中國
梅英東最有意思的寫作鋪陳,是用自身對中國情感的變化,來看中國二十年的「變與不變」。這是相當少見的題材,也因此,本書除了記者報導的非虛構寫作,同時也融入了梅英東的類自傳回憶錄:正因為他的教書生涯、結婚與生子、與妻家家族的生活都與中國土地息息相關。
1995年,梅英東在二十三歲時加入和平工作團,在拒絕去其他七個國家的提議後,被送到了四川內江。他對中國一無所知,有的只有短期教育訓練的漢語學習,他不會用筷子,也不太能說中文,為此他在手背上寫下中文單詞,以方便進行對話、點餐(尤其水土不服――又辣又怪的食物讓他吃盡苦頭)。這是他與中國第一次的文化接觸。令人莞爾的是,梅英東坦承初入中國是帶著質疑、排斥的心理,然而在他面對四川偏鄉的鄰人、旅程中遇到的小人物,乃至於東北的妻子家族,體會到人情與文化的衝突、理解之後,他終於敞開心房,正視所謂的「改變中的中國」。
◎記錄中國的變與不變,書寫消失中的故鄉輓歌
這個命題貫穿全書,當然,梅英東最有巧思的安排正是透過交通工具的使用,來傳達這個概念。他在中國的初登場是在四川內江的巴士上,語言不通的他險被襲擊,最後是他以為冷漠的中國人救了他,留下「襲擊者是彝族、不是我們中國人」的震撼教育,這是文化層面的陌生衝擊。最後以一班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西伯利亞列車來暗喻中國與人民的前途:列車長認為這是一班無限循環的旅途;蒙古女人拋下南方的工作、回到蒙古老家靜待母親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也因此這班列車並非開往未來、而是回到不忍卒睹的過去;南方溫洲的小姑娘連莫斯科在哪都不曉得、卻傻裡傻氣就跳上列車要去當裁縫工,她說只要上了車、就能通往未來……
中國的變與不變,不只是驗證在梅英東旅途中所見的長江三峽的今昔變遷、川震後物是人非、北京老胡同的消失、臥龍生態區的過度開發……最根本的,是從小人物在變化快速的中國,觀察他們如何安身立命、知道自己該如何適應這樣的變與不變。
這二十年對中國來說,變化有多大?對梅英東的人生又有怎樣的改變?最特別的一個改變,或許可以舉以下這個例子來說明:梅英東曾經見到《孤獨星球》的一期封面,那是中國男性長者的臉孔,「要是在以前,我可能會描述那男人為『乾癟削瘦』或甚至『冷淡』,但現在我注意到他飽經風霜的臉、長滿繭的雙手,和磨得到處是洞、被太陽曬得褪色的襯衫。他可以是我們任何一位學生那工作辛勞勤勉的農夫父親。」
中國正在改變,從最初的志工身分進入,梅英東以二十年認識中國、理解中國,他以四川、雲南、西藏、新疆、甘肅、東北和北京為背景,歷經時間沉澱而汲取教訓,本書不僅是他記錄人生不同階段的回憶錄,同時也是關照中國在急遽改變之後,還能回頭省思得與失的箴言錄。
「只要你願意去參與中國,你將會看見許多美麗之處。」
――賽珍珠(《大地》作者、諾貝爾文學獎、普立茲小說獎得主)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中國變奏曲:一個旅行作家的中國二十年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0 |
二手中文書 |
$ 363 |
中國觀察 |
$ 391 |
旅遊 |
$ 404 |
中文書 |
$ 414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中國變奏曲:一個旅行作家的中國二十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梅英東(Michael Meyer)
美國旅行作家,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現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1995年,他作為美國和平團志工來到中國四川內江,1997年之後在北京生活了十年,2007遠赴倫敦寫作,2009年重返北京,並陸續完成《消失的老北京:陪著老北京走過最後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在滿洲: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In Manchuria)等書。
文章散見《紐約時報》、《時代週刊》、《金融時報》、《體育畫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及其他報刊。曾獲得多項寫作獎肯定,包括古根漢獎(Guggenheim Fellowship)、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獎(New York Public Library)、懷亭獎(Whiting Writers’ Award)、洛克菲勒獎(Rockefeller Bellagio)、洛威爾湯瑪士獎(Lowell Thomas Award)、國家人文社會科學基金獎(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Public Scholar award)等。
作者網站: www.roadtosleepingdragon.com
譯者簡介
廖素珊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雙子城校區比較文學研究所肄業。現專事翻譯,譯作有《廣島末班列車:一九四五原爆生還者的真實故事》、《冰與火之歌:群鴉盛宴》、《縱走日本二千哩》、《咆哮山莊》等近四十部。
梅英東(Michael Meyer)
美國旅行作家,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現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1995年,他作為美國和平團志工來到中國四川內江,1997年之後在北京生活了十年,2007遠赴倫敦寫作,2009年重返北京,並陸續完成《消失的老北京:陪著老北京走過最後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在滿洲: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In Manchuria)等書。
文章散見《紐約時報》、《時代週刊》、《金融時報》、《體育畫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及其他報刊。曾獲得多項寫作獎肯定,包括古根漢獎(Guggenheim Fellowship)、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獎(New York Public Library)、懷亭獎(Whiting Writers’ Award)、洛克菲勒獎(Rockefeller Bellagio)、洛威爾湯瑪士獎(Lowell Thomas Award)、國家人文社會科學基金獎(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Public Scholar award)等。
作者網站: www.roadtosleepingdragon.com
譯者簡介
廖素珊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雙子城校區比較文學研究所肄業。現專事翻譯,譯作有《廣島末班列車:一九四五原爆生還者的真實故事》、《冰與火之歌:群鴉盛宴》、《縱走日本二千哩》、《咆哮山莊》等近四十部。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