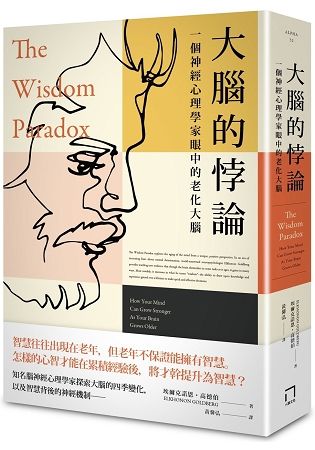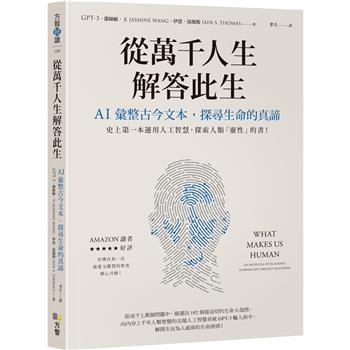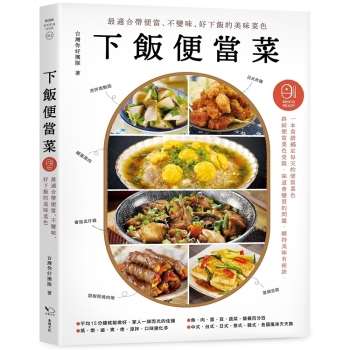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
對「大腦的悖論」的讚揚:
「印象深刻……相當廣博的探討……《大腦的悖論》收集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證明即便進入晚年,還是有可能維持敏銳的心智能力。」
──肯尼斯.西爾巴(Kenneth Silber),《美國科學人雜誌》心智版
「大好消息!我們的大腦能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好!高德伯博士所提出的證據簡單明瞭,且毫無爭議…相當具有知識性且讀來興味十足的書。」
──黛安.史圖特(Diane Stressing),《誠懇家日報》(The Plain Dealer),克里夫蘭
「以一本充滿眾多與大腦相關資訊和想法的書而言,大腦的悖論非常深入淺出,令人享受閱讀的過程。高德伯博士是一個化繁為簡的天才,也是一位才華洋溢的作家。」 ──《大腦》
推 薦
「這本書運用發育神經心理學、腦細胞定位與電腦科學等領域最新的研究結果,優雅地解釋了大腦老化……高德伯博士翻轉了我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具有不同功能,以及前額葉功能的錯誤假設…在這個大力歌頌青春的年代,很開心地能有一本書提醒我們,雖然年華老去,但我們還是在智識上,有所成長。」──愛瑪・克里頓─米勒(Emma Crichton-Miller),《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倫敦
「書中提到當我們步入晚年,不全然都是處於失去的狀態,智慧便是我們最重要的收穫。這是年歲漸長最寶貴的附加價值。」──安東尼奧.達馬西奧,《笛卡兒的錯誤:情緒、推理與人腦》(De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的作者
作者簡介:
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
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是《大腦總指揮:一位神經科學家的大腦之旅》(Executive Brain)、《大腦新的總指揮》(The New Executive Brain)以及《創造力》《Creativity》等書作者,同時也是紐約大學醫學院的神經科臨床教授。目前他也以神經心理學家的身分自行開業,而且是認知神經心理學領域相當活躍的研究者。
個人網站:http://www.elkhonongoldberg.com/
譯者簡介:
黃馨弘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現於生醫新創公司任職。
章節試閱
前 言
身為一個認知神經科學家,我已經很習慣在實驗室冷靜地討論與大腦相關的抽象概念;身為一個臨床神經心理學家,我的專業訓練,讓我對腦功能障礙或腦傷的跡象高度警覺。不過,這樣的敏銳,只適用於﹁別人﹂的腦損傷,當換成自己接受核磁共振檢查時,我不斷痛苦盤算著自己腦中各種可能狀況。想到還要等待檢查結果出爐,我不禁感到害怕。
這麼自相矛盾的人,可不只我而已。我和許多朋友聊過—都是一些世界級的神經科學家、神經學家與精神科醫師—他們也都承認,他們對自己脖子以上的部位是否健康,都不感到好奇。對於自己大腦的狀況,他們可是一點也不感興趣。這種﹁與我無關﹂的態度,總會伴隨著一聲神經兮兮的訕笑,但我卻能理解他們的想法。
對我而言,不確定性令人感到焦慮;而試著釐清事實,不管最終結果為何,則至少能讓人做好心理準備。過去我的好友和死敵們,直言不諱地用了許多動物學上的用語來形容我的性格,可從來沒有人說我是一個抱持鴕鳥心態的人。我為自己遇到困難總是勇於迎「頭」面對的個性感到驕傲;而此刻,我也勇於一「頭」栽進腦部掃描儀的磁圈當中。一開始,我找了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Jim Hughes)
,希望他能幫我開個核磁共振轉診單。但他嘲笑我的這個點子,試著說服我別去做腦部掃描。
「萬一發現良性腦瘤怎麼辦?」吉姆說,「你接下來的人生會受盡折磨的。」他提到美國神經外科之父哈維.庫興(Harvey Cushing)的例子,他就長了良性腦瘤。
我天真地回應說,我覺得自己夠堅強,可以理性面對任何結果。而且,瞭解總是比一無所知更好。
「如果這樣,萬一我們在你的腦子裡發現不好的東西,」吉姆生氣地說,「那會換成我非常自責!」
在一番激辯後,我們都認為為了滿足我那病態的好奇心,讓吉姆感到自責似乎是可接受的風險。吉姆已默然表示同意。
身為一個臨床神經心理學家及認知神經科學家,過去三十五年來,我研究了各種人類大腦損傷會對人類心智造成的影響,也看過、分析過數以百計的腦部電腦斷層掃描和核磁共振影像。但儘管這麼說,這卻將是我此生第一次見到自己大腦的影像。我比一般人都更知道,再輕微的腦傷,都能對一個人的心智甚至靈魂,造成極大的破壞。但在正式檢查前的最後評估階段,我對吉姆說的句句都是真心話。我真的相信,即便最後的結果很糟,我還是能夠承受任何消息,而且無論如何,知道總比無知好。於是就在
一個陽光普照的四月天,我走進曼哈頓中城區的哥倫布圓環核磁共振影像中心。
幾天後,檢查報告和影像檔案送到我手上了(一般不會把影像檔案交給患者,但畢竟我是同事)。這影像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可怕之處,但也沒有什麼特別令人開心之處。放射師認為,我的大腦皮質溝(位於大腦表面,如同胡桃殼上的皺褶)和腦室(大腦中的空腔,裡頭充滿包圍大腦的腦脊髓液)大小皆正常。就我自己看來,腦溝的確完全沒有異狀。但即便年長者的腦室本來就會稍微擴張,我的腦室看起來還是稍微偏大。這表示我的大腦可能有些微萎縮。
另外,影像報告中也提到,在我的左大腦半球白質(當較長的神經通路連結大腦遠端區塊,並圍成名為「髓鞘」、富含脂肪的白色組織,此稱作白質)中有兩個小區塊發出較高的訊號強度。我有注意到這個部分。這種影像上的訊號所代表的意義不明,就我的狀況來說,它們最有可能表示我大腦中有局部缺血病變,也就是一部分的腦組織已因缺氧而壞死。不然就是我大腦中有某個區塊的髓鞘消失了。依據我個人的見解,這表示我有輕微的腦部損傷。
影像報告的其他內容並不全都是壞消息。我的內頸動脈與基底動脈的腦血流正常流動,磁振造影擴散影像也沒有異常。這表示我的主要動脈都非常乾淨、沒有阻塞,也沒有脂肪碎塊堵在裡頭,我的血管都相當健壯。這個結果跟幾個月前做的頸動脈超音波檢查結果相符。我的血壓雖略為偏高,但大致上還算正常,感謝上天,這表示我突然嚴重中風或是動脈瘤破裂的機率極低。我的海馬迴(腦中海馬形狀的結構,對人的記憶至關重要)大小正常,這相當令人高興。因為海馬迴的萎縮,往往是阿茲海默症的前兆。
為了讓自己不要再對檢查結果緊張兮兮,我決定拜訪著名的紐約長老教會醫院( 這裡正好是我第一次到美國時,以學者身分工作的地方 ) 的約翰.卡若南(John Caronna)醫師,他同時也是紐約最頂尖的神經學家。卡若南醫師對人親切熱情,他仔細為我做了身體檢查,也看了我的腦部影像,還將這些影像交給他的同事—康乃爾大學威爾醫學院的神經放射部主任過目。他們兩位都認為,考量到我的年紀,就算有兩個疑似缺血的小點區域,也是非常正常的。
「看起來是顆有被妥善使用的大腦,如此而已。」卡若南醫師用他那極具特色又迷人的幽默口吻說。
但畢竟我看過了數以百計的腦部掃描影像,我還是覺得我的腦室比同齡的人要來的大,而那兩個在影像上很明顯、可能表示缺血的小點,也並非必然跟年紀大有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把我的腦部掃描拿給我的老友山福德.安庭(Sanford Antin)醫師看。山迪是紐約最有經驗的神經放射學家之一,在我的科學生涯中,我們合作了不少具開創性的專案。
山迪看著我的核磁共振影像,立刻認定其中一個點狀物只是假影、不必予以理會,並且很有信心又詳盡地向我解釋假影是如何產生的。然後他說,另一個點狀物也沒有顯著意義,從而認定我的腦溝和腦迴,以各種年齡層的標準來說都非常正常,還誇我有顆「美麗的大腦」。
於是,我終於放下內心的擔憂。回想起來,這次腦部掃描事件可用兩個有趣的角度觀察:神經系統的角度與神經官能的角度。以神經學和神經心理學的角度來講,一般人是否也該在到達某個年齡之後把我所做的檢查列為例行健檢的一部分?這值得討論。也許不需要每年做,但每三到五年可以做一次。預防性的檢查越來越重要,畢竟隨著年歲增長,面對苦痛我們越發脆弱。因為如此,在全球醫療機構的大力推動下,大腸鏡成為對抗大腸癌的一種手段。乳癌篩檢、攝護腺篩檢也都有類似意涵。然而,我們很少為大腦做預防性檢查,彷彿大腦不是人體的一部分一樣。這極沒道理,因為在老年人口裡,失智的發生率往往與其他疾病不相上下,甚至高於其他疾病。
心智、大腦以及身體
這種毫無邏輯又令人感到不幸的態度,大概來自兩個未經證實的假設:一個來自一般大眾,一個來自醫療專家。直到近代,很多人都還不認為心智是人類生理的一部分,這受到醫學和準醫學所能檢驗的範圍所限。這觀念當然並不正確,這是笛卡爾心物二元論的延伸。今日,接受過全民普通教育的大眾越來越多,人們已經具備心智是大腦的一部分、同時也就是身體的一部分的觀念。而這個觀念,將會是本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至於醫療專家,則往往質疑這些能提早診斷出失智的方法。畢竟目前還沒有失智症的治療對策,即便提早診斷出來也於事無補。套句軍事術語來說,這一類的資訊「無助於行動」,等同於沒用,它們只會讓病人感到難過而已。沒有治療對策的診斷結果,僅會為社會帶來更多財務負擔。但這個十年前還準確而令人悲傷的、不言而明之假設,轉眼間已經過時了。各種保護大腦免於老化的藥物或非藥物性治療,如雨後春筍般竄出。簡單來講,說失智症「無藥可救」的假設,已不再屬實。
雖然道理是這麼說,但我發現我的反應還是不免神經兮兮。我很確定和我同年紀的人不管有多開明,對於年歲漸增都感到神經緊張(也許越開明的越緊張),而且每個人表現緊張的方式還都不太一樣。身為一個神經科學家,我的反應是立即預約一個腦部核磁共振掃描;而其他人面對上了年紀後的精神官能症則有不同做法。一般人會拼命否認,更精確地說,是拒絕瞭解,我也親眼在一些同事身上看到這樣的狀況。
這次的經驗讓我開始認真思索,在現代社會中,當一個人的腦袋承載著一個衰老的心靈時,命運會如何。和大多數生命體或大自然中的事物一樣,大腦的健康和失能狀態,並非總是涇渭分明。其中有著極大的「灰」色地帶──即便大腦「灰」質也是有灰色地帶的!
「戰後嬰兒潮」這個字眼雖然源自美國,卻是一個全球性現象。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十年間,如同北美一樣,歐洲與蘇聯的出生率迅速飆升。如今整個社會都在關注「阿茲海默症」的流行,我和數以百萬計同年齡層的人,感受到一樣的焦慮。當中有很多人,也許幾乎是所有人,都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只是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而這些焦慮究竟有哪些只是過度緊張,哪些卻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呢?一部分是現實,一部分是過度緊張。當人在步入中年後期時,開始擔憂個人的精神官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預見的。對我來說,這樣的狀態是豐富多彩的,不管是好還是壞。畢竟以我的專業知識,我知道大腦如何正常運作,也瞭解大腦無法正常運作的各種狀況。我和同年齡層的人不同,我身為腦科學家和臨床人員,靠著診斷和治療各種腦損傷帶來的影響為生,每天都在面對衰老的心靈和處理失智症。若我能探究自己對於老年的焦慮,肯定能幫助許多人。我希望,像我這樣一個漸入晚年的神經科學家所進行的反思,能為各種各樣與我同齡的人帶來助益。當我們年輕時,我們被無名的欲望驅使向前,我們什麼都不怕。然而,正如俗諺說的:當我們老邁,我們只想安穩過日。所謂的「安穩」,是否只是一種停滯不前?所有與老化相關的心智變化都是不好的嗎,或是其實也有些好處? 在我持續探索自己的心智狀態後,我認為老化對我而言,除了焦慮和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外,其實沒什麼壞處。我注意到一件讓我很滿意的事:比起三十年前的我,我現在就算單靠直覺,也不太會做出什麼荒唐蠢事。我的思緒非常清楚,某些時候運作得甚至比以前更好。多數人年老的時候,想法會變得保守,而我卻總是不斷讓自己更勇於向前。我在心中向「停滯不前」發起一次又一次的攻擊。太過安穩的生活,跟死了有何不同?我一點都不想要那樣的生活。
在這段自我追尋的過程中,我感到最可惜的,便是我無法將這些心智上的改變量化後做比較。例如總體來說,我目前的心智狀態比起十年前,雖不能說變得較脆弱,但也不能說變得更強大。我只知道,我的心智和以前有所不同。過去面對問題時,我總是抽絲剝繭地一一擊破,現在則是試著找出其中相似的模式。現在的我,早已對於那些孜孜矻矻、勞心勞力的算計不在行,卻也不像以前那麼需要這些能力。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對於自己感到得意,因為我不需要任何筆記,就能聽懂一堂神祕難解的進階數學課,而且還通過幾個月後的考試。但我現在五十七歲了,步入中年已久,我一點都不想再試一次!這太難了!
然而隨著年紀變大,也有許多事情變得比過去簡單。現在的我能輕鬆迸出許多以前想不到的好點子。常常在面對一個乍看之下相當具挑戰性的難題時,突然就像有魔法般,將那些傷腦筋的過程毫不費力地略過了。問題的解答來的毫不費力、不著痕跡,就像難題自行解決了一樣。我年歲漸增,無法再像年輕人一樣絞盡腦汁,但卻換得一種反應快速且毫不費心思的判斷力。
除此之外,我還發現一件有趣的事。當我解決棘手問題時,天外總是會飛來神奇的一筆。一開始靈感看起來好像與手上問題毫無關連,但到最後往往會對其提供非常精妙的解答。過去認為彼此間沒有連結的事物,其相關性現在逐漸浮現,而且一樣是得來不費吹灰之力。比起過去需要主動積極督促我的心智,現在的我,就像風車主人一樣,只要被動地享受成果就好。我以前在專業領域上得非常辛苦才能有所突破,但現在﹁靈光一現﹂越來越常出現,不但讓我更有生產力,也對研究工作更感到心滿意足。就像孩子找到一個隱藏的餅乾盒一樣開心,還不用遭來處罰。
除此之外,還有更好且好到讓我不敢相信的事,那就是:我終於覺得更能掌握自己的人生。雖然聽來像是輕度狂躁症發作(我沒有,所以敢這麼說),但我的確越來越覺得人生像是場盛大饗宴,不再像過去老是覺得人生充滿痛苦掙扎。我明白盛宴終有結束的一天,但也許正因為知道結束無可避免,隨著年齡增長,我就有益發強烈的衝動,不自主地想要延長這場宴會。這正是步入熟年的自我矛盾:既折服於歲月帶來的改變,卻還是忍不住想要繼續人生這場狂歡。因為生命,並非是一路朝向衰亡的單行道。生命中有許多順流與逆流,需要去經歷、去檢視、去理解以及去享受。
那為什麼我的心智能力突然增強,問題的答案就這麼即時且毫不費力地出現呢?有沒有可能,也要歸因於歲月的副產品:智慧呢?一開始,我很怕就這麼糊里糊塗地被帶進了「智慧」的迷思中,但後來證明這根本就是愚笨之舉。我想要盡可能用相對樸素、而且已經被我用了一輩子的科學用語:「模式識別」,取代「智慧」這個帶有詩意且過於貴重的說法。
然而,即便我已經非常小心地,不去使用任何過於浮誇的用語,我發現我還是用了「智慧」這個字眼,甚至造了個新的詞:智慧悖論(wisdom paradox),用來泛指因為年歲增長,所產生的自相矛盾。我們的心智,是大腦這自然界生物所擁有的器官的產出。雖然大腦會衰老與改變,但每一階段的改變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樂趣、好處、損失以及權衡,如同自然界的四季更迭。年輕的時候,如果我們用探索世界與好奇心埋下了心智的種子,隨之而來的人生經歷將會持續澆灌著這棵作物。等到如同法蘭克.辛納屈在名曲﹁美好的一年﹂中所唱的秋天來臨時,我們就能豐收名為「智慧」的成果。經過一番思考後,我決定投入新的計畫,也就是您手上的這本書。這本書將介紹人類心智宛如四季,從血氣方剛到充滿智慧的歷程。就當我正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深深感到「智慧」在認知層面、道德層面所指涉的維度都過於廣大,以致於我一個人是無法憑藉單一觀點完整說明的。所以我限制了本書的討論範圍,僅止於智慧的認知層面—一個儘管狹隘了點,卻非常值得討論的領域。
第三章
當歷史上的偉大心靈邁入晚年
大器晚成的人才
人類,是極少數平均年齡會遠超過生育年齡的生物。為什麼演化的設計(請原諒各種擬人化與目的論的用詞)在即便個體已無法對於繁衍有任何貢獻後,還要繼續延長個體的壽命?是什麼樣的演化壓力造成如此奇怪的現象?目前學界給出的一個可能解釋是,較年長的個體用其他不同的方式,對於物種的存活做出極關鍵的貢獻。年長個體能夠積累知識,並透過語言等方式將文化傳承給後代。以學者來說這並不難理解,但普羅大眾卻常忽視長者在傳承上的貢獻。
在我們的文化中,精力旺盛往往意味著年輕,而精神力下降則意味著衰老。然而,長者潛在的創造力往往被人忽視。我朋友十九歲的兒子喬安,受到社會普遍觀點的影響,會帶點歧視長者意味地說:「我很訝異像你和我爸這年紀的人,還能一直學習新東西!」當時他的父親已是全歐洲最受人矚目的創新者,也是重點大學的領頭人物和總統候選人。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他甚至是北歐國家的國會中最受注目的人。但這樣的成就也全然沒讓這位年輕人感到印象深刻啊。
今日,喬安這種略為鄙視長者的想法,已受到無數像他父親或父親的朋友(比方說我)等年紀雖長卻依然成功且富有創意的人所挑戰,也許本書大多數讀者也會不那麼同意他的想法。這實在非常顯而易見而廣泛地被人接受,且有許多例子都能支持我的論點,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我將稍微重新整理相關案例,再次揭露這個令人震驚但可能簡單到有點汙辱讀者智商的事實。我會提到兩個較少有人關注的點,加強前幾章所提到的論點。
我想說的第一點是:人的心智不但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很活躍,更可能到年紀大時才變得特別活躍。我稱這樣的人為大器晚成類型。歷史上有太多極富創造力和政治領導力的例子,都是直到六、七十歲甚至八十歲才達到巔峰的。這些偉大的個體都在他們晚年時期才到達人生的巔峰而享有盛名。文學界、建築界、繪畫界、科學界及政治界,都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以下舉的六個例子,將挑戰一般文化中認為年老等同退化這個根深蒂固的概念。
偉大的德國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顯然是文學界一個「越陳越香」的例子。他在五十九歲時出版了浮士德的第一部曲,八十三歲時又出版了第二部曲。歌德的作家生涯極為多產,更別提他晚年的巨作《浮士德》,幾世紀以來都與他齊名。世界知名且極具遠見的加泰隆尼亞建築師高第(Antoni Gaudí, 1852∼1926)也有類似的人生經歷。他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在巴塞隆納建造聖家堂這棟在西方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築物。直到過世的前一刻,他都還專注地在建造聖家堂。七十四歲的高第,創造力正處於巔峰之際,不幸因車禍而逝世,令得聖家堂至今仍未完工。美國也有類似例子。世人稱為摩西奶奶的安娜.瑪麗.羅伯森(Anna MaryRobertson, 1860∼1961)七十歲才開始作畫。一直到八十歲,她對鄉村農耕的描繪才開始受到世人注意。直到逝世之前,摩西奶奶都不斷作畫,直到今天她被視為美國最重要的民俗畫家。
除了人文領域,其他領域也有許多晚年有成的例子。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 1894∼1964)曾說:「數學僅僅是年輕人的遊戲。」但他自己打破了這個說法。維納是模控學之父,他提出假說,認為有個複雜的構造存在於所有生物與人造體系中,那構造能整合成一個系統,而這形塑了現代科學的許多基礎。維納同時是數學家和哲學家,他在五十四歲時出版了控制論;七十歲出版了他的第二重要著作《上帝與魔像股份公司》(God and Golem, Inc.)。今日科學界用於處理複雜系統的通則,即所謂的「複雜度研究」,都是出自維納的洞見,而這許多都是在他晚年時期才產生的。
晚年才登上政治舞台顛峰的例子也不勝枚舉。果爾達.梅爾夫人(Golda Meir, 1898∼1978)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期間內擔任以色列總理,多次領導她的國家度過重重危機。她首次擔任以色列總理已經七十一歲,比溫斯頓.邱吉爾開始他的第一任首相任期的六十五歲、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開始第一任總統任期的六十九歲還晚。梅爾夫人離世前,被認定為以色列之母。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2013),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於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擔任南非第一任民選總統。曼德拉七十六歲才出任總統,即便被監禁了二十八年,他還是保有清楚的想法與堅強的意志。曼德拉為他的國家在各方面形塑了新樣貌,直到本書撰寫之際,他都還是自由南非的象徵。
有些人可能會說,此處所舉的六個在晚年還能有創新成就、登上巔峰的人物,他們不過是因為幸運地擁有好基因,才能夠在晚年都還維持心智上的敏銳。但令人振奮的是,無獨有偶地,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至此,我們已經可以進到我的下一個,起初有點出人意料的論點。
我想說的第二點,失去部分的認知能力,並非認知能力的終結。一個失去部分認知能力的人,即便被測出有認知功能下降情形,甚至有早期失智症狀,還是能在重要事情上具備足夠的生產力,或是在認知方面具備競爭力。我稱這樣的人為遭受侵蝕卻依然強大的心靈。人們在失智初期還能對社會、文化和政治做出重要貢獻,這想法一開始聽起來很不尋常,但仔細思想歷史事件後,就會感到震驚。根據文獻記載,某些最重要的政治決策(可能具建設性,也可能具破壞性)或是偉大的藝術創作,都是由飽受老化時的神經症狀所苦、甚至已有早期失智症狀的長者所做出的。這樣的狀況不只存在政治和藝術領域,哲學界與科學界也有類似狀況。
有趣的是,人類歷史和文化是由許多神經認知功能處於不同退化階段、甚至經歷早期失智的人所形塑。如果僅注意他們心智上的衰退,就會忽視更有趣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彌補了他們心智上的退化,他們心智上的能力和效率能保留下來,如此形塑了這世界的政治和文化?這個彌補機制,其實源自大腦內大量的模式辨識庫,而這些模式早在數十年前就已陸續形成。
根據詞源學,Dementia這個字的原意是「喪失心智」,這是一個相當殘忍而幾無仁慈的毀滅性字眼,它暗示了某種程度的、蠻嚴重的心智喪失。心智喪失有它特定的意涵,因此我們必須減少這個字眼的使用。現實中,所有失智的進展速度都非常緩慢,心智下降大都需要花上幾年的時間,有時候要個十年十五年,特殊狀況甚至會花上更長時間。失智者的心智能力不會一夕之間就從完全清醒驟降到全然消失,差得遠了。失智也不會轉瞬就影響患者所有的心智能力。大多數患者經歷的失智過程,一開始只有少數功能受影響,然後在接下來幾年的時間當中,其他功能才陸續受影響。失智症狀最終會擴散到各個功能上。在發病前期,患者對於自身的控制力還很高,而且能夠進行各種複雜的活動。疾病前一、兩年,患者甚至能進行仰賴高智能的活動。雖然患者有可能在罹病初期就面臨心智能力的急速下降,且大多數患者將無法避免地出現失智症狀,但失智患者往往不會在幾年內就完全失智。另外,也並非所有的輕微認知缺損,都會發展成失智,因此心智退化與全面演變為失智,兩者還是非常不同。內科醫師與心理學家們長久以來已對這個過程有所瞭解,失智症不同階段的心智變化也已被詳細描述。
之前我曾強調,大腦具備了辨識各種模式的機制,而這樣的機制能夠在長久時間內有效地對抗心智退化。在接下來的第四章中,我們將討論大腦中的這種保護機制是如何發生的,但在此我們先再次檢視這現象。聽來雖然矛盾,但透過以下敘述我們便能理解,老化所造成的心智退化和強大的認知功能,是可以共存的。
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將討論於晚年時期在歷史與文化上留下不可抹滅事蹟(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的藝術家和政治領袖。在討論他們做出的龐大成就的同時,也會討論他們在神經學上所表現的早期失智症狀。以下我們將從兩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開始介紹起。
藝術與失智
巴斯克地區位於法國、西班牙邊境一帶,一直以來都是充滿神祕氣息之地。巴斯克語不像其他印歐語系的語言,它相當獨特,來源也不甚清楚。巴斯克人被認為是歐洲最早的居民,大約與居爾特人同期或更早一些。他們長久以來是以部落形式在歐洲大陸生活著,直到多批移民潮和征服者改變了他們的種族和語言。巴斯克地區最近更以動盪不安和不時的暴力獨立運動聞名,不過對觀光客來說這相當抽象,而該地區氣氛也還不到肅殺的程度。相反地,巴斯克的首都聖塞巴斯提安(San Sebastian)是歐洲知名的海灘渡假勝地,等同於船隻、陽光、高級餐廳與奢華享受。該區域同時也是紀念雕塑文化傳統之鄉,會讓人聯想到巴斯克偉大的傳統建築雕刻家愛德華多.奇利達(Eduardo Chillida, 1924∼2002),以及他一生的競爭對手喬治.瓦提薩(Jorge Oteiza, 位罹患重度阿茲海默症的知名雕刻家,是如何在他們的照顧下度過晚年的。原來愛德華多.奇利達晚年幾乎無行為能力,他的心智狀態因罹病而大大受到影響。
隔天我們驅車前往知名的奇利達—萊庫博物館,它是位於薩瓦拉加附近村落的知名雕塑花園,收集了全世界最多的奇利達作品。這棟廣闊的建築是一座十六世紀的穀倉,被奇利達改裝成私人住宅,周邊有美麗的庭院和上有雕塑品錯落擺放的草皮。奇利達的作品大多具紀念意義與抽象外觀。他使用金屬、大理石、石塊及木材,創造了高度抽象美感的作品,雖然規格像獨眼巨人般巨大,但卻細膩呈現了內心的情感。當我漫步在這些巨大雕像間,突然覺得這些雕像與巨石陣出奇地相似。這些作品看起來雋永,好似出自相同的靈感來源,或說承著某種靈感的脈絡走。巴斯克人和居爾特人都是歐洲早期居民的後裔,受到湧進的新住民侵略後他們便將足步轉往歐洲大陸的最西邊。有沒有可能因為他們在歷史上接觸過彼此,因而共享了部分美感上的經驗,而將巴斯克的藝術從四千年前德魯伊人的巨石陣中分離出來,使傳統的藝術能夠藉奇利達或是瓦提薩的手用現代化的方式詮釋出來?這個有趣的想法,在我漫步於雕塑花園時不斷在腦中迴盪。
著,我注意到一些雕像旁的牌子,上頭刻著十九世紀中期、晚期,甚至二○○○年等年份。目前已知阿茲海默症不是突然在某人身上發病的;相反地,它往往花上數年而非數月的時間,逐漸讓人失去心智功能。如奇利達一樣在二○○一年處於重度失智症狀態的人,可能早在九○年代晚期甚至是九○年代中期,疾病就已經開始了。在此地,我被眾多優異作品環繞1908∼2003)。
在我待在聖塞巴斯提安期間,一晚晚餐間的話題突然轉到了愛德華多.奇利達身上。那年,他才剛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不久。招待我的神經學家在地方醫學中心工作,他談論起這著—這些作品是每個策展人和博物館都迫不及待想要收藏的,而它們居然是由一個飽受阿茲海默症侵擾的患者所創作的。我跟招待我的人分享這個觀察,他們看起來跟我一樣有所疑問。
在離開該地幾個月後,我還是不斷想起一個衰老的雕刻大師,即便失去了記憶,仍然使用他的藝術創作力戰勝疾病的模樣。同個時期的北美藝術家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 1904∼1997)有著和愛德華多.奇利達的悲慘故事截然不同的經歷。德.庫寧是荷蘭人,一九二六年時他二十二歲,當時正在美國白手起家。德.庫寧是影響二十世紀美國藝術最重要的人物,他的職業生涯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之久,主要的身分是畫家,有時也是雕刻家。德.庫寧以堅持原創為特色,為繪畫界開闢了新道路。有一次他的學生問他,為什麼從不研究有名藝術家的畫作?他回答說:「在大樹遮蔽下,新東西是長不出來的。」然而後來就好像打自己臉一般地,他自己成為了所謂的「大樹」,他創立了嶄新的學派。早期他迷戀立體主義,然後風格轉換了好幾次,在創造出「安靜的男人」與「瘋狂的女人」之後,德.庫寧成為抽象表現主義的創始者。
一九七○年代晚期,德.庫寧身邊的人開始察覺到他有些微的記憶喪失。如同一般患者一樣,他記不得最近發生的事,卻對很久以前的事情記得很清楚。神經心理學家和神經學家用一個非常冗長的字眼描述這個現象:「具時間梯度的回溯性失憶」(temporal gradient of retrogradeamnesia)—當疾病益發嚴重,相對久遠的記憶也會陸續喪失。為他作傳的海登.赫雷拉(Hayden Herrera)便記錄了有一次德.庫寧甚至無法認出一位認識多年的親密老友。最終,他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
但這位年長的大師還是繼續繪畫,把他的時間全部花在畫室裡,有時一週可以畫出好幾幅作品。德.庫寧八十一歲時甚至諷刺地說:「完成一幅畫,就像是我明天最不該做的事。」(他的記憶雖然受到破壞,但他的智慧卻沒有消失)。
德.庫寧的作品持續進化到他生涯的最後一刻。一九八○年代他作畫的手法持續拓展,他的朋友暨他的傳記主筆愛德華.萊伯(Edvard Lieber)就說,德.庫寧在一九八○年代晚期開始進入「超活躍形式」:作品簡約、顏色明亮、線條流暢如波。德.庫寧在安然進入八十歲時,注意到自己的變化。他說:「我的調色盤裡有各種顏色,只是全都走了色調。以前,我要不斷去瞭解我不知道的事情;現在,我則漸漸不記得過去記得的事。」這樣的改變不僅僅是畫作風格的改變。對德.庫寧來說,繪畫永遠是能更深入瞭解各種事物及自身經驗的一種方式,而並非只是試圖模仿各種風格。多年前他就曾說:「風格是騙人的︙︙塑造風格只是對著自己的焦慮說聲抱歉。」
麼說來,德.庫寧創作上的變化反映了他的哪些自身經驗呢?他的認知功能變化,又在他的藝術裡扮演什麼角色呢?這樣的效果是好還是壞呢?還是好與壞交雜呢?德.庫寧的改變並沒有巧妙地躲過藝術評論家的眼睛。他的改變被視為一種進化而非退化,那些作品有著前所未有的洞見與理解。「畫面的節奏變得更加沉穩、充滿反思,空間更加寬闊──一種新的秩序出現,一種從未見過的冷靜──德.庫寧已從他的疾病中跳脫,他的作品更原始而空靈、運用隱晦的意象去表達背後具體的靈感來源是什麼。」大衛.羅桑德David
Rosand)這麼寫道。「德.庫寧從未遠離大自然,如今又更加親近大自然了。」《紐約時報》的薇薇安.雷諾(Vivien Raynor)則如此描述著。
以上便是二十世紀兩位偉大的藝術大師—愛德華多.奇利達與威廉.德.庫寧的故事。當阿茲海默症於逐漸摧殘他們的生活其他面向時,兩位仍舊在藝術領域創造出一流的作品。無論這種現象背後的解釋是什麼,讓我們先讚嘆一下這個真真實實存在的現象神奇的力量吧。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
前 言
身為一個認知神經科學家,我已經很習慣在實驗室冷靜地討論與大腦相關的抽象概念;身為一個臨床神經心理學家,我的專業訓練,讓我對腦功能障礙或腦傷的跡象高度警覺。不過,這樣的敏銳,只適用於﹁別人﹂的腦損傷,當換成自己接受核磁共振檢查時,我不斷痛苦盤算著自己腦中各種可能狀況。想到還要等待檢查結果出爐,我不禁感到害怕。
這麼自相矛盾的人,可不只我而已。我和許多朋友聊過—都是一些世界級的神經科學家、神經學家與精神科醫師—他們也都承認,他們對自己脖子以上的部位是否健康,都不感到好奇。對於自己大腦的狀況,他...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大腦的一生
第二章: 大腦的四季
第三章: 當歷史上的偉大心靈們,邁入晚年
第四章: 文明社會中的智慧
第五章: 模式的威力
第六章: 探索「記憶」巷
第七章: 永不消失的記憶
第八章: 記憶、模式與智慧的神經機制
第九章: 提「前」做決定
第十章: 全新的事物、熟悉的事物與大腦兩元性
第十一章: 變動的大腦二元性
第十二章: 吃了百憂解的麥哲倫
第十三章: 夏季最熱的一天
第十四章: 多動動你的大腦
第十五章: 模式加速器
終章: 智慧的代價
致謝
參考資料
名詞中英對照
前言
第一章: 大腦的一生
第二章: 大腦的四季
第三章: 當歷史上的偉大心靈們,邁入晚年
第四章: 文明社會中的智慧
第五章: 模式的威力
第六章: 探索「記憶」巷
第七章: 永不消失的記憶
第八章: 記憶、模式與智慧的神經機制
第九章: 提「前」做決定
第十章: 全新的事物、熟悉的事物與大腦兩元性
第十一章: 變動的大腦二元性
第十二章: 吃了百憂解的麥哲倫
第十三章: 夏季最熱的一天
第十四章: 多動動你的大腦
第十五章: 模式加速器
終章: 智慧的代價
致謝
參考資料
名詞中英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