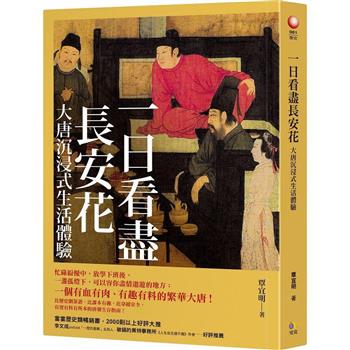序言
七十三歲的素人作家。
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這個夢,作了半個世紀,終於美夢成真。從小會胡思亂想,也很愛讀報紙。上了大學,開始胡謅兩句,登上校刊,自己很得意,卻受同儕揶揄,無非是東拼西揍,「少年不識愁滋味」,無病呻吟的老套。
我沒有上過任何科班的文學課程,所以寫作背景都來自閱讀。喜歡白居易老嫗能解的筆調,以及胡適淡雅自然的語氣。我也不能分辨自己寫的是什麼文體,似乎有些詩的味道,說它是散文最容易:鬆散之文是也。我確實是想著就寫,沒有章法,已經習慣。不過,我會布局,讓文章有層次、有節奏。我對駢文情有獨鍾,就算是白話文,也會不自覺地講求對仗工整,雖然功力膚淺幼稚,卻不在意。我也愛化學,隨著時代潮流,走向理工領域,一輩子就和文學分道揚鑣。
當年,第一次在稿紙上謄寫文章的經驗,記憶猶新;新鮮、期待、小心翼翼,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刻下,然後是漫長地等待被錄用。從職場退休以後,正逢電腦和網路時代來臨。手寫爬格子的勞苦幾乎不再,思考的時間自然擴大,這對書寫者是一大躍進。可以確定,沒有電腦,我不可能累積這麼多的文字。出版業也如此,如今編輯、排版都在彈指之間。自費出版書籍不但容易,甚至已經成為流行。
電腦幫我們儲存,替我們記憶,寫過的,都存在雲端,會永遠留下痕跡。
我寫、我寫、我寫,幾乎每天都在寫。回味自己的文章,總是敝屣自珍,讀它千遍也不厭倦,還會不斷修改添加,往往又是另一番樣貌。概略一算,已經超過一百五十萬字了。這又是另一堂功課——累積的威力,根據《聖經》裡耶穌講的故事,這被現代經營學者稱為「馬太效應」。生命就是經驗和累積的總成;累積、累積,都是一些看起來不起眼的累積。
文學就是生命的解讀,教科書上這麼說——用心觀察,大多數的人都在一個有限的時空裡過日子和演化。就算經常出國旅遊,或是移民,走遍世界,生命過程仍舊被侷限在某一個小角落、小範圍,很難跨越。那些帶領族人翻越山嶺看到新世界的開創性英雄人物,據估計,正好是百萬分之一。文學作品提供了多一種生命的解讀,給世人參考,生命有無限可能,有多重色彩。
我寫我履歷的文明——在這個敗壞中的文明裡,我們仍可以看到許多美善,或許,這才是生命的本質,是非善惡都是本來面貌,每一個世代都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壞的世代。
我有很多故事,我的和我經歷的。故事有兩種,真實故事和虛構故事。「故」、「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過去的事」,理應是真實存在的;虛構的故事是人為的創作,英文裡「小說」和「故事」是同一個字「story」。台灣的俗話說:「戲棚上有那種人,戲棚下就有那種人。」兩者之間經常模糊,然而,不管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故事,都有相同目的,皆為了傳達事件背後的神聖秩序,也可以說是某種事理或真理。
從小就會以怪異的眼光看這個世界,是天生使然。一路走來,自覺「與人間,世味不相投」,經常「不知何處能高歌」(語出:宋代.蕭泰來《滿江紅〔壽大山兄〕》)。那時候,精神醫學還未發達,現代的精神科醫生會給我下診斷,說是「人際關係適應不良症候群」,好像是一種輕微的亞斯伯格症,無可奈何,只好寄情詩文了。我寫的都是真實故事。
一輩子閱讀別人的作品,如今也能留下自己的。出版這本書,單純只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