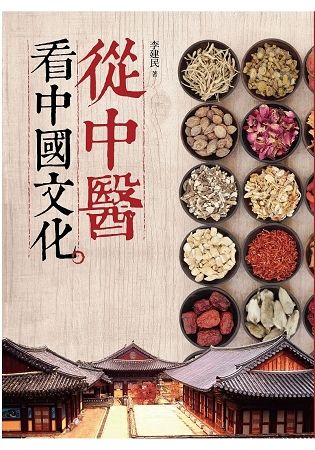一九七0年代以來,大陸考古出土了大量醫學文獻,引起學界重視。對這些出土文物的復原、釋讀、考證、斷代,與現存史料的比對等工作持續進行了數十年,從而引發傳世醫學文獻的斷代與核心醫學觀念的重寫與重建,成為中國醫學史研究的顯學。伴隨著二十世紀末十年,中國興起的一股「國學」熱,「中醫」與傳統文化的交叉研究熱潮也乘時而起,本書即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一本著作。
作者認為,中醫不僅是一門醫學技術,更是一個文化體系。學者或一般人在看待「中醫」時,應以宏觀的文化視野來省視。《漢書‧藝文志》言:「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方技在古代是廣義的「醫學」,包括房中、神仙之術。顧實解釋這段話:「《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秦和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疾,固醫官也。』蓋古醫字亦作毉。上世從巫史社會而來,故『醫』通於治國之道耳。」顯然,中醫的基礎與來源相當複雜。正如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所指出的:「他們創建的體系,不僅是一個政治體系,也是一個宇宙體系和一個人體系統。我們必須理解這個體系的多重性質,特別要理解為什麼在各種科學獨立發展之後,這種有政治意味的系統還如此有吸引力。」這種醫學的文化多樣體,無疑是我們探索古典醫學的核心所在。
基於這個前提,本書開宗明義即申明:不是要透過國學來理解中醫,而是認為中醫本身即是國學的核心要素。中醫與儒道是國學的一體兩面、不可偏廢。是以作者提出:《素問》無疑的應與《論語》、《莊子》、《紅樓夢》成為中國人的生命經典,終身相伴。因此,本書中處理的不同課題,不同於醫學專門者的「醫學內史」,作者是要追求中國文化的通識,是要對傳統歷史文化「全新的整體」之理解。作者呼籲:當我們要重新理解中國文化時,請優先研究中醫文化的全史。
作者說,當我們以「中醫的」眼光,重看中國文化時,彷彿是一個「熟悉化」的持續過程。「熟悉」(heimlich)不僅是對中國文化中隱藏的一面重新理解,它也有「本土的」意思,即中國的本土。中國人理解中國文化卻必須「本土化」,即「中國化」,這聽起來似乎非常弔詭。但中國文化的複雜與內在張力,往往就是在對「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既存事物的「改寫」中持續前行的。因此,重新思考「中醫」與傳統文化的整體關聯,即是本著作的著力所在。
作者簡介:
李建民(Jianmin Li)
1962年3月30日生。臺灣大學史學博士,曾任哈佛-燕京訪問學者(1998),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客座副教授(2002-2003)。執教於臺灣清華大學與臺北大學,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新史學》雜誌社常務社員、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中醫藥雜誌》編輯委員(2008-)、《校園》(基督教福音派雜誌)編輯委員(2009-)、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中醫原創學術文叢》編輯委員(2013-)、《中醫藥文化》「學術委員會」委員(2014-)、《醫療社會史研究》學術委員會委員(2017-)。
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1998)、國科會98年度「傑出研究獎」(2010-2012)、第三屆「大象優秀科技史論文獎」(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辦,2001)。
他主要關注中國「古典醫學」的重建與反思,代表作有《死生之域》、《生命史學》等,曾受邀參與《劍橋中國史》的撰寫工作,並主編【養生方劑叢書】。
著作:
《中國古代游藝史──樂舞百戲與社會生活之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方術‧醫學‧歷史》(臺北:南天書局,2000)。
《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2001年4月再版,2001年12月三版)。
《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簡體字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發現古脈──中國古典醫學與數術身體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本書是《死生之域》的修訂本。
《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2009)。
《隔岸繁花──一個歷史學家的心靈旅行》(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本書收錄學術性隨筆五十篇。
《華佗隱藏的手術──外科的中國醫學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1)。
章節試閱
另類醫學?反思中醫文化
1 「國學」與中醫文化通識
自一九九〇年代初至今,中國持續著「國學」的熱潮。這股熱潮不僅活躍於文化、學術界,而且擴及地方、社會團體。李零將過去二十年的國學熱形容為「一種近似瘋狂的離奇現象」。他似乎視這股不小的潮流,是一個政治化的「舉國」狂熱。但也不能否認,在其中有個人或團體為傳統價值系統的起信及安身立命之道,自發地尋求精神資源。李零在《去聖乃得真孔子》中提到中醫,意思是「新儒家」之類的思想流派的「精神勝利法」與中醫相同:「它要保留的只是內聖,就像中醫,丟了地盤,最終還要領導西醫——在理論上領導西醫。」這是說中醫的技術「地盤」不行、最終只能講一些理論高調嗎?
中國文化傳統包括「中醫」,不但極為豐富、複雜,而且存有不同的層次;我們在客觀地尋求理解的同時,也不斷地做理性的反省。我即想利用余英時先生〈「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一文,對「民國」時期「國學」研究的分期,及不同階段研究的特色及成果,以作為當下「國學熱」的借鑑。
余英時先生將「民國」時期的國學運動分為兩期:第一期是清末至一九一七年;第二期是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以前。這兩大段落的分水嶺,大致是以「新文化運動」為劃界的。先說國學研究第一期。
清末以來的學人以「國學」來作為與「西學」的對照,但也以為西學應該與國學融會貫通。梁啟超即說:「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飲冰室文集》)這種情況也出現在近代中、西醫學。王國維也說:「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觀堂別集》)而中、西醫學同時地進入「盛則俱盛」的階段。西醫對中醫的影響在這個時期,已不像歷史上幾個時期只在一枝一節之上,而是更為系統、全面的。
國學研究的第二期,可以胡適一九二二年在北大《國學季刊》所寫的宣言為代表。這篇宣言認為國學最重要的使命,是要對過去的中國文化進行「專史式」的系統研究。余英時先生說:「國學研究必以建立中國文化史的整體架構為最終歸宿」。這一規劃對今天的國學熱或許仍具有導向的意義。中國醫學史作為不可忽略的「專史」之一,與整體的中國文化史應有更為有機的連接。
第二期的國學研究還有兩項特色。其一是胡適所提倡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其二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分科全面進入到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之內。這兩種情況,在中醫學術、教育也有類似的情況。特別是以科學、實驗室的方式來解釋、證明中醫的理論。不過,中、西醫儘管不斷尋求會通、結合,但在許多關鍵處多是二水分流的局面,而「互相推助」的趨勢卻無疑更加緊密。
在具體的研究成果上,國學研究的第一期,章太炎、廖平都有相當豐富的醫經、醫史的著作。章太炎〈論宋人煮散之得失〉討論古今用藥權量之變化,涉及宋人改湯劑為煮散的歷史背景:「宋人所以創為煮散者,蓋由五代分裂之際,遠方藥物,致之不易,於是減省其量,而以散煮服之。沿及宋時,遂為常法。」南宋煮散風氣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飲片為原料的湯劑。
廖平曾輯錄、評述中醫的文獻二十餘種,題為《六譯館醫學叢書》。他的著述將醫學與經學交互會通。例如,《分方異宜考》論醫書的五行之學,「若醫家專門切要之事,則詳經絡,考部位,識病名,知針藥,於《內經》中取其切要者,不過二三十篇。其屬通論治國、醫人皆所合通者,不過三四十篇。其高深玄遠之《陰陽大論》,與政治陰陽五行家之專篇,則盡可束之高閣,書少功多,庶乎可以自得?收五行以歸經學,日辟國萬里,治法可以重光。」簡言之,醫書多言治國之道,經學史研究也應留意古醫家之論述。廖平又說:「古者經學政法專書,多說人身臟腑。《五經異義》、《白虎通》、《五行大義》、《淮南》、《申鑑》,皆是也。醫道通於政治,如《十二官相使篇》,其尤著者也。」可見經學之書言人身臟腑,不專為治療;政法與醫學兩者貌似神離,用殊理同。
廖平又將《黃帝內經》的內容,析分為「政治、醫診二大派」;這本經典之所以兼言天道人事者,「《內經》本為皇帝外史所掌,旁涉於醫」這些說法,正如匡衡說詩可以解人頤。他認為《內經》治病的專篇,〈小針解〉、〈針解〉、〈八正神明論〉、〈陽明脈解〉、〈脈解〉等五篇,「歷來解家未能合之以成兩美,大抵分篇作注,不免肢解全牛。」因此,他主張將上述五篇合讀,以相得益彰。
國學研究的第二期,陳垣、柳詒徵、呂思勉等幾位國學大師都有中醫文化研究的相關著作。陳垣的醫學史論文很多,主要發表在《醫學衛生報》、《光華醫事衛生雜誌》等刊物。他的醫學史研究,多具現實之意義。如〈釋醫院〉一文,追溯「吾國醫院之制,蓋起於六朝矣」。自此以降,唐有「養病坊」,宋有「安濟坊」,金元有「惠民藥局」等,這些都是官方設立為治療貧民之疾的。陳垣先生說中國人歷來有「以醫院為不祥者」的禁忌,與西人心態不同。他說住醫院有時為必要:「有病須施行手術者必須入醫院」,「有病能傳染家人者必須入醫院」。醫院的歷史,與「現代」醫療技術、衛生制度的革命有密切關係。
柳詒徵在其代表作《中國文化史》中,即闡述中醫藥文化的發展。舉例來說,柳詒徵認為中醫早期重視解剖、手術,外科發達;有人認為中醫治療傾向「內治」並不正確。他說:「蓋古人精於全體之學,劀殺剖割,初非異事,與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又說:「後世獨祖張機,於一切病,唯恃診脈處方之術,是漢代實古今醫法變遷之樞。」所以,以「診脈」、「處方」(湯劑)為主流的「方脈」(內科)一支,並不足完全說明中國醫學之全貌。中醫在骨傷科、瘍醫也有獨特的傳統。
呂思勉的《中國文化史》的「文化」不是狹義的學術技藝,而是「一切人為的事都包括於文化之中」。這本書是以各類專史如政體、刑法、實業等攀上「通史」寫作的宏構。他在為近代醫學史大家謝觀撰寫的傳記《謝立恆先生傳》(一九三五年),即敘述兼通醫術的儒者傳統:「君於醫,雖不以是為業,顧自幼熟誦醫經、經方,長而瀏覽弗輟,親故有疾,或為治療,遇儒醫、世醫、若草澤鈴醫,有一技之長者,必慇勤詢訪討論,未嘗一日廢也。」謝觀肄業於東吳大學,習地理之學,年少曾從馬培之門下學醫。呂思勉說,「予嘗與君上下其論議」,國學與醫學應可對話、相通。
可見,大師們(他們都不是執業醫生)的眼光與今日「內史」取向的研究者或有不同,不少仍具參考價值。從他們所關懷的如外科、醫院、儒醫等課題,及提出的洞見,顯示了極為獨特的視野。
余英時先生回顧第一、第二期的國學研究,指出當今國學研究的處境、脈絡:「我要鄭重地指出,一方面由於西方中心論、科學主義走向式微,而另一方面文化多元論已逐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共識,國學作為一門學術已不再有消解於西學之中的危險。中國自有一個源遠流長的人文研究傳統,這一傳統雖在近百年中受過西學的不斷刷新,卻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在此我並無意倡說「醫學多元論」,以免誤導視聽;但中醫經過百年來的紛擾、打擊終究保持住其「文化身份」,這一點是我個人所深信的。德國學者蔣熙德(Volker Scheid)最新的論著可以支持這個看法。
蔣熙德的新作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孟河醫派三百年》),探討江蘇武進鎮孟河起源的一個中醫流派史及其相關分支的興起、擴展的漫漫過程,時間長達四個世紀。2孟河學派的歷史可以分三個階段:
從十七世紀初葉,費氏家族遷至孟河始,通過血緣、婚姻、師弟及其他社會、政治網絡,逐漸由孟河往上海擴散,形成錯綜複雜的醫學家族(medicinal lineages)。第二階段,在上海名醫丁甘仁的提議下正式出現了「孟河學派」這一名詞;而以上海為民國時期的醫學中心,這個學派產生了「分歧的現代性」的微妙變化。如利用傳統鄉籍的關係建立新的醫學校、團體及學術期刊。而傳統「國粹」(national essence)的潛移默化,及追求儒醫道德的理念已在這一階段現代化的過程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三階段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醫的發展受到國家的支持,以及政治、現代化的持續要求。相對來說,前兩階段的家族、社會關係網絡受到很大的弱化。
中醫的傳統雖然經歷多次強烈的變遷但卻保持一定的穩定結構。所謂傳統是一套文化體系的保存、繼承與改造。而文化是意義創造的具體實現,中醫本身蘊含的意義結構不只是其技術的基礎,同時也貫穿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
一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應該讀哪些書?一八七〇年代的張之洞《書目答問》所建議的書單包含中醫經典。《書目答問》挑選的中醫典籍以唐以前為斷限,一共十三部。有些中醫典籍,非專家也應該讀,這不是張氏個人之見解。
近代四川國學大師劉咸炘在《學略》中提示一般讀者:「《素問》為理祖,非專門亦可讀。李時珍《本草綱目》可考草木名類形狀,亦有益於學者。」粗備國學常識的現代公民應該可以讀《素問》原文。所謂的「理祖」,是指《內經》提供了養生、治病甚至修養、治國的規律。這裡的「非專門」、「學者」,指的不是執業的中醫師,而是中醫在技術層面以外,其知識系統可能成為更多人的「文化通識」。這在傳統社會稱之為「士大夫之學」,指的是「略觀大意」、「存其大體」的讀者及做人境界。它與「專業」、「專家之學」不同,強調的是對國學中的各類學問的貫通、綜合。「文化通識」希望培養現代公民對公共事務、日常生活的判斷能力與人文修養。段逸山先生說,「由儒而醫的現象」非常普遍存在於整個中國醫學史中。
本章的論旨,不是通過國學來理解中醫,而是中醫本身即是國學的核心文化資源之一。中醫與儒道是國學的一體兩面、不可偏廢。而我們為現代人所做的不同層次中醫文獻及歷史研究,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達成「中醫文化通識」的深化及普及。
另類醫學?反思中醫文化
1 「國學」與中醫文化通識
自一九九〇年代初至今,中國持續著「國學」的熱潮。這股熱潮不僅活躍於文化、學術界,而且擴及地方、社會團體。李零將過去二十年的國學熱形容為「一種近似瘋狂的離奇現象」。他似乎視這股不小的潮流,是一個政治化的「舉國」狂熱。但也不能否認,在其中有個人或團體為傳統價值系統的起信及安身立命之道,自發地尋求精神資源。李零在《去聖乃得真孔子》中提到中醫,意思是「新儒家」之類的思想流派的「精神勝利法」與中醫相同:「它要保留的只是內聖,就像中醫,丟了地盤,最終還要領導西...
作者序
序
「中國文化」給予我個人最初的意象竟然與「沙漠」有關聯。我是在臺灣南部鄉下長大的。一九七〇年代末,求知似渴的年紀,我在那個城市街角旮旯的書報攤,找到一本臺北運來的雜誌《仙人掌》。標題醒目:「中國未來動向」、「中國的出發」……沙漠中開花的「仙人掌」,文化沙漠裡的中國臺灣。其實我從沒見過真實的沙漠。
一九七〇年代末,站在城市的電影院前面看大大的劇照,是一種幸福。胡金銓的武俠電影就是我「中國文化」的世界。那是個無窮黨爭、社盟的想像天地。胡金銓作品的「俠」大多有長長的官銜。《天下第一》(一九八三年)的男主角張伯謹是個醫生,全片百看不厭的是針灸治病的游刃場景。這個電影故事由後周世宗尋找民間醫生治病而展開的。「武俠」其實講的是政治權鬥,也是政治智慧。
一九八〇年代初,我北上當兵,在一條叫「重慶」的街道買了一本小冊子《通鑑選注》。那時臺灣出版商人翻印的國學書籍,都改了書名、作者名。這個讀本的作者瞿(蛻)園先生是誰呢?小書有作者長長的序,剪裁襯帖的古文,清楚明白的白話注解,貫穿戰國到五代的歷史關鍵事件的解說,是中國史的極佳入門。後來知道此作品的作者「瞿蛻園」有著「通人」洞見,便盡所能找了他所有的著作瀏覽一過。《通鑑選注》給我的一個啟示,中國文化的主軸是「政治」。
不僅中國文化的主軸是政治,連中國最好的詩也很「政治」。我在臺灣大學求學時,讀過一些「史學方法」的書,其中最為難忘的是洪業的《我怎樣寫杜甫》。這是一本五十七頁的小冊子。直到現在,這本小書仍是我推薦給學生的「治史」啟蒙書。洪先生告訴讀者如何以三百七十四首杜詩來寫杜甫的歷史。這位曾「賣藥都市」的詩人,作品一往情深而不愆於義。洪業先生說杜詩至情的一面在「忠君愛國」。
中醫(廣義)的《黃帝內經》也是政治智慧之書。它是一個俠的世界。治身、治國二而一。醫者意也;政治也是一個「意」。《素問》無疑的應與《論語》、《莊子》、《紅樓夢》成為中國人的生命經典,終身以為師資。中國文化所結的「同晶體」(isomorph)是中醫的自衍、滋生的體系。中醫比附成「科學」是駱駝看做馬腫背。中醫是歷來中國人如何過好的生活的智慧。
中國文化主要的兩大流派,都與「政治」的關懷有關。一是帶有目的或倫理性的,如儒家等。一是「技術流派」。今天我們重新理解中國文化,不能只提倡儒家思想,那即是一座倒立的龐大金字塔而無法立起來。通過中醫的歷史「移感」重看自己的文化是一種方式。
章太炎即將中醫列為「哲學」。在其命名為《菿漢》的幾本小書,可作為一部中國文化史散論。章氏以為百家技藝有與儒術相通者,如按摩、劍術等都講求調氣習定的道理。又論張仲景,主要是飲食養生日用,每令節儉,無至暴疾,及季節的生活習慣。他推崇中國醫學《傷寒論》一支獨尊,如「腸癰」服用大黃牡丹湯,效果不下於手術。
中國醫學史有兩個重要轉型時期,一是南宋,一是明末清初。前者的特色是內在化,中醫並不在技術上突破,而更追求身心修為及內證。這在現代醫學科技發達的後現代,別具意義。南宋代表的是王碩《易簡方》一系的醫學流派,其精神流風一直存在。其次,中醫所謂「復古」,真正是從明末開始的。中醫的「古」只是一個「如」(as)字。我們試圖在歷史找「那詮釋的如」(the hemeneutical as),心摹手追。我們重看了中國文化,相信曾經不相信的,就像「開始」看見那樣來觀看許多事物(believing is starting to look a lot like seeing)。
我較早閱讀的一本醫學史,有王吉民的《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王先生是西醫,卻欣賞中醫。他的醫學史有一節「遊戲」,遊戲也是醫學。後來我的碩士論文的靈感即本於此。文化的原創力往往出自悠閒、遊戲而有餘裕。
猶太思想家Romano Guardini曾經以「群眾人」(mass man)來形容我們現代人。群眾人是一群被現代科技與「理性抽象化」所掌控的人們。群眾人只順服機器、技術的身體感,與抽象計劃的生產模式。群眾人逐漸失去了「位格」(personality),失去「人」的存有價值。中國大陸新一波文化工程是對物化(fetishized)的人及其關係的救贖。
我們以「中醫的」眼光,重看中國文化,彷彿是「熟悉化」的持續過程。熟悉化是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所說的「原創」。「熟悉」(heimlich)不僅是中國文化中隱藏的一面重新理解。熟悉也有「本土的」意思,中國的本土。理解中國文化必須「中國化」。這聽起來似乎很奇怪。但中國文化的複雜與內在張力,往往就是在改寫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情景,作為正負情愫的嘲弄對象。我們都認為「太熟悉」中國文化的某些本質了。而「熟悉化」是用熟悉的事物如中醫日常生活形態(不是醫學專業),去理解業已「陌生的」中國文化而訴合無間。這是作者硜硜自守不敢強作解人的。
中國醫學有明暗。中醫不只是看病把脈、技術的。文化的戥秤上,我更喜歡闇暗、隱去不談的部份。於是我們到達那最昏黑的一角,面對面,看見中國文化的優美與韌性;那曾經使我們失去本土身份,使我們分裂的爭論的歷史長流裡。我們找回對中國文化的「敬畏意識」,共同對著文化存有意識而新奇驚訝,就好像再一次注視了不落凡近、無窮無盡的天空星體。
李建民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序
「中國文化」給予我個人最初的意象竟然與「沙漠」有關聯。我是在臺灣南部鄉下長大的。一九七〇年代末,求知似渴的年紀,我在那個城市街角旮旯的書報攤,找到一本臺北運來的雜誌《仙人掌》。標題醒目:「中國未來動向」、「中國的出發」……沙漠中開花的「仙人掌」,文化沙漠裡的中國臺灣。其實我從沒見過真實的沙漠。
一九七〇年代末,站在城市的電影院前面看大大的劇照,是一種幸福。胡金銓的武俠電影就是我「中國文化」的世界。那是個無窮黨爭、社盟的想像天地。胡金銓作品的「俠」大多有長長的官銜。《天下第一》(一九八三年)的男...
目錄
序
另類醫學?反思中醫文化
1. 「國學」與中醫文化通識
2. 古典醫學的知識根源
疾病的歷史
3. 先秦至中古「病因觀」及其變遷
4. 掩埋屍體禮俗與疾病的想像
5. 鬼神之病與「場所」
中醫技術及其自然、性別、政治意義
6. 艾火與天火—中醫「灸」療法的起源
7. 「附子」毒藥在政治中的運用
8. 傳統家庭的衝突與化解方術
想像身體
9. 唐代「肺石」的身體想像
10. 中國方術史上的「形影觀」及技術
11. 17世紀臟腑圖說的身體觀
12. 明清抵抗火炮的法術身體
純粹手術
13. 3世紀華佗故事的新解釋及啟示
14. 16世紀中醫「反常」手術史之謎
跋:我學習醫學史的經驗淺談
序
另類醫學?反思中醫文化
1. 「國學」與中醫文化通識
2. 古典醫學的知識根源
疾病的歷史
3. 先秦至中古「病因觀」及其變遷
4. 掩埋屍體禮俗與疾病的想像
5. 鬼神之病與「場所」
中醫技術及其自然、性別、政治意義
6. 艾火與天火—中醫「灸」療法的起源
7. 「附子」毒藥在政治中的運用
8. 傳統家庭的衝突與化解方術
想像身體
9. 唐代「肺石」的身體想像
10. 中國方術史上的「形影觀」及技術
11. 17世紀臟腑圖說的身體觀
12. 明清抵抗火炮的法術身體
純粹手術
13. 3世紀華佗故事的新解釋及啟示
14. 16世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