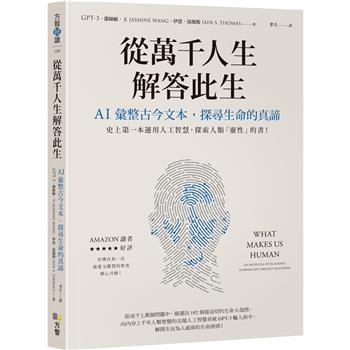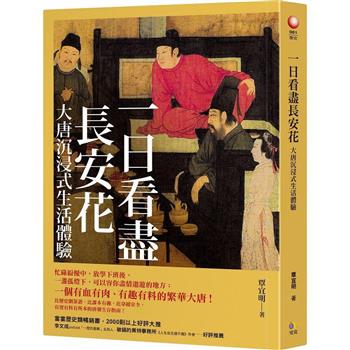書院路27號,如果不是被太后催著去接人,我實在不願意去那個地方。
雖然這個地方是我爺爺發達之後買下地後,為了造福鄉親建的圖書館。
可依山而建的四層小樓,不管太陽多毒,內裡總是陰森森的,夏天倒是因此省了不少電費。後來捐給政府,政府在四層小樓左右各建了一棟三層新樓,又重新翻新舊樓,拆掉了原來的老式門窗,換上又大又敞亮的落地窗,一掃原來黑洞洞的感覺。
不過這般投資,原來姜家圖書館的名字就不能用了,改成了市立圖書館。
之後政府又以圖書館門口的桃樹和小池塘為中心,往外做綠化建成了公園。圖書館還一度因此在省裡評上了獎。
可即便如此,我後來因為參加市里的表彰活動(也去)過幾次,但是每去一次回來必然大病一場。所以對於我來說,那地方如非必要,實在避而遠之。
可今天則是特殊情況,我得接我媽同學的兒子去家裡吃飯。老實說,我感覺這又是一場預謀已久的讀為吃飯寫作相親的活動。自從我媽知道我是gay之後,不但沒有放棄相親,反而喪心病狂地換了相親的性別,給祖國紅紅火火的相親事業添磚加瓦。
到那,我剛出車門就看見有個穿著粉色T恤的青年,正站在圖書館正門口邊的桃樹下,對著我揮手。
我一看那件比桃花還粉嫩的T恤,只感覺眼前一黑,差點想轉頭就走,奈何對方已經迎面走來。
我便只好硬著頭皮迎上前,問:「你好,請問是郎濤,郎先生嗎?我是姜彤,那個……」
那人似乎察覺到了我的尷尬,馬上接過話頭:「你就是我爸爸同學的兒子?」
我點點頭說:「對。」
不想他竟然捂住嘴,吃吃地笑起來:「噗,和我想像不太一樣。」
我被他笑得寒毛聳立,手腳無措,甚至還重新檢查了一下今天剛換的西服:「啊?」
他拉了拉挎包的背帶,說:「我還以為你會故意穿個老頭衫,染個紅毛來。」
「呃……」我不好意思告訴他,我原本是有這個打算,只是後來找不到我爸的老頭衫,而且染頭髮後,明天去公司鐵定會被圍觀。再者覺得這麼對人小夥不太好,還不如之後直截了當地拒絕他。
看我在那發愣,他倒也不見外,翹著蘭花指就一點我的肩膀:「開玩笑的啦,我們走吧,別讓爸爸和阿姨他們久等了。」
這小子講爸爸兩個字的時候,故意學台灣人的發音,嗲嗲的聲音令我在一邊聽著只覺得渾身雞皮疙瘩,每一秒都想拔腿就跑。
心中反覆懊悔著沒有給媽媽好好普及一下gay的常識。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呃,好,車子就停在圖書館對面。」我指著馬路對面的停車場說,「還有小心台階,大門口的石板橋特別滑。」
「好的,姜小哥」郎濤走到我邊上,作勢就要挽上我的手臂。
我連連往邊上倒退了幾步。
「喲,你還挺矜持的。」他如同餓狼撲肉一般擒住了我的肩膀。
我僵著沒敢動。
走過石橋的時候,我看見郎濤原來的位置,站著一個穿綠色舊式軍裝的青年。
他的裝扮很特別,我不由得多看了幾眼。
一件草綠色的老式軍裝,腰間紮著一條棕色的武裝帶,胸前還佩戴著一個紅色胸章。
肩膀上則是挎著一隻和衣服同色的帆布挎包,左手的胳膊上還套著大紅色的袖章,就好像是電視裡出現過的那些紅衛兵的裝扮。
郎濤看我站著不動就問:「你看什麼呢?說起來,以前這裡還是你們家私有的。」
我一邊看著那個青年,他站在桃樹下轉悠,好像在等誰,一邊和郎濤搭著話:「嗯,對,爺爺在的時候,還是這裡的館長。不過後來立了遺囑,不讓我姑姑和我爸繼承,再後來就捐給國」
話還沒說完,郎濤揮手一拍我胸脯。
我險些倒退幾步,只聽見他驚訝地問:「誒,為什麼不讓?難道!」
「是不是太邪門啦?好像說這裡死過不少人,你看都夏天了,桃花還開著。」他低下頭湊在我耳邊故意壓低聲音說道。
我耳朵怕癢,連忙推開他的臉說:「這棵桃花樹確實有點怪。我小時候我媽都不讓來這裡玩。據說以前有人跳水死在這裡了。後來爺爺捐圖書館的時候,指名什麼都可以動,唯獨桃花樹不能動。」
此時,我視野之中那個在樹下的青年突然走到了池塘邊,一隻腳臨空垂在水面上。
我就說要在池塘邊裝上柵欄,結果被市裡管這塊的人以影響美觀給打了回來。
你看,現在是個人都能往下跳。
「你在這裡等我一下。」
我撥開郎濤的手,就往那個青年跑去,心裡祈禱他千萬別往下跳,不然我不會游泳,就很麻煩了。
好在我跑到那,還來得及一把拉住那個青年。
「同學,你……還好嗎?」我氣喘吁吁地問。
青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搖了搖頭。
「這裡池塘沒有欄杆,比較危險。你不要太靠近水邊。」我把他往回拉了拉。
青年點點頭。
「沒什麼事,快回家吧,快吃晚飯了。」我拉著他往回走,沒走幾步,就看見郎濤震驚地看著我。
我回過頭,發現青年已經不見了。
這是跑了嗎?
我不解地走回郎濤的位置。
這時郎濤好像恢復了正常,也不要求和我挽著,也不和我搭話,我們安安靜靜地走到汽車邊,剛坐進去,天色變暗,瓢潑大雨傾盆而下,一點給你做心理預設的時間都沒有。
還沒等我慶倖我和郎濤都上車了。
這小子就出么蛾子了。
我見他低頭翻自己的挎包,嘴裡還嘀咕著什麼,便問:「是不是忘記什麼了?」
「好像是手機落在裡面了。」
我看著車外的大雨,心裡歎了口氣,說: 「我去拿吧,雨這麼大,淋著你就不好了。東西放在哪?
「二樓電子閱覽室和閱覽室中間的多媒體會議室B2裡面,你大門進去左手第一台電腦旁邊,手機應該在那裡。」
「行,那你在車裡等著,我去去就回。」
「謝謝你,姜彤。」
「沒事,應該的。」說著我就從車門邊的凹槽裡拿了把傘打開了車門。
突然郎濤拉住了我的西服下擺,面帶猶豫,語氣吞吞吐吐的。
「姜彤,你剛才……在桃樹下……幹什麼?」
「哦,剛才有個人站在水邊,我怕他掉下去。先不說了,我快去快回。」不等他回話,我就跑著穿過馬路。
我聽見他在後面喊什麼,但雨太大,又隔著馬路,我聽不清。
我揮揮手讓他回去坐著,就頭也不回地走向圖書館。
沒等我走到圖書館,就又在桃花樹那裡看見剛才的那個青年。
這會他呆坐在桃樹下,任憑大雨穿過桃花樹枝,淋在他的身上。
眼看他都快被淋透。
我就看不過這種事,有仇報仇,有怨報怨,犯不著為了別人折磨自己。
我走到他身邊,拍拍他的肩膀說:「同學,你怎麼還在這裡?」
青年低著頭沒理我。
「這個給你。快回家吧。」
我把手裡的傘塞給他,他倒也沒拒絕,有些詫異地接過傘,還站起來對我微笑著揮揮手。
我站著沒動,目送他轉身上了石板橋,才跑進圖書館。
可這就這麼一會,身上竟幾乎都濕了,頭髮上的水不停地往下滴。今天媽媽特地準備的西服,也皺巴巴得不成樣子。
我站在門口理了理頭髮,盡力挽救了一下自己的儀表。
此時圖書館的門口正聚集著不少人,他們猶猶豫豫的,似乎在考慮要不要冒雨走,還是等一等雨勢變小。
我快步穿過他們,拐進右手邊的電梯口,正巧這時有台電梯將要關門。
我一邊大喊一邊快速奔跑:「等等!」
結果我過於專注於看那台電梯,轉彎太快,險些還撞到寫著「青年企業家表彰大會請上三樓」的立牌。
好在電梯裡的人應該是聽到了我的喊話。
電梯門又打開了。
電梯裡面人不多,左側按鈕處邊上站著一個女人,手裡牽著一個孩子,正中央則是一個穿著保安制服的人,右邊的角落裡還有兩個男人背對著我,似乎手還牽著手。
我對按著按鈕的女人道了聲謝,發現二樓的按鈕亮著,就站好不動了。
電梯門緩緩合上。
站著等了好一會,電梯左上角的電子顯示幕上的數位卻始終停留在1上毫無變化,而且電梯也確實沒有任何移動的感覺。
於是我擠到邊上,對站在按鈕邊的女人說:「不好意思,麻煩讓讓。」
雖然我試圖去按2層的按鈕,又試了試關門鍵,但是數字始終沒有變化,電梯也沒有向上移動的感覺。
是電梯壞了嗎?
我有些不解,但也沒有多想就按了開門鍵,打算改爬樓梯。
突然,
滴答——
有什麼東西滴落在我的腳邊。
起初,我並沒有注意,還在檢查電梯的情況,但後來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個味道就好像是菜市場家禽宰殺處那種濃烈的血腥味,腥臭撲鼻,難以忽視。
我這才低頭一看。
眼前的場景令我大吃一驚。
原來我右腳邊,不知不覺中竟然積了一灘紅色的渾濁液體,而且水潭的面積隨著液體的滴落,還在慢慢擴大。
順著水滴的軌跡,我抬頭看去。
只看見原本站在我身邊的女人,就好像融化的雪糕一樣,頭髮混著血肉和腦漿,順著身體往下淌,一直流到我的腳邊。
而且不只是她,她手中的孩子,保安,甚至於角落裡的那兩個男人。
他們的臉已經看不清五官,眼珠、鼻子、嘴巴,都混在紅紅白白的液體裡向下流。
可即便他們的面孔已經無法辨認,但他們的腳尖正指向我,就好像站在原地注視著我一樣 。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書院街27號:姜家圖書館怪談(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言情小說 |
$ 213 |
驚悚恐怖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驚悚/懸疑小說 |
$ 225 |
驚悚恐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書院街27號:姜家圖書館怪談(限)
一次意外,姜彤踏進書院街27號的姜家圖書館,
自此陷入了混亂無序的謎團。
圖書館中為姜彤帶路的詭異玩偶;
屢屢救姜彤於生死,卻來去無蹤的男子;
抽屜裡陳舊泛黃的合照;再次現身的哥哥;
沉浮於暗示與隱喻中的家族袐辛……
肢解、掩埋,錯亂的時間、消失的線索,
血肉模糊的真相掙扎著浮出水面,
姜彤的誤入究竟是一場意外,
還是跨越姜家三代人的命中註定?
作者簡介:
鵝毛筆
資深網路原創小說人氣作家。
一隻熱愛美食的喵喵。
暱稱:鵝喵喵
生日:10月16日
星座:天枰座
職業:作者
TOP
章節試閱
書院路27號,如果不是被太后催著去接人,我實在不願意去那個地方。
雖然這個地方是我爺爺發達之後買下地後,為了造福鄉親建的圖書館。
可依山而建的四層小樓,不管太陽多毒,內裡總是陰森森的,夏天倒是因此省了不少電費。後來捐給政府,政府在四層小樓左右各建了一棟三層新樓,又重新翻新舊樓,拆掉了原來的老式門窗,換上又大又敞亮的落地窗,一掃原來黑洞洞的感覺。
不過這般投資,原來姜家圖書館的名字就不能用了,改成了市立圖書館。
之後政府又以圖書館門口的桃樹和小池塘為中心,往外做綠化建成了公園。圖書館還一度因此在省裡評上...
雖然這個地方是我爺爺發達之後買下地後,為了造福鄉親建的圖書館。
可依山而建的四層小樓,不管太陽多毒,內裡總是陰森森的,夏天倒是因此省了不少電費。後來捐給政府,政府在四層小樓左右各建了一棟三層新樓,又重新翻新舊樓,拆掉了原來的老式門窗,換上又大又敞亮的落地窗,一掃原來黑洞洞的感覺。
不過這般投資,原來姜家圖書館的名字就不能用了,改成了市立圖書館。
之後政府又以圖書館門口的桃樹和小池塘為中心,往外做綠化建成了公園。圖書館還一度因此在省裡評上...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鵝毛筆 繪者: 七芒
- 出版社: 葭霏文創 出版日期:2018-10-26 ISBN/ISSN:978957874920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開數:25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