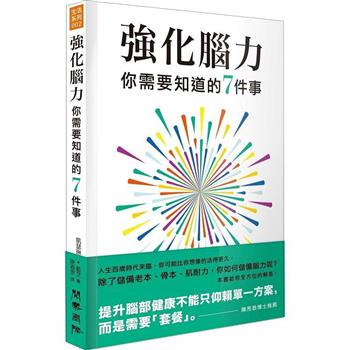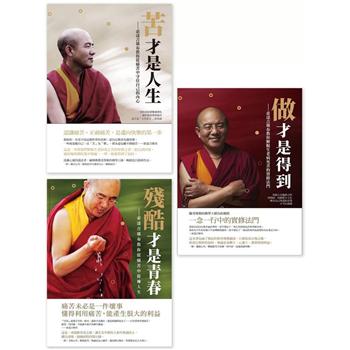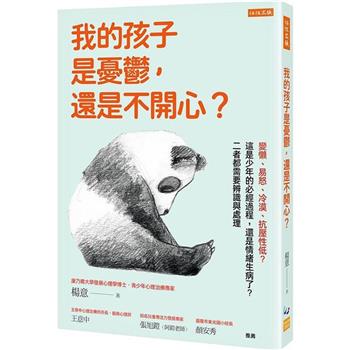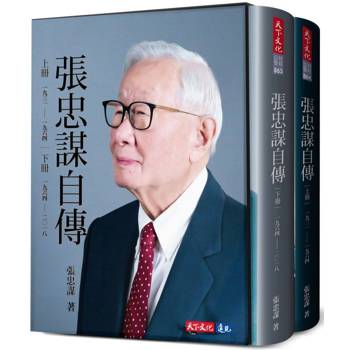因為花園西邊人跡罕至,沒有人會對她冷嘲熱諷,所以錢姑姑才會讓她去花園西邊。
鍾唯唯不置可否,帶著小棠出了清心殿。
她從前是怎麼走的,現在還怎麼走,絲毫不管別人是怎麼看她的,也不擔心會遇上什麼人。如果要躲躲閃閃,避著別人,那躲在屋裡不要出來就好了。
很快,她出來閒逛的消息傳遍了後宮。
各宮開始行動,都往御花園裡去,想要偶遇一下她。
呂純也想去會見一下鍾唯唯,但是裝扮好了又坐回去:「算了,我就不湊這個熱鬧了,你們去打聽一下,萬安宮和芝蘭殿的動靜。」
最早到御花園來偶遇鍾唯唯的女人只能算是小蝦米,遠遠看到鍾唯唯和又又,就虛偽地笑。
想打聽閒聊,卻又沒那個膽子。
再看鍾唯唯一點心虛的樣子都沒有,小棠一副「逮誰滅誰」的凶殘樣,就更沒膽氣和她對著來了,找個藉口飛快遁走。
半圈花園逛下來,也沒遇到狠角色。
小棠鬆了一口氣,抓緊時間勸鍾唯唯:「差不多了,好熱的,我們回去吧。」
鍾唯唯道:「不去,我要在那裡坐坐,等一個人。」
小棠皺了眉頭:「你等誰啊。」
鍾唯唯指指遠處:「等她。」
有些重華不方便做的事,以後都交給她來做好了。
她和韋太后遲早都要對決一場,與其總是躲避,不如早點了結,大家耳根清淨。
遠處一群宮人,打著儀仗,簇擁著韋太后而來。
韋太后神色淩厲,哪怕是隔得老遠,鍾唯唯也能感受到她目光裡的森寒鋒利和得意不屑。正是一副「等你很久了,終於被我抓住你尾巴」的得意模樣。
鍾唯唯微笑著,肅立。
等到韋太后的鳳駕來到她面前,她低頭斂眉,行禮:「下官給太后娘娘請安。」
「不敢當。」韋太后微微探了身,靠近鍾唯唯,用只有二人能聽見的聲音說,「賤人,鳩占鵲巢的滋味很好吧?小偷就是小偷,你的身分地位寵愛,全都是鍾欣然的,鍾家養大了你,你卻要搶占恩人的位置,真夠不要臉的!」
她恨透了鍾唯唯,當然是怎麼難聽怎麼說:「告訴你!鍾氏女想做德妃可以,想做皇后也可以,誰讓先帝許諾了呢?但本宮說的是真正的鍾氏女,而不是你這個冒名頂替者!小偷!騙子!不要臉!」
鍾唯唯早已百毒不侵,心平氣和:「原來太后娘娘才知道下官不是鍾家的嫡女。下官還以為,您早就知道了呢,畢竟陛下是一早就知情的。」
她勾起脣角,露出十分嫵媚的笑容:「大師姐和陛下先於下官認識,然而陛下就是喜歡下官、就是寵愛下官、就是非下官不娶,下官也曾勸他後宮之中要雨露均沾,但是陛下就是不聽、就是要寵下官,下官也是很為難、很惶恐呢!太后娘娘看不慣,不如教教下官怎麼做?」
見過不要臉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
韋太后氣得臉都木了,不假思索地舉手,惡狠狠朝著鍾唯唯的臉打過去。
鍾唯唯靈巧躲開,韋太后撲了個空,卻不肯善罷甘休:「把她抓住!」
「你這個大壞蛋!」
又又突然衝過來,大喊一聲,像小獸一樣朝韋太后撲過去。
一頭撞在韋太后的懷裡,撞得韋太后一個趔趄,宮人眼疾手快扶住她才沒有摔跤。
「小賤種!」韋太后氣得一把揪住又又,劈頭蓋臉朝又又打去。
鍾唯唯攔住韋太后,把又又交給追上來的青影,聲音清冷,一字一頓:「大人的事,不要拿小孩子撒氣,又又身上流著你的血液,你罵他是賤人生的賤種,等同於罵了自己是賤人,這又是何必呢?」
韋太后大怒,手指到鍾唯唯臉上去:「你敢罵我?」
鍾唯唯輕輕巧巧把她的手拿開,輕言細語:「有話好好說,都是斯文人,一言不合就動手,讓人看了笑話。」
韋太后氣得死去活來:「你這個……」
鍾唯唯還是輕言細語:「我這個什麼?太后娘娘,知道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嗎?我是特意在等你。」
她有恃無恐,就連謙稱也不用了。
韋太后收了怒容,上下打量著鍾唯唯:「你想怎麼樣?」
鍾唯唯淡淡地道:「不想怎麼樣,我特意等你,就是想告訴你,我不是小偷,我有父母。我受過良好的教養,我有一手好茶技,我人品很好,名聲也很好。陛下喜歡我,我也喜歡陛下,我臉面不是誰給我的,是我自己掙的。只要陛下願意,我奉陪到底。」
鍾唯唯越是風輕雲淡,韋太后越是憤怒:「你說你當得起就當得起嗎?你想做皇后?想做德妃?從本宮身上踏過去吧!」
鍾唯唯笑笑,不以為然。
韋太后厲聲道:「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打的什麼主意,想要母憑子貴嗎?那也要先生得出兒子來才行!」
「母憑子貴,就像太后娘娘這樣嗎?」鍾唯唯朝韋太后走去,她貼在韋太后耳邊低聲說道,「其實呢,先帝早就預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所以他交給下官一件東西,以免讓陛下為難,背上母子相殘、大不孝的罵名……」
韋太后臉色大變:「胡說八道!」
鍾唯唯微垂了眼睛,臉上一片淡漠:「太后娘娘,兔子被逼急了也會咬人的。是不是胡說八道,您到時候就知道了。您以為,下官等在這裡,是為了和您敘舊或者求饒嗎?」
她並不是全無憑仗,先帝囑託她輔佐幫扶重華,還給了她秘旨轄制韋太后。這東西危險,原本打算不到緊要關頭不拿出來的,現在真是不得不拿出來了。母子相殘對重華沒好處,不如由她來做。
韋太后咬牙切齒:「你好,你好得很……難道你就不怕我弄死你嗎?」
鍾唯唯漠然道:「我不說這個事情,太后娘娘又會放過我嗎?不會,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各憑本事。哪怕就是我死了,那件東西也會在可靠的人手裡,好好地管教你!」
「母後又想生事嗎?」
重華匆忙趕來,眼神陰冷得可怕,把鍾唯唯和又又護得嚴嚴實實。
想到韋雲亭身上那刀刀致命的十二刀,韋太后有些害怕。
再想到鍾唯唯剛才的警告,她心不甘情不願地往後退了一步,虛張聲勢對上重華:「你想打我嗎?你敢不敢打我?有本事你就殺了本宮!看看天下人是否能容得你這個弑母的不孝子!」
「母後太小看朕了。」重華勾起脣角,低下頭,輕聲道,「有件事情,要說給母後知道。有人檢舉祁王私造兵甲,蓄養府兵,朕已派人去查實,搜出五百副兵甲,找到私通勾連京畿大營將領的信件若干。按酈國律,這應該算是謀逆大罪了吧?」
重華話音剛落,韋太后已然爆發:「這是汙蔑!祁王是你的親弟弟!」
重華冷淡地道:「真是遺憾,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朕總不好徇私。」
重華的軟肋是鍾唯唯和又又,韋太后的軟肋便是祁王。祁王是她一手養大的孩子,也是她的依仗和籌碼,更是可以讓她踏著登高的墊腳石。她不能容許重華毀了祁王。
韋太后深吸一口氣,冷靜下來:「陛下,白就是白,黑就是黑,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祁王不會做這種糊塗事,我知道刑部、兵部、大理寺都聽你的,但是朝臣們不是吃素的,他們不會允許你顛倒黑白。」
所以,這算是徹底撕破臉,把雙方的車馬擺出來過明路了?
重華的手裡有刑部、兵部、大理寺,但是吏部、戶部、工部、禮部是韋氏和呂氏的人,現在呂氏觀望居中,工部和禮部雖然還以韋氏、呂氏馬首是瞻,但是底下的人已被重華換了一小半,真的擺明車馬鬥起來,難說誰輸誰贏,只不過國家會遭受重創罷了。
重華微笑著,好整以暇:「母後說得很對,但是這樣的謀逆大案,真的要查究起來,恐怕要拖上很久。朕是很有耐心的,就怕祁王嬌生慣養,吃不了苦。」
來而不往非禮也,你敢動我的心頭肉,我就敢動你的心頭肉。
和不講道理的人講什麼道理?
韋太后惡狠狠地盯著重華看了半晌,再陰冷地看向鍾唯唯,目光最後落到又又身上,冷笑一聲,轉身離開。
但是重華不肯就這樣放她走:「母後留步。」
韋太后倨傲地抬著下巴:「你想如何?」
重華指向李孝壽:「朕要向母後借一個人。」
李孝壽腿一軟跪了下去:「陛下饒命……」
又給韋太后使勁磕頭:「太后娘娘救命啊!」
韋太后當然不會允許重華把李孝壽帶走,不然豈不是相當於當眾搧了她一記響亮的耳光?
她怒道:「我不許!」
重華卻不是和她商量,而是直接下手:「割了李孝壽的舌頭。朕平生最恨這種刁奴,把主人都給教壞了。」
李孝壽被人拖下去,血濺當場。
韋太后似乎覺得那柄雪亮的刀是在她的嘴裡轉動,一拉一割,分外疼痛屈辱。
李孝壽死了,祁王一個圈禁幽閉逃不掉。即便是最後韋氏通過全族之力努力把這個所謂的「謀逆」罪名洗清,祁王也是吃夠苦頭了。
她所輸的,不過就是手裡沒有軍隊罷了,所以重華才會如此囂張。
她這是生了個什麼東西啊?說是兒子,其實和討債的惡鬼差不多!
韋太后憤怒地瞪著重華,顫抖著手指,想說什麼,卻又說不出來,硬生生氣暈過去。
萬安宮的宮人一片悽惶,嚇得如同風中的落葉一樣,抖個不休。
重華淡淡地道:「把太后娘娘送回去,傳召太醫。」
宮人一哄而散,青影識相地先帶著又又離開。
火紅的石榴花下,只留下重華和鍾唯唯二人。
重華輕聲問鍾唯唯:「你和她說什麼了?」
鍾唯唯道:「並沒有什麼,不過是女人之間的那些賭氣難聽話而已。」
她知道,和韋太后這樣對上,重華的心裡其實並不好受。他堅強冷漠的外表下,藏有一顆柔軟敏感的心。
她握住他的手,低聲說道:「你本可以不來。我特意挑在這裡等她,是因為這是我和她之間的事,我可以應對。」
重華張開手臂將她擁入懷中,無聲地使勁抱了她一下。
他拉著鍾唯唯坐下來:「因為你不是師父嫡女的事情暴露出來,又沒辦法突然給你一個身分,所以封妃的事情要暫緩進行。不過這只是時間問題,只要拿捏著祁王,他們就不敢太過分。等一段時間,一切就緒,直接就位吧,我要看著你風光從鳳華門裡被人抬進來,入主交泰殿。」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司茶皇后(4)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1 |
古代小說 |
$ 221 |
言情小說 |
$ 246 |
中文書 |
$ 252 |
古代小說 |
$ 252 |
華文羅曼史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司茶皇后(4)
封妃之事受阻,鐘唯唯與韋太后在花園交鋒,韋太后諷刺其出身不明鳩占鵲巢,重華及時趕到,以徹查祁王謀逆之事大挫韋太后銳氣。太后隨即要挾呂純,指使其出手反對唯唯封妃。呂純利誘前來傳話的韋桑,要韋桑竊取韋後保存的銀鎏金荷花茶盒,韋桑行事時一切順利,似乎有人暗中為其大開方便之門……
芳荼館青雲班迎來茶師選拔,唯唯坐鎮,得到眾多支持,她暗中交代方健助其尋找下落不明的大師兄與鐘袤。時隔不久,鐘欣然母女奉懿旨入宮……
作者簡介:
意千重
資深網路原創小說人氣作家,閱文集團大神作者,言情小說口碑作家。
作者本人熱愛傳統文化,書中涉及傳統文化部分皆考據嚴謹,人物塑造飽滿鮮活,情節富有張力。
章節試閱
因為花園西邊人跡罕至,沒有人會對她冷嘲熱諷,所以錢姑姑才會讓她去花園西邊。
鍾唯唯不置可否,帶著小棠出了清心殿。
她從前是怎麼走的,現在還怎麼走,絲毫不管別人是怎麼看她的,也不擔心會遇上什麼人。如果要躲躲閃閃,避著別人,那躲在屋裡不要出來就好了。
很快,她出來閒逛的消息傳遍了後宮。
各宮開始行動,都往御花園裡去,想要偶遇一下她。
呂純也想去會見一下鍾唯唯,但是裝扮好了又坐回去:「算了,我就不湊這個熱鬧了,你們去打聽一下,萬安宮和芝蘭殿的動靜。」
最早到御花園來偶遇鍾唯唯的女人只能算是小蝦米,遠遠看到鍾...
鍾唯唯不置可否,帶著小棠出了清心殿。
她從前是怎麼走的,現在還怎麼走,絲毫不管別人是怎麼看她的,也不擔心會遇上什麼人。如果要躲躲閃閃,避著別人,那躲在屋裡不要出來就好了。
很快,她出來閒逛的消息傳遍了後宮。
各宮開始行動,都往御花園裡去,想要偶遇一下她。
呂純也想去會見一下鍾唯唯,但是裝扮好了又坐回去:「算了,我就不湊這個熱鬧了,你們去打聽一下,萬安宮和芝蘭殿的動靜。」
最早到御花園來偶遇鍾唯唯的女人只能算是小蝦米,遠遠看到鍾...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