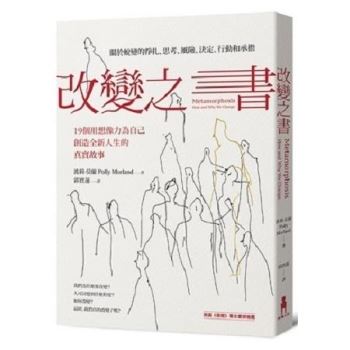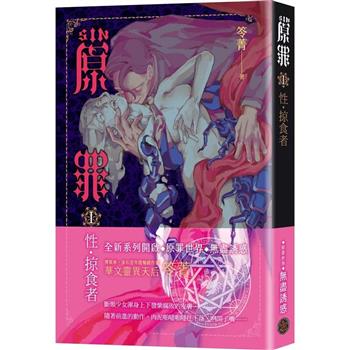這場生日會一直持續到午夜。舒岩早早告辭出來回到宿舍。
許平川想送他,被他拒絕了,他想自己是不是真的看起來很柔弱,以至於每個人都覺得他需要被送回家。
他像每一個來到江州後自己獨處的夜晚一樣,躺在床上,看著書發呆。
舒岩有點懷疑自己的初衷。
先放棄的無疑是自己。那時候他厭倦了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不,其實他不會厭倦,他其實是喜歡的,喜歡這種不用有任何心理負擔的,特殊關係。可是為什麼還是放棄了?
因為即使自己再懦弱,也是自私的。接觸的時間越多,他就越喜歡對方,越喜歡對方就越想獨占對方。
能不能喜歡我?能不能只喜歡我?因為我只喜歡你。
舒岩嘆口氣,把書蓋在臉上,他現在很想給安遠打個電話,他想問問他是不是A先生,不管以什麼樣的問題,就是想問問……可是,他沒有安遠的電話,他忘記和他要號碼了。
那麼A先生呢,現在如果打給A先生呢?他會接嗎?如果自己拿現在江州的手機號碼打給他,他會接嗎?接通以後我可以直接問你是不是安遠嗎?或者,或者這些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如果可以接通,如果真的接通,我可以告訴他,我喜歡他嗎?可以嗎?可以嗎……
舒岩一下子坐起來,他翻出舊卡換上,打開手機,他想只要把A先生的號碼複製到手機通訊錄上就可以了,這樣他就可以……正在舒岩準備點開設置的時候一條短信提示跳了出來:
A先生:你是不是給我打電話了?對不起,手機當時沒在身邊我沒有接到,被別人亂接了。等我再打過去你就關機了。如果你看見這條資訊的話,你能給我打個電話嗎?
舒岩手指有一點顫抖。他看著螢幕,踟躕了。
打個電話給他,不就是自己剛才所想嗎?
但是。舒岩閉上雙眼想:沒有但是。
一個電話而已,還是打吧,不要多想,按下去,然後告訴他。
手機上的時間顯示晚上10點整。
舒岩按下了號碼。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無人接聽。
舒岩想也許他在忙吧。
也許他沒有看見吧。
也許他出了什麼事情?
也許手機丟了?
也許,舒岩想了好多好多也許,從最開始的焦急到惱怒再到擔憂到平靜。
他只想他接電話吧。怎麼樣都好,接電話吧。
我可以承受一切結果,只要你接電話。
可是沒有,什麼都沒有,一遍一遍的無人接聽,到午夜到三更。
手機在枕邊又一次在播放著你撥打的電話無人接聽。
舒岩躺在床上,覺得自己像個傻子。
一個電話,一條短信,都可以輕易的左右自己。
我到底犯了什麼錯,為什麼我的路要這麼難?喜歡就必須是這樣嗎?每個人的戀情都要經歷這些嗎?
是我錯了嗎?錯了嗎?
可是,你們不是和我說,喜歡這個事情,沒有錯嗎……
***
許平川回到宿舍的時候看見抱膝坐在床上的舒岩,月光透過窗子照在他的身上顯得身體蒼白而纖細。
許平川說:「喂,你別哭啊。」
舒岩說:「沒有啊,我沒哭。」
許平川說:「那你臉上的是什麼?汗水嗎?」
舒岩說:「我沒哭。」
許平川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他坐在自己的床上,看著舒岩說:「我是不是跟你說過喜歡這件事情並不丟人?」
舒岩說你說過。
「那我現在再告訴你一個事情。放棄這件事情,也並不丟人。」
舒岩的眼淚流的更厲害了,像斷線的珠子,一顆接一顆的掉下來。
許平川說:「舒岩,哭,也不丟人的。哭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可是哭是一種正常的發洩管道,你不能鄙視它。」
舒岩把頭埋在膝蓋上,肩膀一抖一抖的,他哭的很大聲。
許平川站起來,揉了一下舒岩的頭髮,他說哭吧,舒岩,哭完了,就算了吧。
在這個春天的夜裡,許平川陪著舒岩坐到了天亮。
旁邊床上的舒岩已經哭累了睡著了,許平川起身把舒岩身上的被子又往上蓋了蓋。他看著舒岩紅腫的眼想,如果愛要這麼折磨,那乾脆就不要愛好了。
舒岩醒來的時候覺得全身的骨頭跟散了架一樣,眼睛腫的睜不開。
許平川說:「扭過頭去,你別看我,我害怕。」
舒岩說:「幾點了,上班是不是要遲到了?」
許平川冷笑說:「你問誰呢?你是在問老闆上班是不是要遲到嗎?」
舒岩揉著發紅的雙眼說:「那老闆你給我點時間我稍微洗漱一下就去上班行嗎?」
許平川說:「快別了吧祖宗,你一會去衛生間照照鏡子,就你這個樣子嚴重影響本酒莊形象,我怕嚇壞我的客戶。麻煩您家裡蹲一天,哪也別去,我建議樓也不要下,以免鄰居閒話,以為你被家暴了。」
舒岩瞇著眼看著許平川,頭髮一團糟,他皺著眉說:「這樣不好吧,本來給的工資就挺少的,你還總讓我請假,你心裡過意的去嗎?」
許平川樂了,說:「成啊,還有心思說這種話,說明你傷的不重。那什麼,跟我說說怎麼回事吧,你總知心姐姐知心姐姐的叫,我也不能白擔這麼個稱呼是吧。」
舒岩說:「能不說嗎?」
許平川:「沒有這個選項。」
舒岩想那就說吧,反正之前也都說過了很多,臉在許平川面前早就丟的差不多了,還有什麼不能說的呢。
於是他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細細的和許平川說了。
許平川聽後皺著眉頭問:「就為這個?」
舒岩不高興了,他說:「什麼叫就為這個,你知道什麼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許平川說:「那駱駝被壓死了嗎?」
舒岩沉默了,他不知道怎麼回答。
許平川說:「舒岩啊我其實真的搞不懂你這個電話,電話戀愛吧……你這樣累不累?你為什麼不直接發個短信給你的那個什麼A先生,告訴他,你已經在江州了,這是你的新號碼,問他願不願意和你見一面,有什麼事情當面說,這樣不好嗎?你幹嘛要把卡換來換去的,我不知道你這樣折騰自己的用意是什麼。」
舒岩說:「你猜,你猜我用意是什麼。」
許平川說:「你別說了,我現在不想知道了。我跟你說,你有氣不要衝著我發好嗎?!祖宗,你當我什麼都沒說過,你有錢,你就願意用倆手機卡,願意倆手機卡都充錢養著,我沒有什麼意見啊。」
舒岩說:「等等,你等等,你剛剛說什麼?手機卡充錢?」
許平川說:「對啊,你的手機卡沒錢怎麼用。」
舒岩說「:……我一直忘了充了。我當時很難過,覺得一輩子都不會用這個卡了,我就沒有去充過錢了,到現在已經三個多月了。」
「但是沒停機是嗎?你想打的時候隨時都可以用是嗎?」
「打客服,查一下充值記錄。」
舒岩拿著手機直愣愣的看著許平川,許平川一把把手機搶過來說:「沒用的東西!成天就知道跟我凶!我打。」
舒岩直直的坐在那裡看許平川打電話,見許平川沒說幾句就掛了電話。
「怎麼樣?」
許平川看著舒岩腫的可笑的眼,他說:「有人給你老家這個手機卡充了一千。」
「啊?」
「啊什麼?」
「哎……」許平川皺著眉說,「我想……他是怕和你失去聯繫。」
可是已經失去聯繫了……
舒岩,患得患失是病,得治。
「只是沒有打通電話而已,你就覺得已經是絕地了嗎?你說這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要放棄嗎?要結束嗎?我覺得你和對方都很奇怪,這算搞什麼呢?戀愛的小遊戲?為什麼不能坦白的說呢?」
舒岩沒有回答,他想許平川說的挺對的,但是誰會不想從容,坦然,瀟灑的談一場愉快的戀愛呢,我也不想愛成這樣啊,可是,可是……可是我很慫啊……
舒岩想著這些就把手機拿了過來,他猶豫了一下,給A先生發了個短信:
【我昨天給你打了電話,但是沒有打通……如果方便的話,你可以給我手機13xxxxxxxxx打電話,這是我在江州的號碼。】
舒岩看著資訊,想了想,又把後面那句刪除了。他覺得也許還不到時候,也許自己還沒準備好,也許……他刪除後又寫了一句:
【每天晚上9點以後我都會開機,你可以聯繫我。】
然後按下發送。
他想,我現在只攢了這麼多的勇氣。
做完這些,舒岩關了手機,換上了平日用的卡。剛開機,李林的短信就發了過來,他問舒岩要不要參加他們公司主辦的一個培訓課程,程度大概是wset2,李林覺得課程很基礎,適合舒岩來聽一下,。而且這次的講師很不錯,是馮易,李林的老師。短信上李林把地址日期都一併寫上發了過來。
舒岩把這個事情和許平川說了一下,許平川點點頭說:「去吧,這種課程聽聽總是沒錯的,畢竟你沒什麼基礎,還是要系統的學習一下,不過……不過我提醒你,和李林最好不要走的太近。」
舒岩說:「為什麼?你之前不是一直讓我和他學習嗎?」
許平川說:「學習是學習,李林絕對是合格的講師,但是我的意思是,在工作以外的地方,不要和李林走的太近,他和咱們不是一路人。」
「他不是也是GAY嗎?」
「是的,他是。但是這也是他和咱們不一樣的地方,他,有女朋友。」
舒岩從知道自己是同性戀那一天起就從沒想過要交女朋友或者結婚之類的。
出櫃這種事舒岩還沒有仔細考慮過,但是他想總不能耽誤別人女孩子吧?好好的姑娘家家的誰不是想找個愛的人共度一生?可是自己註定給不了她或者她們愛,所以乾脆敬而遠之,保持適當距離。
他不是很理解李林這種行為。他問許平川李林是不是雙性戀?許平川冷笑說:「他是不是雙性戀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算是雙性戀也不能有了女朋友的時候又去找男人吧?他就算是異性戀,也要保持對愛情的忠貞吧?」
舒岩說:「從你嘴裡說出忠貞兩個字還是感覺挺違和的。」
許平川搖頭道:「此言差矣,我雖然在性方面比較隨性,但是我並沒有腳踩過幾條船啊。如果我有了喜歡的人,我肯定不會再去找別人的,我覺得這是對這段感情起碼的尊重。而且李林這個樣子也不是第一次了,他應該就是GAY,只是交個女朋友當幌子那種,估計以後也會結婚生子吧。這種人嘴上說的是屈服於現實為了父母為了家人什麼的,可是實際上他們才最是自私。他們會說婚後我會對這個女孩子好,我會照顧她,做個好丈夫,做個好爸爸。可是哪個女孩子僅僅是因為你會對她好才嫁給你的呢?哎,不說這個了,總之還是不要和他,或者說他這群人走太近,和他玩的好的幾個人,都和他大體差不多,有幾個都結婚有孩子了,還不是偷著出來玩。他們騙的了別人但是騙不了自己,心和身體分分鐘都在出軌的邊緣,不出櫃,卻要出軌,我看不起他們。」
舒岩點點頭:「我也說不清,但是我不會那樣做的,絕不會。」
許平川笑著看了他一眼,起身換衣服,他說:「你今天就在家裡待著吧,我去上班了,晚上可能不會太早回來,我還要去安遠的店裡跑一下,看一下他那邊的進度。」
安遠。舒岩咯噔一下子,他想自己就憑聲音就斷定他是A先生是不是有點可笑?
自己費勁心思見了林立,可是卻什麼結果都沒有。
他其實不是很在乎安遠是不是A先生,他在乎的是A先生是不是真的真實存在。
當然,A先生必然是存在的,可是舒岩現在看不見,摸不著,如果對方是安遠,那麼舒岩至少會覺得A先生離自己這樣近,至少他是一個實體:有血有肉有表情。
安先生的表情總是有點嚴肅的,雖然他常常對許平川笑,可是面對自己,安先生總是沉默的時候多。
舒岩想自己對安先生,還是瞭解的太少。
許平川招呼了一聲就出門了。舒岩躺回床上想再睡一下,他覺得自己真的是有點累了,昨天一夜的折騰,直到早上才感覺又稍微活過來一些。
舒岩閉著眼,想起了A先生充了一千塊的事情,忍不住笑了起來。
舒岩覺得此刻的自己一定像極了電視劇裡那些坐擁粉紅色房間的少女主角一樣,為了一點柔情而沾沾自喜。
真的只要一點柔情,就可以忘記傷痛。
他想這種感情真的太可怕了。
他曾經想過為什麼會對A先生如此的執著,但是自己也解釋不清楚,也許真的就是在恰好的時間恰好的情緒中遇到恰好路過的那個人。在最終的結果出來之前,舒岩不知道A先生是不是恰好對的那個人,但是在已經過去的那個冬天裡,A先生是他孤獨寂寞的時候最溫柔最溫暖最掛念的人。
我真的曾經放棄。我也並沒有覺得丟人。雖然心很痛,可是我有試著去放棄。但是,我還是帶來了那張發誓不用的卡,我還是撥通了發誓不再打的電話,我甚至抵抗不了相似的聲音,走過的街道,路過的街亭,這些都讓我想到你。想你是不是也曾經和我看過一樣的風景。
許平川說喜歡並不丟人,放棄並不丟人,哭也不丟人,那麼什麼才丟人呢?
舒岩想,只有對自己說謊,才最丟人吧。
在周公把舒岩帶走前,舒岩迷迷糊糊的想:如果這段戀情並沒有一個好的結果,但是自己至少可以學會不對自己說謊吧。
或者少說謊。
第八章
再次醒來的時候,手機響個不停。舒岩現在手機一響就容易激動,他快速的把手機拿過來細看,發現號碼並不認識,他想是不是安先生找自己?畢竟自己很久沒有出現了……不論A先生是不是安遠,工作總還是要做的,可是現在都是許平川在替自己跑腿,想來老闆召了自己這樣一個員工也是夠倒楣的。舒岩深呼吸,給自己做了一下心理建設,他想無論聲音再像A先生,現在,至少是現在,安遠是安遠,A先生是A先生。他接通了電話,放在了耳邊,呼吸還是不能平靜。
「喂,請問是舒岩舒先生嗎?」
聲音溫柔清亮,這不是安遠。
「我是,請問你是哪位?」
「不好意思,冒昧給你打電話,因為你一直沒有聯繫我,我怕你是太忙忘記了,所以和李林要了你的電話,擅自先打給你,我姓宋,宋知非。就是上次卡特落品酒會上弄髒你西裝的那個人,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印象。」
舒岩想起了那個並不愉快的品酒會和那位總是得體從容的先生,他忙說:「我記得的,你是宋先生。」
宋先生說:「我見你一直沒有聯繫我,所以我就主動來和你索要清洗費的單據了,這事兒我一直想著呢。」
「啊,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有聯繫你,是因為……」
舒岩想因為那西服我根本還沒送去洗,最近光顧著悲春傷秋,想是西服已經不知道在哪個角落變成了鹹菜疙瘩。但是這話他不能說,好歹還是要維護一下自身的形象的。他於是扯道:「因為是我朋友送去洗的,他回來也沒有給我單據什麼的,我也是忘記問了,所以我並不知道價格。另外,真的,這個事情宋先生不用掛在心上,小事情而已,西服洗乾淨了就好了,宋先生這個錢真的不要給了。」
「這樣啊……」
電話那頭宋知非的聲音有一絲笑意他說:「那麼你把我的手帕還給我吧。」
舒岩腦子嗡的一下,他想手帕?那條手帕早就不知道扔到哪裡去了。
他想不管怎麼樣先穩住再說。
「手帕啊,那個好的,手帕我會還給宋先生的,你看要不然你留個地址,我寄給你?」
宋知非說:「寄給我就不必了,我這幾天正好要出差,不方便收快遞,你看這樣好不好,我回來以後,咱們約著見一面,我請你吃頓飯,就當是為那天的失禮賠罪了,到時候你把手帕拿來,一舉兩得。」
舒岩想那是正好,還有幾天時間,足夠他把手帕找到洗乾淨還掉,但是如果找不到……找不到再說找不到的吧。於是舒岩就答應了宋知非的邀約,宋知非笑著說:「那麼舒先生我們過幾天見了。」
舒岩說:「好好,過幾天見。」
掛了電話,舒岩開始滿世界尋找西服和手帕,好在他的世界不大,就70平米。西服這種大件,翻一翻還是能翻到的。但是手帕這種小件,就如同房間裡有異次元的黑洞一樣,早不知道被吸到了哪裡去。舒岩急的滿頭大汗,他想怎麼自己被潑了一身的酒,反而還要賠點東西出去呢?
舒岩最後累的坐在沙發上,還是沒有找到手帕,他想乾脆賠一條給宋知非吧,就是不知道宋知非用的手帕,會不會很貴。他想想自己的工資,又想想宋知非的穿著,腦子繞了一圈後,忽然想到了A先給交的1000塊錢話費。
舒岩想,這錢,要是直接折現,該有多好啊。
***
已經是晚上11點,雖然對於江州來說這個夜晚才剛剛開始,但是對於安遠來說,每一分鐘都是煎熬。
白天的時候以為可以見到舒岩,但是並沒有,許平川依舊一個人來的,他說舒岩又一次病了。他想仔細詢問一下情況,可是許平川似乎不願多說,只是打著太極把話題扯遠。
安遠拿出一根菸點燃,叼在嘴裡,他趴在方向盤上,看著雨刷劃來劃去。車外的雨好大,只有這車裡的一方天地是安靜的。
車停靠在馬路邊上,昏黃的路燈下,雨水顯得格外清晰,雨滴爭先恐後的拍打在車窗上,安遠吸了一口菸,拿起了放在副駕駛上的手機,他一手夾著菸一手翻看通話記錄,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寶貝兩個字。
昨天第一個電話響的時候,他正在和宋知非吃飯。
安遠終於在宋知非工作的地方「偶遇」了他,自然要請他到自己新開的餐廳吃個晚飯。宋知非還和以前差不多,總是掛著笑,對誰都很客氣,他見到安遠表現出的平靜讓安遠心裡很不是滋味。他以為他自己已經變的很好了,至少,至少配的上一個讚許的眼神。可是沒有,宋知非還是那樣禮貌的微笑。
把宋知非帶到自己的餐廳,宋知非笑著誇獎了幾句,安遠特意把位置安排在了那副牆繪的位置。
餐廳裡的燈光並不明亮,暖黃色的燈讓一切都看起來隱祕與曖昧。那滿牆壁的向日葵就像生長在黑暗中一樣,向日葵田中騎著瘦馬的騎士早已被陰暗吞噬。
宋知非笑著說客隨主便,請安遠做主替自己安排幾道菜,安遠自然選著得意的上。
一道一道的擺上來,雖然是西餐卻是中式的吃法,這也是這個餐廳的特點之一。
安遠喜歡隨意一點的生活,他厭惡正式西餐的拘謹,也不喜歡西式簡餐的粗暴,所以他選了個折衷的方案,菜是正宗的西式,卻是可以自由組合,隨人心意。酒自然是之前都搭配好的,許平川那天試菜還是草擬了一份酒單,本來是要等舒岩來細化的,但是此時是來不及了,安遠知道宋知非是懂酒的人,正藉著這個由頭請他批評指正。
宋知非拿著酒看了一下,笑說:「居然是義大利的呢,安遠你知道的很多嘛。」
安遠忙說:「沒有,也是請人幫忙弄的。」
「這酒很好,配這個菜正合適。」
「是嗎,那太好了。」
安遠看著宋知非喝酒,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讓他想起高中的日子,他離他那麼遠,沒有什麼機會說話,現在終於離宋知非這麼近,卻又沒有話說。
他有點想去抽一根,雖然他們坐的是吸菸區,但是他拿不準宋知非是否介意他在他面前吸菸。
宋知非是個極稱職的客人,他話不多,但是不會冷場。他和安遠淡淡的說著以前學校的日子,說的全是些無關緊要的事和人,也會說現在的情況,三筆兩筆的帶過,安遠坐在對面,也笑著討論,看起來很和諧,裝的很像老友敘舊。
已經是最後的甜品了。
宋知非晃著白葡萄酒,他的目光終於停留在那副牆繪上。
「這畫挺好看的。」
「謝謝。」
宋知非收回了目光,依然繼續著他們不痛不癢的話題。
安遠的內心無比的失望。他看見宋知非望著畫的雙眼,裡面很平靜,毫無波瀾。
宋知非似乎都忘了,當然,可能他根本也不在乎。
那年宋知非臨走前辦的那場同學會,他拿走了宋知非的酒,而在成堆的送給宋知非離別的禮物中夾雜著自己畫的一副賀卡。
也是大片的向日葵天,但是天是藍的。
「我可以抽支菸嗎?」宋知非笑著問。
安遠愣了,他沒想到宋知非會抽菸,他點點頭說:「當然可以,這裡是吸菸區。」
宋知非掏出菸來熟練的吸起來。
「你要來一根嗎?」宋知非把菸推到安遠面前。
外國菸,安遠婉拒,他抽不慣。
安遠拿出的依然是自己的長白山,這麼多年來,他還是喜歡這個味道。
呼出那口氣,煙霧繚繞中,安遠稍微覺得舒服了一點。
對坐著抽菸,成熟的談笑,安遠等了十年,終於和宋知非坐在一起,但是這好像和自己想要的相去甚遠。
兩人盡職盡責的聊到了十點鐘,老同學的戲碼演的很足。
宋知非告別的時候說:「這裡真的很不錯,等到正式營業,他一定會帶朋友過來,到時候可要給他打折。」
安遠笑著表示無論宋知非什麼時候來,都必定是店裡的VIP。
看著宋知非遠去的背影,安遠覺得心空的很。
取車準備回家的時候,安遠發現自己那部私人的手機提示燈一直在閃,他心忽然跳的厲害,他打開手機,螢幕上的未接來電下都是「寶貝」兩個字。
他想起自己發的那條短信,他想起那天發現被表妹帶回家的男人隨意接了電話的事情。他曾經以為,他再也聯繫不上他的寶貝了,每天夜裡,他都撥打著對方的電話,可是每天都是關機。那一天,他把一副隨時都會哭出來表情的舒岩送回了宿舍。也只有那一天,他把手機忘記在了家裡,結果就錯過了對方的電話。
舒岩。
安遠想到這個看起來乾淨單薄的男孩子。他看自己的眼神總是專注又小心,矛盾吧,就像是在電話裡一樣。
安遠猜,舒岩就是電話裡那個人。
他沒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也有九分的肯定。
一個來自於小城市的年輕的並不專業的品酒師。
怎麼會那麼巧合,樣樣都合得上。
而且那天那通電話那種清亮乾淨的聲音,順著空氣穿越幾千里,安遠閉上眼,他想,我找到了。
螢幕又一次亮了起來,安遠看著手機,卻沒有接。
鈴聲一遍一遍的迴盪在車裡,他有點怕。
他才和宋知非吃了一頓愉快的晚餐,他目送著宋知非上車離開,他覺得他連頭髮都是疲憊的。而此刻他坐在車裡,他無法去接這個來自於曾給他最大溫柔和安慰的人的電話,他很怕他叫不出寶貝,他很怕自己掩藏不住的煩躁,而這煩躁,可能真的說不清,是為誰。
安遠心裡亂透了,他開始如同每次在通話中和對方提及宋知非後那樣怨恨自己。他不想再為了其他人而給對方帶來任何不快和傷害了。他知道有些話不應該說,可是他總是忍不住,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電話裡總是對那個人那樣的肆無忌憚。安遠不是不害怕後果,他怕極了,可是他總是會在對方的柔情中不計後果。
其實說到底,還是因為自己是個自私的混蛋吧。
電話一遍一遍的響起,安遠把車開的極快。
直到進門的時候,電話還在響。
安遠回到房間,把手機放在了枕邊,他聽著鈴聲一次又一次……直到靜默。
此時隔壁傳來了男歡女愛的聲音,安遠想:
為什麼?這世界如此糟糕。
早上的時候收到了對方的短信。
對方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說著可以晚上9點後聯繫他。安遠看了以後覺得更難過了。
是什麼讓自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他?
安遠不敢想。
今天是和許平川約好見面的日子,他很想逃避。他不知道怎麼樣來面對舒岩,他可能還對自己,真正的自己,對安遠這個人一無所知。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電話情人(下)(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4 |
二手中文書 |
$ 193 |
中文書 |
$ 198 |
華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電話情人(下)(限)
當舒岩來到了安遠的城市,與安遠有了交集之後,漸漸對對方的身分產生了懷疑,在現實與虛擬的縫隙中,兩人彼此試探,卻從不攤牌。
電話中的A先生和現實中的安遠,舒岩不知該不該先邁出那一步……
作者簡介:
桃白白
生日:12月30日
星座:摩羯座
資深網路原創小說人氣作家。
一言箋:重度尷尬癌晚期。
章節試閱
這場生日會一直持續到午夜。舒岩早早告辭出來回到宿舍。
許平川想送他,被他拒絕了,他想自己是不是真的看起來很柔弱,以至於每個人都覺得他需要被送回家。
他像每一個來到江州後自己獨處的夜晚一樣,躺在床上,看著書發呆。
舒岩有點懷疑自己的初衷。
先放棄的無疑是自己。那時候他厭倦了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不,其實他不會厭倦,他其實是喜歡的,喜歡這種不用有任何心理負擔的,特殊關係。可是為什麼還是放棄了?
因為即使自己再懦弱,也是自私的。接觸的時間越多,他就越喜歡對方,越喜歡對方就越想獨占對方。
能不能喜歡我?能...
許平川想送他,被他拒絕了,他想自己是不是真的看起來很柔弱,以至於每個人都覺得他需要被送回家。
他像每一個來到江州後自己獨處的夜晚一樣,躺在床上,看著書發呆。
舒岩有點懷疑自己的初衷。
先放棄的無疑是自己。那時候他厭倦了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不,其實他不會厭倦,他其實是喜歡的,喜歡這種不用有任何心理負擔的,特殊關係。可是為什麼還是放棄了?
因為即使自己再懦弱,也是自私的。接觸的時間越多,他就越喜歡對方,越喜歡對方就越想獨占對方。
能不能喜歡我?能...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