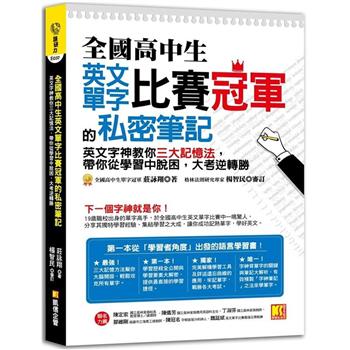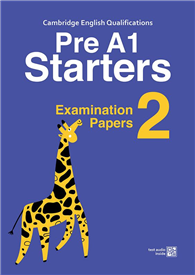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泰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近年在國際理論,特別是在面臨傳統美國勢力和中國崛起兩股力量的東南亞國家中,時興一種稱為「對沖外交」的策略。簡單來說就是小國拒絕「選邊站」,不加入中美任何一方勢力,採取在效果上互相抵消、看似矛盾的外交策略,進而維持己方模糊的立場,留下退路。諸如東盟各國及本書的主角泰國,都多多少少施行這類的兩面政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泰國曾經將自己定位為美國的重要戰略盟友,在越戰時泰國是美國在東南亞反共的堡壘,以及美軍的基地。同時美國也提供數百萬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做為回報。然而,作者觀察到近幾十年來泰國的對外關係出現了驚人的逆轉,曾經是死敵的中國,如今被泰國軍政府視為有價值的盟友。這項轉變反映了中國一步步增加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也同時是美國在亞洲的重大挫折。
在本書中,作者班傑明.札瓦基考察泰國自一九四五年到二○一四年的政治發展,以堅實的歷史分析,大量的文獻紀錄和深度訪談,剖析原本是美國堅實盟友的泰國,為何會向中國投懷送抱。泰國與東南亞各國又如何在美國宣布「重返亞太」時,成為中美雙方的角力場、全球事務的戰場。這場外交戰爭虛掩在泰國內政的派系鬥爭、選舉角力、軍事政變、經濟發展與財閥崛起的錯縱脈絡間,兩頭牽拉的是崛起中國強化地緣安全的需求,以及冷戰後美國對於亞洲發展的政治短視與錯估形勢。
作者在本書最後總結,泰國往中國的偏移,對於整個東南亞區域未來發展方向是重要指標,因為每個國家都將面臨與泰國類似的區域經濟與地緣政治的抉擇,到底該親中還是親美,要如何才能求取國家的最大利益。
【國際書評】
一本描寫關鍵時刻的重要書籍。札瓦基投注澄澈目光,縝密研究美國最複雜、最具歷史重要性的其中一段亞洲關係。
——蕭恩.克里斯賓(Shawn W. Crispin),《亞洲時報》東南亞主編
札瓦基的悉心記錄與平衡分析,為一步步發生、時常隱而未現卻似乎無可動搖的地緣政治漂移掀起簾幕。詳盡說明泰國所面臨的處境,導致一度被視為斬釘截鐵的美國盟友,愈來愈傾向務實且策略上具決斷力的中國。
——麥可.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哈佛大學
對於普遍成見展現有力的反論述,一般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就能解釋泰國的背離美國、往中國靠攏。藉著透徹研究的細節,本書追查美國傲慢與笨拙外交的遺憾路徑。
——丹尼爾.法恩曼(Daniel Finemen),著有《特殊關係:美國與泰國軍政府》(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美國罕見地從「我們對其人民一無所知的遙遠國家」深深增廣見聞,本書研究令人坐立難安,描述改變世界的美中動態角力如何於泰國開展。讀畢令人垂淚。
——傑弗瑞.萊斯(Jeffrey Rice),著有《戰事到隆安:一個越南省分的革命衝突》(War Comes to Long An: Revolutionary Conflict in a Vietnamese Province)
作者簡介
班傑明.札瓦基Benjamin Zawacki
畢業於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及聖十字學院。二○一四至二○一五年哈佛法學院人權中心訪問學者,並擔任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學術會員至二〇一六年。曾任五年國際特赦組織東南亞研究員,且是美國總統卡特,以及緬甸兩位「資深領袖」的政策顧問。札瓦基定期為東南亞媒體撰稿,長住泰國十五年。
譯者簡介
楊芩雯
做過雜誌記者和編輯,現為專職譯者。譯有《聖彼得堡》、《製造俄羅斯》、《普丁的國家》、《蝗蟲效應》、《總統的人馬》、《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強尼上戰場》獲二○一五年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翻譯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