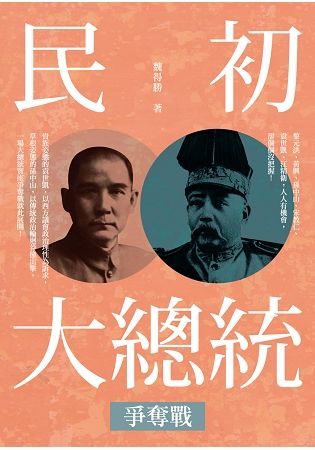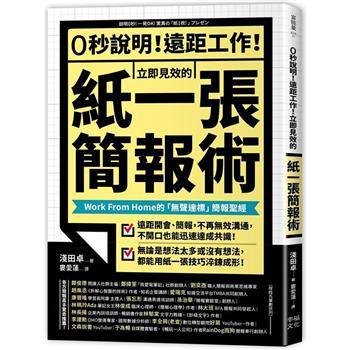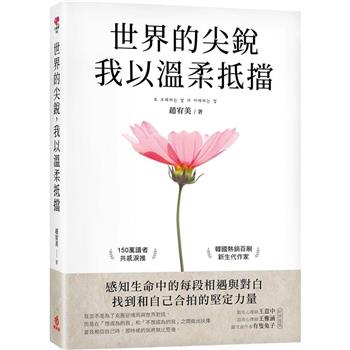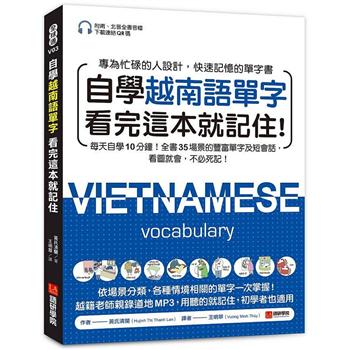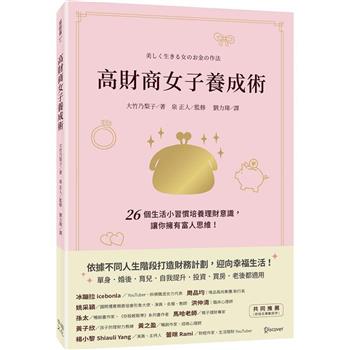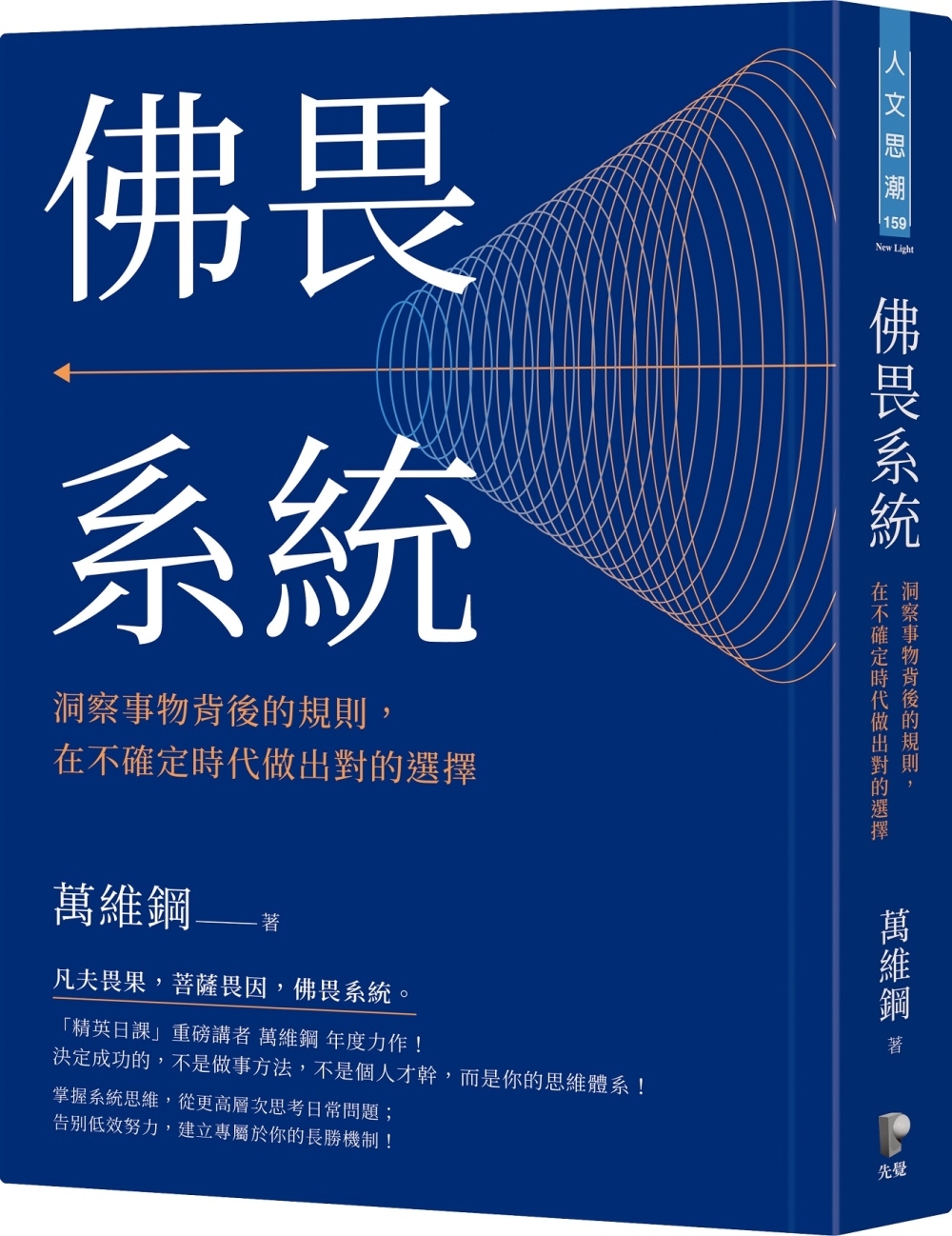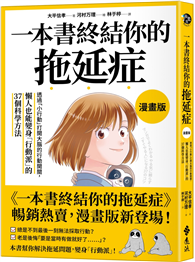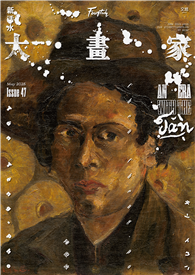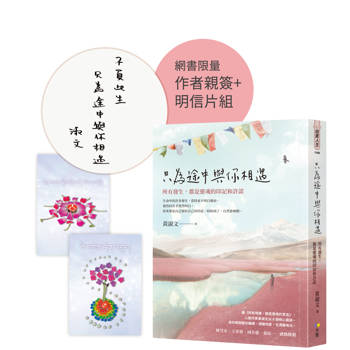序
當同齡人正在大學裡攻讀時,我卻奔波於中越戰爭的前線與後方之間,用手中的筆或照相機,記錄一個特殊的時代。漫長的中越局部戰結束後,我除了每天到辦公室看看報紙和書信之外,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讀書,我稱之為惡補。為此,我特別感激上司對我的寬容,給了我多年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的機會,使我得以回到書齋,研習自己喜歡的歷史。在軍中機關大院,我的行蹤是辦公室、寢室、食堂,三點一線,周而復始。
大約是二○○一年的某個時候,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某某報社的編輯,約我在湖邊喝茶。我並不認識那位編輯,因此有些猶豫。對方解釋說,他是從大學歷史系某教授那裡,獲知我的電話的。我釋然,並答應赴約。畢竟,茶約的地點,就在我的寓所附近。
繞翠湖一圈,有幾十家茶樓,而相約的地點,卻在一個研究院內;而且,不是一個編輯,而是幾個陌生的副刊編輯,他們來自不同的報社。大家落座後,被問最多的就是自修什麼專業。我說是歷史。又問,哪一部分呢?我說是北洋史(以下簡稱民初史)。之後,這些讀書版的編輯,便向我約稿。約著約著,他們發現,我的歷史寫作,距民初史越來越遠。我的筆觸,自遠古史出發。
歷史研究這部分,我最大的缺失就是沒有師從(但這也恰恰是我的長處,可自成一體),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完全沒有捷徑可走。研習民初史之初,我感覺有些吃力,弄不明白,民初人物的所作所為。逐漸得出一個認識,若理解民初,須先理解民初之前的歷史;若理解中國史,須先理解世界史。是以從中國的遠古史、從世界史著手,一路走來,完成中國簡史、世界簡史,以及多本中國斷代史的寫作,這才回到最初我最想研究的那個民初史。
我鎖定的民初史,大致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八年。這本書,就部頭(篇幅、體例)而言,是本小書;就內涵來說,或不止於此。我從未試圖顛覆歷史、解構歷史,更不會為歷史翻案。我要做的,就是去理解歷史,並把我的理解形成為史觀,然後解釋給讀者,與大家一起討論。討論歷史的目的,並非一味的追尋歷史真相,而是從中獲得思想的伸展,以便讓我們在當下或未來的生活中,保有最大程度的文化尊嚴。
魏得勝
二○一七年秋,於翠湖西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