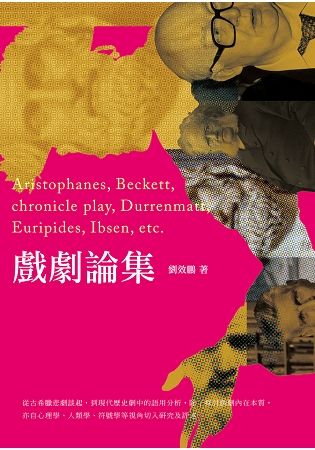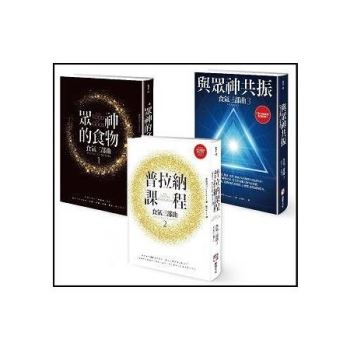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戴神女信徒》劇中的曖昧與嘲弄
摘要
尤瑞匹底斯(Euripides)於垂暮之年,客居在馬其頓時,寫下這齣奇偉的《戴神女信徒》(Bacchae)就像是要嘲諷那些努力為他貼標籤和尋求定位的批評家。他在這部悲劇的形式上全然回到傳統,並且展現了駕輕就熟、完美的技巧。同時,因其取材於一樁廣為流傳的歷史事件─戴昂尼色斯(Dionysus)返回希臘的底比斯,探究其廬山真面目以及悲劇的源頭,似乎是最後向雅典人證明其悲劇的驚世才華。
有的人說該劇是理性主義和叛逆的尤瑞匹底斯的臨終遺言,也有人說他放棄了一貫質疑神和宗教的立場,更有人坦承沒有辦法說清楚它真正的意圖,但沒有人能否定它的魅力、強烈、奇幻之美。主要是因為該劇呈現出多重的對立,矛盾,與曖昧,而且常以反諷或悲劇的嘲弄方式表達,彷彿怎麼說都能講得通,然而又都只是片面與枝節。
本劇的衝突與糾葛主要建立在戴昂尼色斯與彭休斯(Pentheus)之間的對抗,形成整個動作推進的力量。雖然彭休斯是不自覺地陷入某種困境和圈套,但是他的急躁、傲慢、剛愎自用才是他無法脫困、走向悲劇結局的根本原因。剛開始他幾乎扮演了迫害宗教的角色,到後來竟成了受害者、犧牲品。
這部戲劇之所以如謎般地複雜與難解,完全出自戴昂尼色斯:他一方面像個救世主解放那些被壓迫的婦女和低下階層的人,賜給信徒們忘卻憂愁的酒、音樂,與慈愛,使其歡樂自由,變得更有生命力,與神同在、合而為一;但在另外一方面,他卻讓信徒失去理性,變得瘋狂,拋家棄子,茹毛飲血,回到原始;再則他對所有輕視、懷疑和反抗他的人更是陰險毒辣,殘忍無情。
其實,戴昂尼色斯與彭休斯的對峙完全不成比例,酒神預知一切的結果,根本是在玩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故意被捕,然後脫困;王宮地震失火,大顯神威;計誘彭休斯窺探祕儀,反被識破;極盡羞辱後,終為母親和姨母所殺,死無全屍,真可謂慘絕人寰。彭休斯之死,猶可說是咎由自取,地生者怎能與天神的苗裔相抗衡!然而,亞格伊(Agave)只有當年不信其妹與宙斯的雲雨之情,甚或是有關酒神的出生故事;如今已是入門的信徒,為何還要慘遭親手殺子之痛,並且變成一條蛇到處流浪,其姐亦然。甚至殃及底比斯的締造者卡德穆斯(Cadmus)─酒神的外公,也要貶為蛇,流放到外地。凡此種種殘暴地摧毀整個家族,極盡羞辱地對待自己的血親,豈止是太過,簡直邪惡。果真如此,這樣的神、這樣的教派應該盛行於希臘,一年有四個隆重的節慶,尊衪為戲劇之神,每部悲劇的主角都是戴著面具的戴昂色尼斯?
關鍵字:ambiguity, irony, Bacchae, Dionysus, Pentheus
--------------------------------
尤瑞匹底斯(Euripides,480-406B.C.)是希臘三大悲劇家中最晚的一位,但可能比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496-406B.C.)死得早些;因為有史料記載,索氏在得知尤瑞匹底斯的噩耗後,率領合唱團在古希臘劇院(proagon)散髮著喪服以示哀悼,同時亦可見他們雖屬競爭者、勁敵,但也有敬重、相惜之情。另外有一個巧合,也值得希臘悲劇研究者重視的議題,那就是兩人在生命的臨終前,無不竭盡所能完成巨著,而且都與以往的劇作風格迥然有別,似可代表他們最後的悲劇觀照。更令人驚訝的是,在馬其頓的尤瑞匹底斯所寫的《戴神女信徒》,雖然在內容上奇幻、狂野、浪漫,但在表現形式上卻規矩、緊湊、統一,比起二十多年前的《米迪亞》(Medea),有過之而無不及;反過來,索福克里斯的《在克隆納斯的伊底帕斯》(Oedipus at Colonus)神祕、抒情、富哲理,卻在結構上很鬆散頗有尤氏昔年之風。
不過,尤瑞匹底斯有生之年只得過四次獎,遠不如其他兩位悲劇家,因此,也可以說他在當代比較不受歡迎。差堪告慰的是,所傳流下來的作品以他最多,總共有十七部悲劇,和唯一完整流傳至今的羊人劇(satyr play),比兩位前輩加起來還要多;有可能是後世更喜歡他的劇作,作家的顯與隱真是難說得很。
至於當代人為何比較不歡迎他的作品?其中的原因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表現形式技巧上的缺失,另一類是有關表現內容上的爭議。第一類又可分成下列幾點:(1)他有好多部劇本在序場(prologue)中直接道出動作的前因、現在的情況、行事的動機,和預期的結果,類似我國戲劇中的自報家門模式。一般的批評家認為是欠缺藝術技巧的明證,同時也可能失去懸疑,劇場效果不佳。(2)有些插話之間缺少邏輯的關聯,顯得多餘和累贅,破壞統一的原則。(3)經常以神從天降的方式來解決劇中的衝突、困境與命運(參見Poetics1454b,頁15)。(4)合唱團與戲劇動作的關係薄弱,僅淪為段落劃分的功能。誠如亞里斯多德所云:「合唱團也應當作為演員之一;它應該是整體的一部分,參與動作,要像索福克里斯的處理樣式,而不是尤瑞匹底斯。」(劉效鵬譯,頁152)第二類是認為他貶低了悲劇人物的高度,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有損英雄的尊嚴。尤其是愈細膩、愈真實地表現心理的動機和過程,愈構成問題。再者,批評者認為他所選擇的某些題材不適合在舞台上演出:例如米迪亞為了報復傑生的負心而殺子;費特兒(Phaedra)對其繼子希波利督斯(Hippolytus)之激情;亞格伊(Agave)在瘋狂中殺子,並炫耀伊之英勇事蹟等等。此外,他對傳統價值觀頗有微詞,質疑神的公正性,認為人類的禍福取決於機運,他所關切主要是道德問題而不是神或宗教(參見Brockett,頁22-23)。
然而,垂暮之年,自我放逐,客居於馬其頓的尤瑞匹底斯,寫下這齣奇麗炫目的《戴神女信徒》,像是嘲諷那些努力為他貼標籤和尋求定位的批評家。他在這部戲劇的表現形式上,全然回歸傳統,接近艾思奇勒斯(Aeschylus, 525-456B.C.),而且展現出駕輕就熟、完美的技巧。除了在序場中仍是由戴昂尼色斯一個人的獨白,介紹故事背景,說明他自己的出身來歷,回到母親的故鄉要為她洗刷污名,報仇雪恨,廣招信徒,建立其教派,與壓制該城邦的君主彭休斯戰鬥。雖然稍嫌直截了當,但清晰有力,戲劇的動作已經開始,衝突一觸即發,懸疑確立,張力十足。合唱團是由來自東方的亞洲,追隨戴昂尼色斯多年的女信徒組成,她們是參與動作的演員,成為整個戲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個插話之間都有密切關聯,具有概然或必然的邏輯性,並無多餘或不必要的場次。
其次,本劇取材於一樁廣為流傳的歷史事件:戴昂尼色斯回到母親的故鄉─希臘的底比斯。雖然這個的題材艾思奇勒斯已經處理過,並且在其情節中保留了很多這個古老神話與奇蹟發生的典型風貌,但是完整流傳下來,提供豐富訊息者反而是本劇。當然,我們不能視其為歷史劇,因為希臘的悲劇家向來對於神話傳說題材的處理都是別出心裁、獨具匠心、不受限制,更何況尤瑞匹底斯以反叛和挑戰傳統聞名於當世者。同時,他的旨趣在創作,寫出個人想像的酒神面貌和事情的真相。甚至在本質上或內在上(intrinsic)不是個宗教的命題及其演繹,可能更關切的是人類的依存關係,或者是人與環境之間的緊張性、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抑或者尤瑞匹底斯只是藉著戴昂尼色斯作為一種手段,利用酒神祕儀的狂歡所產生的戲劇動作,幫助觀眾思考其自身存在的神祕性與危險性(Rosenmeyer,頁371)。
不過,無論如何,酒神總是跟悲劇的起源有密切的關係─亞里斯多德說:「悲劇根源於酒神頌之作者。」(Poetics1449a,頁13-14)可能脫胎於羊人劇;希臘雖是多神的民族,但西元前五世紀只有在酒神祭才演戲,與整個戲劇的發展史相結合;更不用說後世的尼采(1844-1900)認為希臘悲劇是以酒神所代表醉的、非造形的音樂藝術,和日神所代表夢的、造形藝術結合,並自其靜穆的語言中誕生。兩種極端相反、矛盾對立的力量之間的衝突與和解,從而有這樣的怪話:「用戴昂尼色斯的狀態顯示與說明,但是以音樂可見的象徵,作為戴昂尼色斯狂喜的夢世界。」他甚至概括地說:「它是一個無庸置疑的傳統,在希臘悲劇最早的形式中,只記載了戴昂尼色斯的受難,而他也是唯一的演員。在尤瑞匹底斯之前,都是足夠公正的說法,唯一的主角,乃戴昂尼色斯之遺族,其他所有希臘舞台上著名的人物,普羅米修斯、伊底帕斯等等,都只是原本主人翁的面具。事實就是一個神隱藏於所有的面具後頭,對這些名人多麼值得讚美的理想性格所做的評斷罷了。」(Nietzsche,頁65-66)
是故,尼采斷言希臘悲劇傳至尤瑞匹底斯而亡,因為他注入了理性,但罪魁禍首卻是蘇格拉底,從而有這樣的批評:「褻凟神明的尤瑞匹底斯啊!當你想迫使這臨終者再次欣然為你服務時,你居心何在?它死在你粗暴的手掌下,現在你需要一種偽造的冒牌神話,它如同赫克勒斯的猴子那樣,只會用陳舊的鉛華塗抹自己。而且,就像神話對你來說已經死去一樣,音樂的天才對你來說同樣已經死了。即使你貪婪地搜刮一切音樂,你也只能拿出一種偽造的音樂。由於你遺棄了酒神,所以日神也遺棄了你;從他們的地盤獵取全部的熱情,並將之禁錮在你的疆域內,替你的主角的台詞,磨礪好一種詭譎的辯證法─你的主角們仍然只有模仿的冒充的熱情,只講模仿的冒充的語言。」(頁69)再者,尼采認為:「尤瑞匹底斯經歷悲劇這種垂死的掙扎,……而後以繼起的藝術阿提卡新喜劇而聞名。在他身上,悲劇以變質的形態持續存在,成為悲劇異常艱難而暴烈的死亡的紀念碑。」(頁70)由於尼采認為悲劇之可貴在於能以遊戲的方式,建構個體的世界的毀滅卻能流露出原始的喜悅;我們眼見酒神所化裝的個體,憑藉其意志陷入戰鬥的羅網,為其所犯的錯誤掙扎和忍受苦難而在舞台上說話行事;並且我們可以從這個苦難的景象中體察真相,因為這個世界根本是混沌不明、非理性、不能理解的;如果認為它是理性和有秩序的,反而是一種錯誤的幻覺。在尼采看來尤瑞匹底斯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不能同時既做詩人又做思想家,認為他在某種意義上所戴的面具和說話的口吻既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蘇格拉底。「所以,尤瑞匹底斯的戲劇是一種既冷又燙,既可凍結又可燃燒的東西。一方面盡可能地擺脫酒神因素,另一方面又無能達到日神的效果。……它既是冷漠悖理地思考『取代日神的直觀』,用熾烈的情感『取代酒神的興奮』,乃是偽造出來的、絕對不能進入藝術、思想和情感。」(頁78-79)於是尼采總結尤瑞底斯的審美原則是「理解然後美,與蘇格拉底的知識即是美德為平行原則。因此,我們可以把尤瑞匹底斯看作是審美的蘇格拉底主義的詩人。新藝術的先驅,也是舊悲劇的毀滅者。」(頁85)依此觀點,尼采認為尤氏是藉著《戴神女信徒》向當代提出,要把原始全能的酒神因素從悲劇中排除,重建非酒神的藝術、風俗和世界觀的基礎,要把他從希臘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可是,酒神太強大了,最聰明的對手彭休斯都被迷住了,然後就帶著這種迷惑奔向自己的厄運(頁76)。因此,他以諷喻的口吻說:「尤瑞匹底斯必定被雅典法庭的酒神女信徒撕成碎片,但畢竟他把這位無比強大的神靈趕跑了。」(頁82)然而,尤瑞匹底斯並沒有落到如此悲慘的下場,相反地,本劇和其他的兩部戲劇由其後人提出參賽為他贏得第五次獎。
可能的原因是其處理的方式與態度,他的雙面對待、多重的對立、矛盾與反諷的方式,因此有人認為他已放棄一貫質疑神和宗教的立場;但有人以為它是理性主義和反叛的尤氏的最後遺言,甚至認為無人能說清楚本劇真正的意圖和目的。
然而,悲劇畢竟是模擬一個動作,不管它多麼複雜、曲折,和富於變化,必然是具體可把握的,更何況有其長度上的限制,不可能是無窮或龐大到無法理解的程度。同時,戲劇的動作是由人來表演,必然擁有性格和思想兩個不同的層面和性質,就因為這些我們才能描述動作的本身,而性格和思想是動作產生的兩個自然的原因,而動作又決定了所有的成敗。然後,情節是對動作的模擬(Poetics, 1450a)。是故,現在我們雖自本劇的動作和情節入手,但又不可避免地涉及性格與思想兩面向。
前已言及這部戲劇在開始的序場中就由戴昂尼色斯來自報家門,敘述其神人所生的高貴出身,卻遭到污蔑,因此必須平反冤屈,且要挾怨報復卡德穆斯及其女兒:「我使那些姐妹們瘋癲,離開家庭,住在山上,精神錯亂。我還逼她們穿上我祕教的服裝,所有住在底比斯女人,只要是女人,我都使她們離家。……儘管這個城市不願意,但它必須澈底了解沒有加入的後果。」(32-40行)接著他又指責彭休斯壓制其教派,與神作對,不承認他是一位天神,一定要處理(39-49行),假如用武力帶走山中的信徒,就會率領她們一起戰鬥(51-53行)。甚至戴昂尼色斯已號令由亞洲來的女信徒吹著笛子打著鼓,聚集在彭休斯的宮門前,情勢逼迫到一觸即發的地步。按照第一場彭休斯的倒敘,戴昂尼色斯到達底比斯推行新教掀起這番波瀾時,他湊巧出國,一回來就聽到:「這個城市有了新的邪惡,我們的女人利用一種假的神祕狂歡作為藉口,紛紛離開家庭,聚集在深山密林,用舞蹈禮敬一個新神,戴昂尼色斯,不管祂究竟是誰,她們藉口是酒神的信徒要舉行儀式,在酒器裡裝滿了酒,其實是把愛神放在酒神之前,一個個溜到荒野去滿足男人的情慾。有些我已經逮捕,戴上手銬,由官員安全收在監獄;那些留在外面的,我將從山上,捕捉下來,然後用鐵網綁住她們,即刻停止她們所有的邪惡縱情。」(216-32行)彭休斯在還沒有查明新教祕儀的真相之前,單憑自己主觀的臆測、想像她們必然從事淫褻的勾當,就立刻下令拘捕所有的信徒,足以顯示出他性格中的急躁、專斷,和傲慢特徵。當然,新教女信徒紛紛離家,聚集在深山中進行的祕儀活動,完全顛覆了該社會婦女原本的地位與角色,必然破壞了舊秩序,造成極大的震撼,讓統治者非常不安與恐懼。從而彭休斯也基於政治的敏感性和權力的威脅性,對這位傳說中的酒神已經非常敵視、嫉恨,大有除之而後快了:「我會將他的腦袋齊肩砍下。」(240行)對於外傳戴昂尼色斯的長相溫和、俊美,「金黃色又氣味芬芳的鬈髮,面頰紅潤,兩眼蘊藏著愛神的魅力」(235-36行),是可以讓「他日以繼夜與年輕女人廝混,引誘她們去歡樂慶典」的根本原因(237-38行)。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彭休斯更不肯承認戴昂尼斯是神,以及衪的奇特身世:「這傢伙聲稱曾經被縫在宙斯的大腿內,事實卻是他和他的母親同時死於雷擊,因為謊稱宙斯與她做愛。無論那外地人是何等人物,以他如此狂妄的言行,難道不該活活吊死?」(242-47行)因為這等心理狀態和性格,導致彭休斯不自覺地開始扮演了宗教迫害者的角色。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戲劇論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8 |
戲劇總論 |
$ 343 |
中文書 |
$ 343 |
戲劇 |
$ 351 |
戲劇評論 |
$ 351 |
藝術設計 |
$ 351 |
表演藝術 |
$ 351 |
Arts & Photography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戲劇論集
|本書集結作者近年發表的專論文章,內容涵蓋東西方戲劇研究,分析各種戲劇獨特的美學與藝術表演體系。
|作者嘗試從傳記、歷史、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等視角,跨領域分析藝術文本,提供藝術研究者另闢蹊徑的研究參考。
本書收錄作者近年來發表的論文,除了從戲劇內在本質分析外,亦自傳記、歷史、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等各種不同的視角切入。其中有兩篇是古希臘的悲劇和喜劇的探討,其他則是現代或當代劇本的研究。〈海達蓋伯樂的笑容〉最是微觀的分析;而〈歷史劇的語言〉則涉及宏觀問題;至於〈鏡框式舞台與京劇戲台人物上下場之強調方法比較〉係屬導演領域,且涵蓋兩種不同的劇場與文化,各有其獨特的美學與藝術表演體系。
集結作者近十年發表的九篇論述,研究題材貫穿古今,並以多元角度剖析戲劇蘊含的美學及藝術性,是戲劇藝術研究學者值得參考的書籍。
作者簡介:
劉效鵬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及藝術研究所。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和研究所。曾任華岡藝術學校校長、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主任,亦曾任教於世新、銘傳、輔大、台藝等大學相關系所。
著有《海達蓋伯樂研究》、《戲劇評論集》、《亞里斯多德詩學論述》、亞里斯多德《詩學》譯註、《導演的基礎元素》(即將出版),並發表〈永樂大典三本戲文與五大南戲結構比較〉、《暴風雨》的五個中譯本舉隅比較等論文。
章節試閱
《戴神女信徒》劇中的曖昧與嘲弄
摘要
尤瑞匹底斯(Euripides)於垂暮之年,客居在馬其頓時,寫下這齣奇偉的《戴神女信徒》(Bacchae)就像是要嘲諷那些努力為他貼標籤和尋求定位的批評家。他在這部悲劇的形式上全然回到傳統,並且展現了駕輕就熟、完美的技巧。同時,因其取材於一樁廣為流傳的歷史事件─戴昂尼色斯(Dionysus)返回希臘的底比斯,探究其廬山真面目以及悲劇的源頭,似乎是最後向雅典人證明其悲劇的驚世才華。
有的人說該劇是理性主義和叛逆的尤瑞匹底斯的臨終遺言,也有人說他放棄了一貫質疑神和宗教的立場,更有人坦承...
摘要
尤瑞匹底斯(Euripides)於垂暮之年,客居在馬其頓時,寫下這齣奇偉的《戴神女信徒》(Bacchae)就像是要嘲諷那些努力為他貼標籤和尋求定位的批評家。他在這部悲劇的形式上全然回到傳統,並且展現了駕輕就熟、完美的技巧。同時,因其取材於一樁廣為流傳的歷史事件─戴昂尼色斯(Dionysus)返回希臘的底比斯,探究其廬山真面目以及悲劇的源頭,似乎是最後向雅典人證明其悲劇的驚世才華。
有的人說該劇是理性主義和叛逆的尤瑞匹底斯的臨終遺言,也有人說他放棄了一貫質疑神和宗教的立場,更有人坦承...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本書是我十年來陸續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現在集結成冊。首先要感謝那些邀稿人,尤其是台灣藝術大學的劉院長晉立教授,沒有他們的敦促我就不可能寫成這些命題作文。然而,書被催成墨未濃,十年磨劍未竟功。雖迭經修訂,但疏漏仍多,謬誤依然不免,如蒙賜教,感激不盡!既要遵循學術論文的風格,總得拾人牙慧,東施效顰,差堪告慰的是尚能保有幾分自己的主張和見解。渡過學海,見到多少奇峰巨浪,愈發讓我膽顫心驚,頓時失去寫作的興趣和信心。所幸內子丹鳳總是給予安慰和鼓勵,哪怕是滄海一粟,也有其微末的價值。故以此書獻給她,感...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戴神女信徒》劇中的曖昧與嘲弄
摘要
自希臘、儀式、佛洛伊德之觀點論《利絲翠塔》中性愛消弭戰爭的喜劇性
摘要
壹、前言
貳、妙點子(A Happy Idea)與〈會飲篇〉
參、滑稽與可笑
肆、自儀式角度的詮釋
伍、佛洛伊德對消弭戰爭的主張和亞里斯多芬的點子相去不遠
海達蓋伯樂的笑意
摘要
前言
壹、動機目的與方法
貳、分類討論
參、結論
論易卜生與索爾尼斯世界之毗鄰
破題
壹、胸中之竹
貳、寧非烏有
參、未完成待續
《等待果陀》中的否定與創意
摘要
壹、沒有情節不說故事...
《戴神女信徒》劇中的曖昧與嘲弄
摘要
自希臘、儀式、佛洛伊德之觀點論《利絲翠塔》中性愛消弭戰爭的喜劇性
摘要
壹、前言
貳、妙點子(A Happy Idea)與〈會飲篇〉
參、滑稽與可笑
肆、自儀式角度的詮釋
伍、佛洛伊德對消弭戰爭的主張和亞里斯多芬的點子相去不遠
海達蓋伯樂的笑意
摘要
前言
壹、動機目的與方法
貳、分類討論
參、結論
論易卜生與索爾尼斯世界之毗鄰
破題
壹、胸中之竹
貳、寧非烏有
參、未完成待續
《等待果陀》中的否定與創意
摘要
壹、沒有情節不說故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