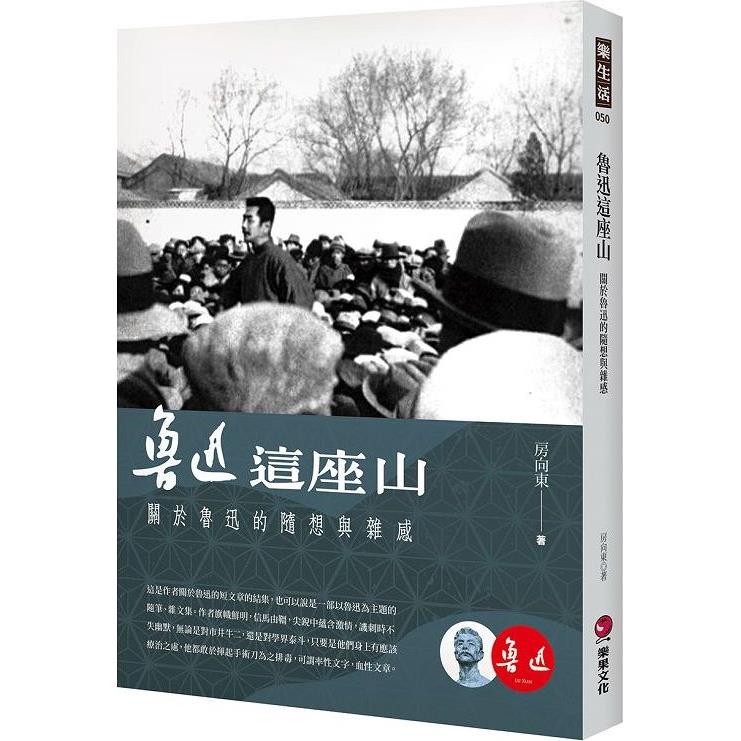多維視野中魯迅「罵人」現象的再審視........................................8
1.「罵人」與魯迅的偉大................................................8
2.蔡元培把西方之花種植在中國的土地上..................................10
3.不只是魯迅在「罵」..................................................11
4.敢罵與「罵以上的事情」..............................................12
5.「罵人」與友誼......................................................13
6.團體與團體中的個人及個人傾向........................................14
7.以「現代評論派」為麻雀..............................................15
8.魯迅只是抓其一點,不及其餘..........................................18
9.不以親疏好惡定高低..................................................19
10.人是會變的..........................................................19
11.魯迅「罵」過的人的變化..............................................22
12.雜文的「不滿」與「罵人」............................................24
13.魯迅論人的理性態度..................................................29
14.魯迅「罵人」的幾種類型..............................................32
15.「實罵」與「虛罵」..................................................35
16.「大眾的靈魂」和「時代的眉目」......................................39
17.魯迅的「多疑」......................................................41
18.歷史的環境讓魯迅「刻毒」............................................48
19.魯迅是單純的、寬容的................................................54
魯迅:現代中國最受誣衊的人..................................................58
1.魯迅:現代中國的孔夫子..............................................58
2.「拳王」地位與文壇週期性「感冒」....................................59
3.屍骨未寒,罵聲即起..................................................61
4.魯迅一無是處之一:魯迅不是革命家....................................62
5.魯迅一無是處之二:魯迅不是思想家....................................71
6.魯迅一無是處之三:魯迅不是文學家....................................81
7.魯迅一無是處之四:「私德」問題......................................89
8.做為政治符號的魯迅..................................................93
9.喜愛魯迅作品與忠誠「黨國」的矛盾....................................96
10.魯迅的過錯還是時代的不幸?..........................................106
11.聞一多與王蒙:魯迅的「多」與「少」..................................111
12.所謂「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 119
13.表現自我,以魯迅為參照..............................................122
14.揚此抑彼,客觀上傷害了魯迅..........................................129
15.相對的無知者........................................................131
16.絕對的無知者........................................................136
17.變魯迅為工具........................................................137
18.小雜感..............................................................139
迫於時勢 .......................................................................143
被精神病 .......................................................................149
活的墳墓與行走的屍首.........................................................153
「暗暗的死」及其他............................................................156
「酷的教育」...................................................................160
「有運動而無文學」............................................................162
「流官」 .......................................................................163
正常與否 .......................................................................166
社會的與靈魂的................................................................168
知識與道德..................................................................... 170
晴雯是否也愛林妹妹............................................................173
蕭蕭落紅裡的基因密碼.........................................................177
阿Q下崗及教材變更............................................................182
拂袖而去與曲意逢迎............................................................198
魯迅與「憤青」及其他.........................................................204
魯迅的手稿包油條..............................................................209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212
文章不宜太像文章..............................................................215
兩株棗樹……...................................................................220
「褒貶」自有春秋..............................................................222
蕭伯納身邊的魯迅..............................................................229
狗的階級性.....................................................................232
貓的階級性.....................................................................239
「只會生孩子的階級」......................................................... 248
「拿貨色來看」................................................................252
「後死者的苦痛」..............................................................262
細瓷與地火.....................................................................273
關於魯迅與錢鍾書及其他.......................................................278
從狩獵到播種 ——《魯迅與他「罵」過的人》後記 .............................284
《魯迅與他「罵」過的人》新版自序...........................................289
關於《魯迅:最受誣衊的人》的一封信........................................298
魯迅門下走狗...................................................................307
宏觀反思 微觀透視 ——介紹張夢陽的《中國魯迅學通史》 ......................311
關於《精讀魯迅》..............................................................318
魯迅與「閩客」................................................................320
說「鳥」 .......................................................................324
雜感.............................................................................328
頑皮的小老頭................................................................... 330
「狗脾氣」.....................................................................336
魯迅當「官」...................................................................340
魯迅是怎樣當父親的............................................................345
魯迅的孫子賣爆米花............................................................354
嵇康為何而死?................................................................358
再談嵇康之死...................................................................364
「一統」情懷...................................................................376
魯迅「吃人」...................................................................379
短命的人 .......................................................................382
「托尼」之痛 ——魯迅的「內傷」 ..............................................386
肩住黑暗閘門的犧牲者.........................................................391
魯迅這座山.....................................................................396
魯迅之死 .......................................................................405
遷墓............................................................................ 428
無處逃脫 .......................................................................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