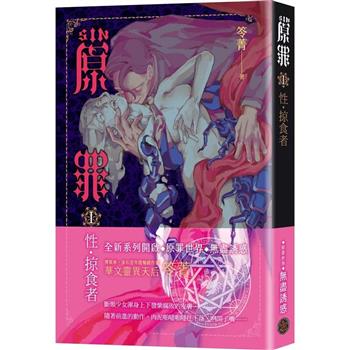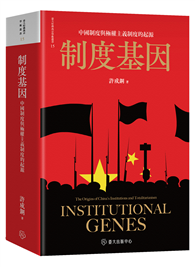學界有所謂「軟著陸」「硬著陸」之說。軟著陸意謂出自名門,或來自經院,一步一步沿著一條鋪滿了鮮花的路走向成功,猶如張開降落傘緩平著陸。而我卻是在高天飛機上,無任何倚仗憑藉,眼一開心一橫,就那麼赤條條地跳了下去,直落硬降!我以一個普通中學生,一跳而進紅學界,再跳而入文壇,都是在年將不惑時的勾當。我特別感謝馮其庸先生,貴為紅壇要津,我無任何奧援,一紙論文相投,納我進入紅學界,長驅直入為理事,取得文人資格,繼而又告我有寫小說之才分,堅我信心,又「硬跳」了文壇。我還要感謝我的責任編輯顧仞九先生,接納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生手,毅然將這部書推出世界,他的膽量識見不凡--我是想說,我有點像柏油馬路上突然長出來的蘑姑,自必是「怪」。
物反常即為怪。(康熙大帝)的出現看去是有些怪,但我可不願讓千百萬愛這書的讀者認為我是個不可思議的怪作家。假如這世上有人曾經始終和我同路跋涉過艱難人生。他就告訴你,我其實原來是個痴人。他會告訴你我是怎樣一個讀書狂,在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裡我不曾在凌晨一點半前睡覺,告訴你我曾被管理員遺忘關扣在圖書館中而不自知曉,告訴你我捧書走路,踢跳了腳指甲,血流殷道而渾然不覺。假如他看見我裁開包水泥的牛皮紙袋作卡片,一字一句地摘錄那些「劈柴」紋理,他就只能如實說「二月河不過是文壇一痴」。
人生就是這樣,像柳絮,又像汪浪中的水藻,有時會被機遇和命運拋到各種莫名其妙的環境中。可以離、可以合、可以悲、可以歡;可以華堂擊壺而歌,可以躺在煤堆上黑甜一覺;可以出入於冠蓋如雲之廊廡,亦可以蟄居幽處於僻壤寒谷--我用心走過來了。白居易「張空拳於戰文之場,策蹇步於利足之途」斯言不吾欺亦不汝欺。如此而已,「而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