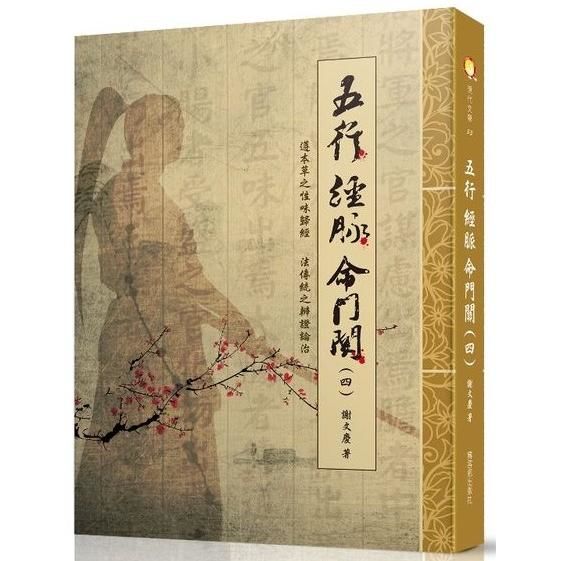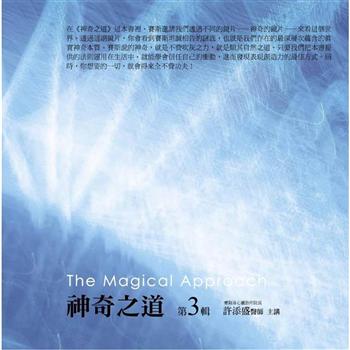第廿四回 聯外制內
眾鳥何啁啾,肅殺氣相遞,城郭方百里,阡陌景交替。本為白商素節,草木黃落之季,惟遇深秋天寒竄雜,金風玉露難免蕭瑟。坐觀中州瑞辰大殿,戶限為穿,文武眾臣,眾口囂囂,無不以待國師歸殿呈報。
薩孤齊一入殿堂,立對主公打躬作揖後,佇立廳中央,惟聞中鼎王嚴肅說道……
「一切訊息,始自東震大殿。國師舟車勞頓,隻身護送真經,功不可沒。然而真經之外,何以萌生枝節?甚而傷及友邦重臣?本王聞訊當下,暫以片面之詞視之。今見國師回殿,已是負責之舉,文武眾臣於此一聚,只為探得來龍去脈,盼國師詳實以述。」
「榮根此行東州,只為安全護送《五行真經》,故採低調行事。孰料身抵東州後,遇友邦之相對禮儀,不甚尊重!不僅不見軍機首長於港埠相迎,更指派一名不見經傳之年輕女子,上前鑑識真經之真偽,此等矮化我中州之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國師話說至此,眾臣嘩然,紛紛點頭,同表友邦失禮對待。
薩孤齊又說:「為此,榮根咬牙容忍,但不為中州爭口氣,實在辜負中鼎王對貧僧之拔擢與器重,遂臨時起意,提出東州須追加雙倍打撈計畫之材源,若能如願,即可減輕我中州之龐大支出。」
「雙倍材源?如此巨量,東州怎會輕易點頭?」財政大臣辜亦劻疑問道。
國師回應道:「凡為中州之福利,榮根絕對竭盡己能,全力力爭,遂以收回原始承諾為由,欲將《五行真經》帶回,並強烈表明,若友邦予以為難,榮根不惜與《五行真經》俱焚,雙方僵持一陣,終得到嚴東主首肯。為此,得有勞掌理財政之辜大人,為我中州緊盯友邦承諾!」
「好啊……真是大快人心啊!能讓吝嗇之嚴震洲點頭,惟我中州國師能也!哈哈……」中鼎王興奮道。
然此時刻,狼行山突然入殿,對中鼎王致敬後,立對國師問道……
「國師此行之回程倉促,行經濮陽而未予相告,直接夥同公主回往惠陽。先不咎國師此等禮數不周,難到真如東州所言,國師傷了友邦軍機大臣,以致亂了方寸,甚以潛逃方式歸隊,是否有損我方之國格?」
薩孤齊冷笑回道:「貧僧回濮陽時,並不見狼城主於府城坐鎮,聽聞狼城主因與一女子談笑暢飲而惹怒了公主,甚而離家不回。貧僧遂前去逸和苑慰問,巧遇公主有回返娘家之意願,遂偕公主前來惠陽。」
薩孤齊如此一說,隨即引來廳堂一陣嘈雜,且令中鼎王搖頭以對。
「還望國師尊重國是殿堂,勿藉私人家務而模糊焦點。然私人家務,倏可釐清,但以國師之身分,竟於友邦境內,出手傷人,此舉甚可引來雙方戰事,還請國師據實已告!」狼略顯不悅道。
薩孤齊微笑回道:「軍政內閣,匿藏內賊,直可動搖國基,啃蝕國本。然我中州之軍機與神鬣,猶如龍之雙犄,堅不可摧。孰料東州軍機屬下,良莠不齊,遂讓貧僧此行,感觸良多。話說,榮根於護送真經途中,聽聞火連邢教主,因私掘密道不慎,竟遭南州赤晶石所傷,現已呈腦寒瘖啞狀態。昔日貧僧曾隨世勛太子入洞麒麟,並無大礙,猜想,是否各州晶石窟,真有鬼魅?抑或不兆之說?故藉此行,向東震王提出前往青龍洞窟參訪之要求,倘若能有所發現,即可向中鼎王報備。」
國師接著又說:「孰料,當隨軍機總管曹崴入洞後,同行之軍機副總管余翊先,居心叵測,貧僧與曹總管論及邢教主事件時,巧見余翊先舉止詭異,有盜採晶石之嫌,怎料余惱羞成怒下,竟嫁禍於貧僧,甚對貧僧出手,貧僧出於自衛而回擊,遂引來曹總管護短,致使衝突擴大,一陣混亂中,曹總管竟使出了〈劈手鎮樁〉絕技以對!情急之下,貧僧深覺,若枉死於此,則個人與中州勢必蒙羞,故奮力一回擊,劈中了曹總管之左肩骨,待逃出洞口時,又見衛蟄沖將軍率兵前來,所謂好漢不食眼前虧,遂躍入了洞窟旁之山泉流水,順流逃離!」
軍機總管戎兆狁,接話表示,國師所言,頗為合理。惟聞屬下回報,東州確實對余翊先發出了緝捕令,其父余伯廉一如當年嚴東主處置嚴翃寬一般,表明與余翊先完全切割。倘若余翊先毫無嫌疑,為何畏罪潛逃?然而,東州視我國師之舉不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國師遂選擇直奔惠陽,對我中州核心表明實情。
「好,國師為不使中州蒙羞,機警以對,化險為夷,值得嘉許,故賞賜白銀百兩,以為犒賞。」中鼎王又說:「惟因中、東二州尚有合作計畫,故誤會不宜渲染與擴大。倒是今早南區都衛水師罕井紘軍長傳來,探勘船似乎覓得了些古船殘骸,此聞之於打撈計畫,無疑是劑強心針,為此,我中州暫不宜與東州起衝突;倒是嚴東主願意再提供雙倍材源,中州必須做出善意回應!即日起,增加輸往東州之五穀及釀酒數量,並獨降東州相關稅收,應可平息此一風波。」
待國師與諸臣一一離席,薩孤齊仍不放心地回顧了一下,僅見中鼎王上前拍了拍狼行山肩膀,猶有說教意味,遂於睥睨一笑後離開了大殿。殊不知,狼行山正對著中鼎王提議,立馬召集戎兆狁總管與神鬣門刁總督,並前往殿後議室一聚。孰料此一聚會,竟使議室徹夜燈火,通宵達旦!
翌日,狼行山睡眼惺忪地走在承豐大街,心想著,「唉……國事雖如麻,終究易於家務之釐清啊!嗯……還是得向婕兒說清楚才是。對,回雷王府好好地解釋才對。」適值此念頭閃過腦海之際,遠處隱隱呈現之一幕,霎令狼行山一陣腦麻,「那……那是……」驚見一對男女自群瓏客棧走出,背對著狼行山,雙雙上了二馬背,不待狼行山追上,二人隨即馭馬,俄而奔離了承豐大街。
頓時一陣錯愕之狼行山,嘴裡直唸:「不可能!婕兒怎可能會……」
原來,狼行山所見二人,一乃自個兒妻室雷婕兒,另一則是燒成灰都識得出之……樊曳騫!
「這……這太不像話了!」雷嘯天聞狼行山敘述後,於王府大廳咆哮道。
雷夫人隨即酸言道:「怎麼?那女婿私會舊情人不就該死啦!婕兒甫回濮陽,怎知咱們那寶貝女婿,尚與那姓蔓的藝妓瞎混,所幸遭婕兒逮個正著,否則,咱們至此還矇在鼓裡嘞!」
「蔓姑娘她……她只是個曾救過我之好友,況且她……」正當狼行山說著,雷婕兒回到了王府。
「阿爹、娘,瞧這野兔,女兒的箭術還不錯吧!哦……狼城主回惠陽啦!有啥事兒比密會蔓晶仙重要啊?哼……」婕兒又說:「過往僅是見著阿爹於叢林獵鹿,真沒料到,原來打獵這麼好玩兒啊!哇……還真覺累了,女兒回房歇著啦!」
雷嘯天見婕兒走了後,推了阿山一把,「快……快追上去啊!」待狼行山離開後,突然!「呃啊……我的頭!」雷王瞬間頭疼發作,隨即服了狼行山留下之「苛依松」,咬牙說道:「難道……真如法王所說,吾之腦袋須剖開,才得祛這頭疼?」
「若此藥丸兒能止疼,咱們再想想其他法子,或許坊間名醫有解。」夫人又說:「對了,聞薩孤齊提及,當日為東震王鑑識真經之年輕女子,即是替東震王診治肝疾者,名曰龐鳶!」
「龐鳶?真是她!」雷王面露訝異,又說:「日前聞展鵬與岑鴞回報,曾於北渠發現惲子熙行蹤,後因一身懷絕技,名曰龐鳶之女子出現,致使二人無功而返。難道……會是同一人?嗯……得差人仔細打探一下。」
忽然!由西廂房傳來爭吵聲響,雷嘯天不禁搖頭嘆氣,唸道:「這麼吵下去,咱們何時才能抱孫啊?」
數日之後,狼行山牽著雷婕兒於市集閒逛,此回反由遠處瞧他倆動作親暱者,即是置身客棧露台,獨飲悶酒之……樊曳騫!然此時刻,一人突然搭了下樊將軍肩膀,轉身坐了下來。
「怎麼啦?樊將軍一人獨飲,不悶啊?瞧您一副艴然不悅樣兒,貧僧直覺……同令咱們咬牙者,應是同指一人才是。」
「啊!不知國師來到,真是失禮了。」樊曳騫接著又問:「聞國師之說,莫非……國師亦與那姓狼的……結過樑子?」
「自從狼行山登上駙馬爺後,干涉了中州諸多朝政;狼之思維與行徑,幾與貧僧背道而馳。貧僧此回於濮陽城,見狼駙馬私會一蔓姓女子!想想,老天爺實在太眷顧他了,世間若干好處,怎盡歸狼行山所享嘞?所以,只要除了咱們眼中釘,以樊將軍之資歷與才能,何以不能頂替狼行山?」
「如此說來,國師可有良計可施?」樊好奇道。
接著,薩孤齊拿出了蔓晶仙所遺之小橫笛,並對樊曳騫詳述了一套未來計策。
數日後,薩孤齊佯裝巧遇狼行山,惟因曾於殿堂道出了狼之家務,遂客氣地對阿山表示歉意。阿山本不欲與國師多聊,待薩孤齊一提「蔓晶仙」這三字,霎時吸引狼行山之注意。薩孤齊表示,之前自東州回程時,雖見倉促,卻於近濮陽東城門時,見過蔓姑娘含淚朝向廣濱埠,而後登船前往了東州。待貧僧進濮陽城後,因遍尋不著狼城主,遂聞了城主於嵩安客棧發生之事兒;只因公主性格火爆,故能體會駙馬爺當時心情。又說:「然於殿堂上,因狼駙馬質疑了貧僧行徑,故僅以簡單解釋帶過,還望駙馬爺莫擱在心上。」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五行 經脈 命門關(四)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5 |
小說/文學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武俠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7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五行 經脈 命門關(四)
博客思出版武俠系列~~《五行經脈命門關(四)》
武俠小說為經 中醫脈絡為緯
見識武俠新風貌~~
世間任一門學問,皆有其基礎之學以至繁複深奧,一如數學可及高等之微積分,惟處理生活瑣事,卻僅需小學之加減乘除即可;同理,醫學領域亦有其基礎常識可習。本著作之內容鋪陳,即以常見之外感病與臟腑病,對應《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針灸大成》等重要醫經,藉以領略中醫之辨證論治!然為使故事發展不致脫鉤人體臟腑,筆者自創五向之於五州域,以對應五行與五臟,且隨故事之發生區域,順勢提及該臟腑之相關證候與療法,並以歷代之傳世名方,引人熟悉中醫醫書之描述語法,更藉故事諸角色之身擁武藝,讓讀者於潛移默化中,識得周身之十二經脈,甚是奇經八脈,以期能藉此著作,習得五行與經脈之概說,順勢引領讀者踏入中醫之基礎領域。
博客思出版武俠系列~~《五行經脈命門關(四)》
作者簡介:
謝文慶,淡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畢業,曾任新竹科學園區聯合光纖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系統工程師,後創立梵亞實業有限公司,從事耐久建材之代理銷售。歷經科技與勞作數載以至年逾不惑,突感人體臟腑奧妙,遂研習五行經脈與傳統醫經藥理,不僅領略一針一草以療病之藝術,更受惠諸聖先賢之經驗累積,故戮力推助中醫之美,以入人心。
章節試閱
第廿四回 聯外制內
眾鳥何啁啾,肅殺氣相遞,城郭方百里,阡陌景交替。本為白商素節,草木黃落之季,惟遇深秋天寒竄雜,金風玉露難免蕭瑟。坐觀中州瑞辰大殿,戶限為穿,文武眾臣,眾口囂囂,無不以待國師歸殿呈報。
薩孤齊一入殿堂,立對主公打躬作揖後,佇立廳中央,惟聞中鼎王嚴肅說道……
「一切訊息,始自東震大殿。國師舟車勞頓,隻身護送真經,功不可沒。然而真經之外,何以萌生枝節?甚而傷及友邦重臣?本王聞訊當下,暫以片面之詞視之。今見國師回殿,已是負責之舉,文武眾臣於此一聚,只為探得來龍去脈,盼國師詳實以述。」 ...
眾鳥何啁啾,肅殺氣相遞,城郭方百里,阡陌景交替。本為白商素節,草木黃落之季,惟遇深秋天寒竄雜,金風玉露難免蕭瑟。坐觀中州瑞辰大殿,戶限為穿,文武眾臣,眾口囂囂,無不以待國師歸殿呈報。
薩孤齊一入殿堂,立對主公打躬作揖後,佇立廳中央,惟聞中鼎王嚴肅說道……
「一切訊息,始自東震大殿。國師舟車勞頓,隻身護送真經,功不可沒。然而真經之外,何以萌生枝節?甚而傷及友邦重臣?本王聞訊當下,暫以片面之詞視之。今見國師回殿,已是負責之舉,文武眾臣於此一聚,只為探得來龍去脈,盼國師詳實以述。」 ...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中醫之傳經送寶,西醫之透視剖析,或可以兩大門派視之,而少以信仰待之!只因門派可相互切磋、取長補短,始能求精求實;但若持以信仰觀念,則易生區隔與排斥,甚因堅信一方,枉失了對證療治之良機。然而,門派各有所持,始能區分特色;倘若以「楚河、漢界」為棋盤之分野,中醫別於西醫之最大特色,則非「五行、經脈」莫屬,且指出「命門」乃生命之始,甚為壽終火熄之處!依此特點,遂令著作直取「五行 經脈 命門關」為名。
年逾不惑之後,心生疑問,何為「臟腑」?
走過四十寒暑,自知對皮裡肉下之常識薄弱,遇身體不適,就醫服藥,縱然...
年逾不惑之後,心生疑問,何為「臟腑」?
走過四十寒暑,自知對皮裡肉下之常識薄弱,遇身體不適,就醫服藥,縱然...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導讀
第廿四回 聯外制內 一0
第廿五回 三陽淬礪 七二
第廿六回 追本溯源 一三二
第廿七回 誅凶殄逆 一九五
第廿八回 滅景追風 二五四
第廿九回 烏集之交 三一六
第 卅 回 發奸擿伏 三七六
第廿四回 聯外制內 一0
第廿五回 三陽淬礪 七二
第廿六回 追本溯源 一三二
第廿七回 誅凶殄逆 一九五
第廿八回 滅景追風 二五四
第廿九回 烏集之交 三一六
第 卅 回 發奸擿伏 三七六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