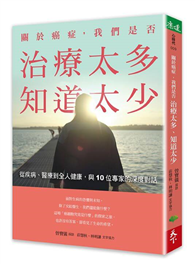去到那裡之前,就只是一般的案件採訪。
大宮的KTV。
這是我第一次踏入的店。穿過週五夜晚鬧區震耳欲聾的喧囂,我們找到了坐在路邊的金髮女生告訴我們的那家店。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KTV大樓。狹小的通道迴響著客人抓著麥克風嘶吼的歌聲,吵鬧的打拍子聲無止無盡。我們在一臉訝異的店員帶領下,穿過通道進入那個包廂,隔著小桌在沙發坐下。我一邊坐下,眼角餘光掃見店員反手帶上門口的廉價門板。我的視線瞥著只差幾公分就完全闔上的門板最後的動作,下一瞬間卻被坐到對面的青年嘴唇動作給吸引了。那名壯碩的青年劈頭第一句就說:
「詩織是被小松跟警方殺死的。」
我的屁股都還沒完全坐下。
一定就是在這一瞬間,我的心中有什麼改變了……
案件的第一波報導總是一團混亂。
這起命案也不例外。最早接到的消息是「隨機砍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這天我任職的《FOCUS》編輯部休假。我早就決定要好好睡個懶覺。前天我幾乎整天沒闔眼。為了趕截稿,我近乎熬夜地寫完稿子,看過清樣,結束稿件的最後確認後,還參加會議之類的,一眨眼就入夜了。當然一回到家,往床上一倒,立刻不省人事,醒來的時候都已經中午了。生活在正常時間帶的家人老早便展開各自的日常,空蕩蕩的家中,就只有寵物金倉鼠「之助」在籠子裡跑來跑去的沙沙聲。久違的悠閒的一日即將開始。
也有許多雜務等著我去處理。得去洗衣店取到現在都還沒領回來的夏季外套。讓「之助」放個風,打掃一下牠的小窩吧。我猶豫該從哪件事著手,決定清掃倉鼠籠,伸手拿出籠中的飼料碗時──
手機響了。
開端總是手機。對社會記者來說,手機就像恐怖的項圈。
或許會是總編以莫名沉著的聲音說:
「發生大地震了,你立刻趕去現場。」
也有可能是同事打來的:
「那起命案的兇手落網了!現在要被帶去警署了!」
或許是其他報社認識的記者:
「警方終於對XX進行搜索了!」
甚至有可能是來提供線報的:
「我家附近有人養的巨蟒逃走了!」
什麼都無所謂,是誰都沒關係,反正手機響了,就是工作上門了。我按下通話鍵,不祥的預感幾乎變成了事實。
「清水兄,不好意思在你休假的時候打擾!」
不出所料。就算猜中,也教人開心不起來。是編輯部攝影師櫻井修的聲音。
「有消息說埼玉桶川站附近有個女人被殺了。似乎是隨機砍人。」
我忍不住嘆息。我跟櫻井前前後後已經共事將近十五年了,他是我最為信賴的同事之一,北至北海道,南至沖繩,我們共同採訪的案件、事故、災害多不勝數。搞不好比起我太太,他更要了解我。他非常清楚在採訪中落後的記者會有多遜,所以應該是出於好意通知我,但這也是我好不容易才盼到的安息日,坦白說,真希望他放我一馬。
「……你一個人嗎?」
「大橋也正在趕去現場。」
大橋和典是編輯部的年輕攝影師。
「意思是這個案子我負責?」
「不,山本總編沒說什麼……」
這表示接到指示的只有攝影師。對攝影週刊來說,照片就是一切。總編山本伊吾應該是打算先派攝影師過去,能拍到什麼就先盡量拍。我這個記者就算裝做沒事人,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不過事情落到我頭上,也是遲早的事。所以櫻井也才會打給我。《FOCUS》編輯部沒有幾個記者會分派到這類稱為「搜查一課(譯註:日本的警察機關裡,通常搜查一課負責的是殺人、強盜、傷害、綁架等重案。)案」的採訪。要是我繼續留下來給倉鼠放風,到時候要扛起採訪落後的責任的,可是牠的飼主。就在我猶豫躊躇、揮舞著倉鼠飼料碗的這一瞬間,已經展開採訪的其他記者應該正不斷地蒐集到各種消息。下個星期,應該就可以在書店看到他們比我更詳盡許多的報導。
是要現在享樂,事後付出可怕的代價,還是立刻工作,分期處理掉麻煩?多歡樂的選擇題啊。我是個勞碌命,沒有選擇的餘地。
「……兇手呢?」
「完全沒有眉目。我也是剛接到編輯部的消息,離開家而已。」
「……那,我這裡稍微調查一下。」我想我的聲音應該變得很陰沉。再怎麼說,案件報導講求的是速度。這一點我也再清楚不過。但難得休假一天,才剛起床二十分鐘就泡湯了。我右手握著掛斷的手機,左手拿著倉鼠的飼料碗,喃喃自語:
「幹麻好死不死,偏偏挑在今天發生……?」
但是,接下來我將深刻感受到這起命案不能以今天或明天這樣的單位來看待。漫無止境且遙遙無期的採訪,就此揭開了序幕。
我立刻著手打電話。
任何採訪都一樣,第一步是蒐集資訊。就算糊里糊塗地衝到現場也無濟於事。雖然心急如焚,但與其不清楚天候就航向驚濤駭浪的大海,最起碼也要先在港口踢一下木屐占卜一下天氣(譯註:日本有踢木屐占卜天氣好壞的習俗。口中說著「希望明天好天氣」,踢出套著木屐的腳,一般認為掉下來的木屐呈正面就會是晴天,反面就是雨天。)再做打算。這種時候,要先打電話給平日就有交情的同行記者,或是查閱通訊社的新聞快訊之後再出擊。
我從採訪用的斜肩包裡取出筆電,雙手敲打鍵盤,一邊查閱快訊,一邊用肩膀夾著電話,開始蒐集資訊。一旦開始行動,便勢不可擋。為了這種時候,我的熱鍵登錄了將近四百支電話號碼。我一通接著一通,不停地打。
「聽說桶川發生命案,你們派記者過去了嗎?我也正要過去……」我一面表明自己也將加入戰局,向各方向打探消息。
詢問多位報社記者、電視台人員後,不到十分鐘,回撥的電話便愈來愈多,也有已經開始採訪的其他報社及電視記者聯絡我。電話中接到插撥,接起來後又是插撥,忙得簡直像航空管制員,我這個舊型十六位元的大叔腦幾乎快要處理不過來了。
初期資訊很零碎。
匆促寫下的便條紙上填滿了我雜亂的字跡。被害人女子是住在桶川市隔壁上尾市的女大生,豬野詩織,二十一歲。案發地點在JR高崎線桶川站的正前方,屬於上尾警察署的轄區。刺死人的男子目前在逃,警方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花上三十分鐘從四面八方蒐集到的資訊,整合起來就只有這樣。總之是掌握到案件的骨幹,知道是住在哪裡的什麼人,在何處遭到什麼樣的傷害了。行動前就能掌握5W1H的狀況可以說是寥寥無幾,能知道這些已經是萬幸了。
我直接穿著身上的牛仔褲,抓起褐色外套,搭上背包,衝出家門。
前往現場的交通工具,是我自己的四輪驅動車。這也是我還是報導攝影師時留下的紀念,不過在採訪事件時,最重要的是盡速抵達。如果搭電車更快,就搭電車;搭飛機更快,就搭飛機,完全不考慮距離和費用。過去我曾為了搶先五分鐘而風光得意,或為了落後五分鐘而頓足懊惱。這起命案,最恰當的選擇是車子。如果遇到塞車,就隨便找個停車場丟下車子,改搭電車,如果接下來還需要車子,在現場攔計程車或租車就行了。
十八年來,我一直站在「第一線」。在腦袋思考之前,身體會自己先行動起來。我衝出家門,跳上車子,把背包扔到後車座。腦中描繪出前往桶川的路線,轉動鑰匙發動引擎。打開車用電視的開關,把車開出去。從衝出家門到開出車子,應該花不到五分鐘。
我將手機設定為免持擴音,一邊開車,一邊打給櫻井說明狀況。
「要怎麼安排?」櫻井問。
「你在現場拍攝『雜感』。如果有警方鑑識人員就拍進去。大橋在上尾署外面待機,為兇手落網的時候做準備。」
「了解。」
「現場拍完後,你也去上尾署。」
「沒問題。」
彼此都很熟悉對方的行事風格了,不必詳細討論。
我任職的是攝影週刊,因此攝影師的安排是最優先事項。今天應該確保的,首先是現場的照片,再來是如果有記者會,就是警方記者會的照片,若兇手落網,當然就是落網時的照片。我請櫻井拍攝現場,大橋到警署外守候,櫻井拍完現場後,就可以轉去拍攝記者會。報導需要的照片每次都不同,只能依照案情和規模、發展來判斷。這次因為事前已經蒐集到一定程度的訊息,所以攝影師的安排也很順利。
路況通暢,感覺是個好兆頭。不過移動期間,腦袋也不能放空休息。我用眼角餘光留意車用電視畫面,腦中模擬抵達現場後該做的事。要做的事堆積如山。決定要採訪哪些對象、請求支援、安排攝影師……
總之,已經發生的案件採訪,動作最快的人就是贏家。弄錯步驟將會帶來致命傷。採訪對象會被他社記者打攪,受訪者愈來愈不願意開口,假裝不在家,或銷聲匿跡。甚至是寶貴的資料被其他記者搶走,相關人員串證,有時甚至還會捏造出不在場證明……。雖然不願意想像,但這就是現實。
車用電視開始播報新聞。「十二點五十分左右,桶川站前的人行道發生一起持刀殺人命案。死者為住在上尾市的二十一歲女大學生,豬野詩織……」距離現場還有一段路程。我握著方向盤,在腦中記下「十二點五十分」這個時間。「死者豬野前往車站準備搭車去大學上課……」、「死者豬野正要停下自行車,一名男子從後方靠近,首先持刀刺入她的背部,接著刺向胸口……」播報聲片斷傳入耳中。我將這些也全部輸入腦中。雖然不管怎麼樣都必須直接採訪,但最好先把握該前進的方向。
目擊者的證詞也立刻播出來了。「我聽到有人大叫:『哇!好痛!』」回答記者採訪的是現場附近的店員。店員聽到叫聲,跑出店裡,看見一名男子跑走的背影。人行道上倒著一名女子,店員說:「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停切換頻道,將看似有關的資訊全部記在腦裡。「警方不排除隨機砍人的可能性……」聽到男主播的聲音,我切實地感受到果然各家媒體都傾巢而出了。但是另一方面,卻也有一股怪異的感覺。
我知道為什麼媒體會爭相報導這起命案。
這樣說或許不好聽,但殺人命案本身,日本各地每天都在上演,所以並不是每一起命案都會受到媒體大篇幅報導。
人命不可能有貴賤之分,原本不管任何人怎麼樣遇害,都是重大事件,但現實上,不同的命案,世人的關注程度也不同。是因為媒體報導,所以民眾關注,還是因為民眾關注,媒體才大肆報導?我不知道。
不過,只要看看各家媒體對這起命案的第一波報導的標題「女大生被當街刺死」、「隨機砍人?女子被刺身亡」,就可以知道媒體矚目的要素是什麼。關鍵字是「年輕女子」、「隨機砍人」。
「年輕女子」不必特地說明,令我在意的是「隨機砍人」。
近年來,隨機砍人事件頻傳,甚至有報紙提到,如果說九八年可以用「毒物列島」(譯註:一九九八年,日本和歌山發生一起毒咖哩事件,祭典中的咖哩遭人摻入砒霜,造成四人死亡,多人送醫。此後日本各地陸續發生在食物摻入毒藥的模仿犯罪。)來形容,那麼九九年就是「連環隨機砍人」。就是陸續發生了這麼多起與兇手非親非故的一般民眾慘遭殺害的事件。只要發生轟動的大案子,就會引發一連串類似的模仿案件。若是二○○○年,應該可以稱為「十七歲的犯罪」吧(譯註:二○○○年前後,日本連續發生多起年約十七歲的青少年所犯下的凶殘犯罪,如五月的西鐵巴士劫持事件等,讓「十七歲」一詞甚至成為該年度的流行語大獎候補。)。媒體關注的模式就是如此。
在東京池袋鬧區,一名男子砍傷路人後,四處奔跑並以鐵鎚毆打逃走的民眾,遭到逮捕。
從羽田飛往札幌的全日空班機,遭到熱愛模擬飛行的男子攜帶刀械進入機艙劫機,並殺害機長。
山口縣下關市,一名男子開車衝進車站,揮舞菜刀追砍民眾。
我本身就參與了池袋與下關兩起隨機砍人事件的採訪。下關的事件,我三星期前才剛寫過稿子。
這名三十五歲的菁英分子兇嫌十分謹慎,作案前還預先到下關站裡面勘查過環境。他到租車行租下用來衝進車站的車子時,特別指定要小型車,並在車站附近購買菜刀,然後從站前圓環的出口開車衝上人行道,犯行充滿計畫性。他接連撞飛女高中生,衝進車站大廳,直到驗票口前才停下車來,下車後面露猙獰的笑,握著菜刀翻進驗票口裡面……
毫無意義的殺戮。遇害的人毫無救贖可言。如果被害人有任何過錯,他們唯一的錯,就是相信這個「社會」是安全的,在那一瞬間身在那個地點。
站前、隨機、砍人……。桶川的命案,讓人聯想起這一連串事件。
但,我的思考隨著車子在紅燈前停了下來。這起命案是否有些不同?
隨機砍人事件的受害人,大半都是跑得慢的老人或小孩。但這次的死者是年輕女子,而且只有一個。就是這一點讓我覺得似乎有些不對勁。
為什麼選擇年輕女子?為什麼只砍殺一個人?
| FindBook |
有 18 項符合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6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
第一次死於兇手的刀下;
第二次是被見死不救的警方殺死的;
第三次是被見獵心喜的媒體殺死的。
她生前的求救吶喊,一直沒人聽見。
是什麼樣的社會,讓一名普通女性求救無門,慘死於眾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
又是什麼樣的黑暗,讓一名平凡的週刊記者,決心和國家權力與眾多同業站在對立面?
本書特色:
★榮獲日本新聞工作者會議大獎、日本編輯嚴選雜誌報導獎
★引發日本電視台深入專題追蹤,全日本注目並催生反跟蹤狂法案!
★被譽為「記者的教科書」,日本報導文學的扛鼎之作!
★長踞日本亞馬遜網路書店排行榜高位,日本讀者★★★★☆震撼推薦!
★你絕對會希望身邊的每一個人都看過的一本書!
王立柔(前《報導者》文字記者)
李屏瑤(作家)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臥斧(文字工作者)
胡晴舫(作家)
神小風(作家)
張亦絢(作家)
張茵惠(MPlus主編)
蔡宜文(作家)
陳又津(小說家)
陳珊妮(創作歌手)
楊子磊(攝影記者)
董成瑜(《鏡文學》總編輯兼總經理)
蔡宜文(作家)
賴瑩真(律師)
螺螄拜恩(暢銷書人氣作家)
--誠摯推薦
「如果我被殺了,那就是小松殺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僅二十一歲的女大學生豬野詩織,
遭人於日本埼玉縣JR桶川站外刺殺身亡。
豬野詩織生前向朋友訴說,自己不斷遭到前男友小松和人的暴力恐嚇與跟蹤騷擾。
不願意和詩織分手的小松,總是將能夠簡單蹂躪殺害詩織的話語掛在嘴邊,
逼迫詩織聽從自己。
不肯坐以待斃的詩織,決心前往埼玉縣警轄下的上尾署報案,
卻被警方以不介入民事糾紛的藉口,給拒於門外。
詩織只能將與小松交往過程中的遭遇完整告訴好友,
並將留給父母的遺書藏在房間角落。
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年輕女性遭到殺害。
詩織的死亡引起媒體矚目,週刊記者清水潔也加入採訪行列,
在一路遭擋碰壁的追訪過程中,他自覺冥冥之中有股力量讓他聽見了詩織的遺言。
透過縝密的調查、漫長的跟監,清水調查出詩織前男友小松的真實身分、
比警方更早鎖定兇手,掌握案發後即下落不明的小松行蹤……
清水起先認為這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社會案件採訪,
沒料到竟會踏上一段平凡人為平凡人討公道的孤寂旅程──
●相信警方能保護人民是我們的錯嗎?
比上百名刑警更早鎖定兇手,暴露日本警方嘲弄被害者的吃案醜態。
●當新聞媒體不再是揭露真相的正義之聲
批判依附國家權力生存的主流媒體,拒絕被害者一再遭受汙名化!
●過著平凡日子的你我都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
當親密關係成為撼動社會的恐怖慘案,催生《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
凶案悄然落幕二十年,但我們還能拯救二〇一九年的豬野詩織。
對本應保護人民,竟棄人民於不顧,
甚至試圖壓迫人民噤聲的警察機關提出嚴厲批判;
對本應傳達正確訊息,卻只在乎收視率及銷售量,
不惜扭曲被害者形象的媒體提出尖銳質疑。
事件真相揭露以來,撼動著一個又一個日本讀者,
清水潔孤獨卻執著的追尋,促使日本政府在二〇〇〇年通過《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
而距離桶川案二十年後的台灣,
我們同樣面對著因為缺乏情感教育,頻頻發生跟蹤狂犯罪的現況;
也同樣面對著只在乎數字,不在意事實的媒體。
此時閱讀清水潔這本充滿對被害者的同理心,及對記者生涯的自省之作,
將會是敲醒我們心中之門的一記警鐘。
【各界迴響】
我相信大多人聽到或閱讀桶川事件的資料時,
都會對兇嫌的所作所為感到憤怒,也不認為他的做法是正確的,
但兇嫌敢發出「散布強姦影片」的威脅,正代表他有自信有人將替他撐腰。
他很靠勢,靠的不是他的小弟,他的金錢,也不是他的麻吉和親戚,
而是千千萬萬個面孔模糊,在平常生活裡可能都被稱為「好人」的平凡百姓。
我們一定都有對電視機裡各種犯罪案件痛罵的時刻,
但有沒有一時半刻停下來思考過,
某些傷害能夠被創造出來,被賦予破壞力,其中有多少是眾人授權?
--前《報導者》文字記者王立柔推薦序節錄
調查報導並非靈感乍現,然後華麗轉身獻上意外撞上的內幕。
調查報導是日積月累的耕耘,它來自勤奮的跑線與探訪,
甚至得埋首在枯燥的公文與判決書裡,拉出不尋常的線索。
清水潔就是這樣的一位記者,手機不離身,總是第一時間衝到現場。
他不滿主流媒體對政府機關訊息的照本宣科,
從眾人不假思索的「隨機殺害年輕女人」社會案件裡,
發現日本女性面臨情感報復後的孤立無援,
而真正該負責的不只是兇手,還有怠惰輕忽的警方。
清水潔在扭曲的新聞風向裡,試圖爬梳真相。
他告訴讀者,獨立思考和不輕信的重要,
也讓我們知道,調查報導這門課,是一門腳踏實地的技藝。
--《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
法律並非道德底線,
面對假新聞刺激民粹,也不要輕易放棄關於正義的思辨!
──陳珊妮(創作歌手)
這個日本版的《預知死亡紀事》,沒有華麗的技巧與文學的野心——
但它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帶來震撼。最使我百感交集的,是那份近乎傻氣的樸實,
我彷彿聽到作者清水潔在說:她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如果只是用「人對人的在乎」,我們可以走到多遠?
權力機構的歧視與失格,導致平凡人為平凡人討公道。
悲劇在最初,看起來是如此微不足道。
全書幾無術語與理論,然而,但凡不識「制度失靈」或「親密暴力」者,
必能從這部寫實的守護性命之作,得到啟發與借鏡。
──張亦絢(作家)
漫長且寂寞的追查,鍥而不捨的態度,才能成就正義。
──賴瑩真(律師)
清水潔雖自嘲為受人鄙夷的週刊記者,但透過此書,
他揭示了記者如何在社會新聞的採訪中讓被害人免於輿論成見的二次傷害,
並在追查真相的基礎上勇於挑戰公部門的陳腐,
進而讓弱勢者的處境得以被社會重視,最終促成了法律的修改。
──楊子磊(攝影記者)
作者簡介:
清水潔
1958年生於東京。日本知名調查記者。曾為新潮社《FOCUS》調查記者,現為日本電視台報導局記者、解說員。以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的調查報導獲得日本新聞工作者會議(Japan Congress of Journalists)大獎以及編輯嚴選雜誌報導獎。2014年以《殺人犯還在外面──遭到掩蓋的北關東女童連續殺人案》獲得新潮紀錄大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譯者簡介:
王華懋
專職譯者,譯有數十本譯作。近期譯作有《今晚,敬所有的酒吧》、《便利店人間》、《無花果與月》、《戰場上的廚師》、《花與愛麗絲殺人事件》、《破門》、《一路》、《海盜女王》等。
譯稿賜教:huamao.w@gmail.com
章節試閱
去到那裡之前,就只是一般的案件採訪。
大宮的KTV。
這是我第一次踏入的店。穿過週五夜晚鬧區震耳欲聾的喧囂,我們找到了坐在路邊的金髮女生告訴我們的那家店。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KTV大樓。狹小的通道迴響著客人抓著麥克風嘶吼的歌聲,吵鬧的打拍子聲無止無盡。我們在一臉訝異的店員帶領下,穿過通道進入那個包廂,隔著小桌在沙發坐下。我一邊坐下,眼角餘光掃見店員反手帶上門口的廉價門板。我的視線瞥著只差幾公分就完全闔上的門板最後的動作,下一瞬間卻被坐到對面的青年嘴唇動作給吸引了。那名壯碩的青年劈頭第一句就說:...
大宮的KTV。
這是我第一次踏入的店。穿過週五夜晚鬧區震耳欲聾的喧囂,我們找到了坐在路邊的金髮女生告訴我們的那家店。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KTV大樓。狹小的通道迴響著客人抓著麥克風嘶吼的歌聲,吵鬧的打拍子聲無止無盡。我們在一臉訝異的店員帶領下,穿過通道進入那個包廂,隔著小桌在沙發坐下。我一邊坐下,眼角餘光掃見店員反手帶上門口的廉價門板。我的視線瞥著只差幾公分就完全闔上的門板最後的動作,下一瞬間卻被坐到對面的青年嘴唇動作給吸引了。那名壯碩的青年劈頭第一句就說:...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平凡人也能選擇的善良或邪惡--王立柔
前言
第一章 案發
第二章 遺言
第三章 鎖定
第四章 偵辦
第五章 逮捕
第六章 成果
第七章 摩擦
第八章 終點
第九章 餘波
後記
補 遺 遺物
文庫版後記
前言
第一章 案發
第二章 遺言
第三章 鎖定
第四章 偵辦
第五章 逮捕
第六章 成果
第七章 摩擦
第八章 終點
第九章 餘波
後記
補 遺 遺物
文庫版後記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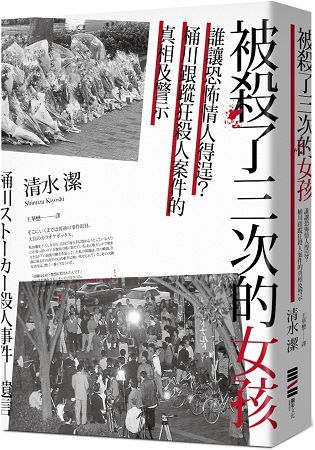
 2021/06/13
2021/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