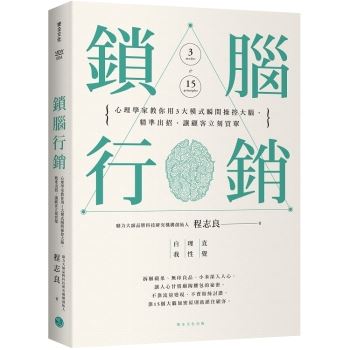港口上方的天空是電視收播頻道的顏色。
「不是說我有在用,」凱斯(Case)聽見有人這麼說;他正用肩膀頂開擠在「喳呼」(Chat)旁的人群,從中間穿過。「比較像我的身體自己生出嚴重的藥物缺乏症狀。」蔓生(Sprawl)口音說著蔓生區的笑話。喳呼的正式名稱是 茶壺酒吧(The Chatsubo),專為外國專業人士而設;在這裡喝上一週也聽不見兩個日文字。
照料吧檯的是瑞茲(Ratz)。他往一托盤的玻璃杯倒入麒麟生啤酒,義肢手臂單調地抽動。他看見凱斯後微笑,露出一口混雜東歐鋼與棕色蛀痕的牙 。凱斯在吧檯找到位置坐下,一邊是朗尼‧左恩(Lonny Zone)旗下妓女那不太真實的日晒膚色,一邊是高挑美國人身上俐落的海軍制服;這位軍人的顴骨明顯隆起一道道部落紋面。「維吉(Wage)剛剛有來,帶著兩個混混 。」瑞茲用完好的那隻手把一杯生啤酒滑過吧檯。「可能想找你,凱斯?」
凱斯聳肩。右邊的女孩咯咯傻笑,用手肘輕輕推他。
酒保的笑容加深。他的醜陋已進入神話範疇。在這個可用金錢換取美貌的年代,像他這樣缺乏美感的外貌,頗有某種紋章般的效果。他伸手拿另外一個杯子時,骨董手臂嘎吱作響。那是俄國軍用義肢,具備七功能力回饋操控器 ,包覆在骯髒的粉色塑膠下。「你可是大師中的大師,凱斯先生 。」瑞茲咕噥;這對他來說就算笑聲了。他用粉色爪子搔了搔白色汗衫下突出的肚腩。「在那種有點好笑的勾當裡,你可是大師。」
「沒錯。」凱斯啜了口啤酒。「總得有人負責搞笑,但他媽肯定不是你。」
妓女的咯咯笑聲拔高八度。
「也不是妳,姊妹。所以滾邊去,好嗎?左恩和我私底下關係很好。」
她看進凱斯眼裡,幾不可聞地啐了一聲,嘴脣幾乎沒動。但她乖乖離開。
「老天。」凱斯說。「你開的是妓院嗎?男人連好好喝杯酒都不行。」
「哈。」瑞茲用一條抹布擦拭疤痕累累的木酒桶。「左恩會分紅。我讓你在這裡工作,是因為娛樂效果還不錯。」
凱斯拿起啤酒,這時酒吧陷入一陣異樣的寂靜,彷彿一百個互不相關的對話竟來到同一個停頓點。接著那名妓女又發出歇斯底里的咯咯笑聲。
瑞茲哼了一聲,「天使剛剛經過。」
「中國人。」一名喝醉的澳洲人大發議論。「神經接合他媽就是中國人發明的。隨便哪天,給我到大陸做一場神經手術 ,把你弄到好,老兄……」
「聽這話,」凱斯對著自己的酒杯說,苦澀之意忽然如膽汁般一湧而上。「可真是狗屎啊。」
日本人放掉的神經手術技術遠比中國人曾掌握的還多。千葉的地下診所極為先進,每個月都有人換上完全以工藝技術打造的身體,他們卻沒辦法修復他在曼非斯(Memphis)那家旅館所受的損傷。
在這裡待一年了,他還夢想著網際空間(cyberspace),但希望夜夜消逝。無論他嗑多少冰毒 、如何在夜城(Night City)排隊或抄捷徑,母體(matrix)仍會入夢;邏輯編織而成的明亮格網,在無色的虛空中開展……現在,蔓生區是一條橫跨太平洋、漫長而詭異的回家之路,而他不是操作手,也不是網際空間牛仔。只是另一個招搖撞騙的傢伙,努力想打通關節。但夢境在日本的夜晚上演,彷彿過度活躍的巫毒法術,而他為此哭泣,在睡夢中哭泣,在黑暗中孤獨醒來,蜷縮在某個棺材旅館的膠囊內,雙手刨入床板、緩衝泡棉從指間擠出,試圖觸及並不在那兒的機臺。
「我昨晚看見你女朋友。」瑞茲推了第二杯麒麟給凱斯。
「我沒女朋友。」凱斯舉杯喝酒。
「琳達‧李(Linda Lee)小姐。」
凱斯搖頭。
「不是女朋友?你們沒什麼?只是公事嗎,大師?為生意而獻身?」酒保棕色的小眼睛深陷於皺紋中。「我覺得我比較喜歡你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你比較常笑。現在,某晚,你可能太過裝腔作勢;最後落得被裝進診所水槽,肢體不全噢。」
「太傷我的心了,瑞茲。」他喝完啤酒,付過錢便離開,高聳的窄肩縮在被雨水打濕的卡其尼龍防風外套下。穿行在仁清路 (Ninsei)的路人間,他聞得到自己身上的汗臭味。
凱斯現在二十四歲。他二十二歲時成為一名牛仔、活躍分子、蔓生區身手最好的人之一。他師承麥考依‧波利(McCoy Pauley)和波比‧昆因(Bobby Quine);他們是高手中的高手,這行的傳奇人物。他上線 時總是處於腎上腺素高昂的狀態,年輕和高超技術的副產品;連上特製的網際空間控制板 ,讓他的意識脫離軀體,投射進母體的交感幻覺中。他是個小偷,替其他更有錢的小偷工作;這些雇主提供穿透企業系統明亮外牆所需的外來軟體,開啟通往數據沃野之窗。
他犯下典型錯誤,一個他曾發誓絕對不犯的錯誤。他偷雇主的東西。他暗槓了一些,試圖穿過防護柵移送到阿姆斯特丹。他還是不知道怎麼會東窗事發。不過現在也不重要了。他原以為會賠上性命,但他們只是露出微笑。他們當然歡迎,他們說,歡迎他取用那些錢財。他也將會派上用場。因為──微笑不減──他們會確保他再也無法工作。
他們用一種戰時俄國的黴菌毒素毀壞了他的神經系統。
他被綁在曼菲斯一家旅館的床上,天賦一微米一微米燒掉,在幻覺中度過三十小時。
神經損傷非常微小、不起眼,但效果十足。
凱斯曾活在網際空間的無軀體狂喜中,對他來說,這就是「墮落」。在他身為牛仔紅牌時常去的酒吧,菁英態度涉及某種程度對肉體不經意的蔑視。軀體就只是肉而已。凱斯墜入自身肉體的監牢中。
他的所有資產很快被轉換為新日圓,厚厚一綑舊紙鈔,無止盡地在世界各地黑市的封閉圈子裡流通,就像特羅布里恩群島(Trobriand Islands)島民的貝殼。蔓生區的合法生意很難用現金交易;在日本,現金已不再合法。
在日本,他堅定不移地確知他將找到治癒之道。在千葉。或在合格診所,或在黑市醫療的陰暗之地。千葉就是移植、神經接合與微仿生學的同義詞,也是一塊吸引蔓生區科技犯罪次文化的磁石。
在千葉,他眼睜睜看著他的新日圓經過兩個月為期的檢驗與諮詢後化為烏有。地下診所裡的男人是他的最後希望,但他們只是讚賞讓他致殘的專業技術,最後緩緩搖頭。
現在他睡在最便宜的棺材旅館,最靠近港口的那些,沐浴在把碼頭像大舞臺般整夜照耀的石英鹵素光潮之下;因為電視螢幕色彩的天空如此刺目,你看不見東京的燈火,甚至也看不見富士電力公司高聳的全息投影商標;東京灣只是一片廣袤的黑,白色保麗龍漂浮於淺水,海鷗盤旋其上。港口之外是城區,法人所屬垂直城市 的巨大方塊俯瞰圓頂工廠。較舊的街道形成一道狹窄中界,分隔港區與城區;這道中界沒有官方名稱。夜城,以仁清路為中心。日時,仁清路上的酒吧都拉下百葉窗,顯得毫無特色;霓虹燈熄滅,全息圖也失去生命,在含毒的銀色天空下等待。
喳呼以西兩個街口,一家名為茶罐(Jarre de Thé)的茶鋪,凱斯用一杯雙倍濃縮咖啡沖下這晚的第一顆藥。扁平粉色八角形的強效巴西右旋安非他命,跟左恩手下一個女孩買的。
茶罐以鏡為牆,鏡框是紅色霓虹燈。
剛開始,發現自己在千葉孤立無援,阮囊羞澀,找到治療方法的機會更是渺茫,他像是切入了快速自我毀滅模式 ,用一種似乎早已不再屬於他所有的冰冷強硬態度掙錢 。第一個月,他殺了二男一女,弄到的錢對一年前的他來說只會覺得可笑。仁清路耗損他,到後來,街道本身漸漸變得像某種死亡願望的具象化,某種他沒意識到自己已沾染的毒素。
夜城彷若一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瘋狂實驗,設計者是一名無聊的研究員,一根大拇指永遠壓在快轉鍵上。停止掙錢,你便沉沒無蹤;若動作稍微過快,又會打破黑市脆弱的表面張力;無論哪種結果,你都完了,徒留一抹隱約的回憶,淺淺刻在瑞茲這種常駐分子的腦中,只不過心臟或肺或腎或許會留下來,供某個有新日圓支付診所水槽的陌生人使用。
這裡的生意是潛意識中的嗡鳴,若是懶惰、心不在焉、行事笨拙、忽略錯綜複雜的行規,死亡是公認的懲罰。
獨坐在茶罐內,隨著八角藥丸生效,他的手掌冒出細小汗珠,突然感覺得到手臂和胸口每一根顫動的寒毛;凱斯知道他從某個時間點跟自己玩起遊戲,這個無名的遊戲非常古老,一場終末的接龍。他不再隨身攜帶武器,不再保持基本警戒。他接下街頭最快、最寬鬆的工作,得到無論你想要什麼他都弄得到手的名聲。 一部分的他知道,自己的自我毀滅弧度在日益稀少的客戶眼中愈來愈明顯;同樣那部分的他也安適地沐浴在自我毀滅只是早晚問題的認知中。也正是這一部分的他,因預料中的死亡而沾沾自喜,尤其痛恨想到琳達‧李。
他在某個雨夜的遊樂場發現她。
在燒透藍色香菸煙霧的明亮鬼魂下:巫師城堡(Wizard's Castle) 、歐羅巴坦克大戰(Tank War Europa)、紐約天際線的全息圖……他現在記憶中的她就是那個模樣,臉龐沐浴在永不安寧的雷射光下,五官只剩下色彩代碼:巫師城堡亮起時,她的顴骨閃耀著緋紅;坦克大戰打到慕尼黑時,她的額頭浸染著碧藍;滑動的光標在林立的摩天大樓樓壁敲出火花,在她的嘴脣勾勒出艷金。他那晚很亢奮,維吉的一個K他命磚正在送往橫濱的途中,錢已入袋。溫暖的雨淅瀝灑落仁清路人行道,他冒雨走進遊樂場,目光莫名就是鎖定了她;一堆人站在機臺前,他只看見她沉迷遊戲中的那張臉。當時她臉上的表情,在幾個小時後港區的一家棺材旅館內,他從她的睡顏再次看見;上脣像是孩童描繪飛行中鳥兒的線條。
穿過遊樂場站在她身旁,仍因做成的那筆交易而亢奮,他看見她抬眼一瞥。黑色煙燻妝框住灰眼。眼神像是被來車頭燈定住的動物。
他們共度的夜晚延長到早晨,再延長到氣墊船站買票以及他第一次渡過東京灣。雨一直下,沿原宿地區灑落,在她的塑膠外套上形成點點水珠,東京的孩子腳踩白色樂福鞋與輕便雨衣,連袂走過知名精品店;最後,她和他一起站在午夜柏青哥店的嘩啦聲響中,像個孩子般牽住他的手。
頭一個月就在毒品發揮完整效力和張力中度過,然後他才進一步將那一對永遠像受驚嚇小動物的眼睛轉化為反身需求的井 。他看過她的人格化為碎片,如冰帽般崩解,碎片漂走,最後才看見那原始需求,癮頭的饑渴盔甲 。他觀看她追著下一顆非法毒品,那種專注令他回想起他們在滋賀一欄欄販售的螳螂,旁邊是一缸缸藍色變種鯉魚和裝在竹籠裡的蟋蟀。
他凝視空杯內的那圈黑色渣滓,正隨他剛剛嗑的冰糖震動。桌面的棕色薄板黯淡無光澤,有一些歲月留下的細小刮痕。隨著右旋安非他命漸漸攀上他的脊椎,他看見無數留下那種表面刮痕的隨機碰撞。茶罐的裝潢是來自上世紀的某種陳舊無名風格,硬生生融合了日本傳統與蒼白的米蘭塑料雕塑,但似乎一切都蒙上一層隱約的薄膜,彷彿上百萬名客人的「壞神經」 莫名地攻擊了鏡子和曾經光滑的塑料,導致所有表面沾染上某種怎樣都擦不掉的物質而起霧。
「嘿。凱斯,好夥伴……」
他抬頭,對上畫了煙燻妝的灰眼。她身穿褪色的法式軌道工作服 和白色的新運動鞋。
「我一直在找你呢,朋友。」她在他對面坐下,手肘撐在桌上。藍色拉鍊裝的袖子從肩膀處扯掉。他不自覺地查看她的手臂是否有使用真皮碟或針孔的痕跡。「來根菸?」
她從踝間的口袋掏出一包壓扁的葉和圓(Yeheyuan)濾嘴香菸,抽出一根遞給凱斯。凱斯接下,讓她用紅色塑膠打火機為他點著。「你睡得好嗎,凱斯?看起來很累。」她的口音透漏她來自蔓生南區,接近亞特蘭大(Atlanta)。她眼睛下方的皮膚看起來蒼白不健康,但仍平滑堅實。她二十歲。疼痛開始在她嘴角刻下永恆的線條。她的黑髮以印花絲帶往後綁起,圖樣可能是微型電路或城市地圖。
「記得吃藥的話就還行。」一波實實在在的渴望襲向他,慾望和寂寞乘著安非他命的浪潮湧入。他記起在港區棺材旅館內過熱的黑暗中,她肌膚的味道,她的手指在他後腰交纏。
都只是肉,他心想,都是肉體想望。
「維吉。」她瞇起眼。「他想看到你臉上開個洞。」她幫自己點了根菸。
「誰說的?瑞茲?妳跟瑞茲有往來?」
「不,是莫娜。她的新炮友是維吉的手下之一。」
「我又沒欠他多少。真把我做了,他總之也拿不到錢。」凱斯聳肩。
「現在太多人欠他,凱斯。他可能會用你殺雞儆猴。你最好當心點。」
「一定。妳呢,琳達?有地方睡嗎?」
「睡。」她搖頭。「當然嘍,凱斯。」她顫抖,趴在桌上,臉龐覆上一層薄汗。
「給妳。」他從防風外套的口袋掏出一張皺巴巴的五十元紙鈔,不自覺地先在桌下撫平,對折兩次,然後才拿給她。
「你自己才需要,親愛的。最好拿去給維吉。」她的灰眼這會兒流漏一抹情緒,他讀不懂,也從來沒見過。
「我欠維吉的比這多太多了。你拿去吧。我還會有更多。」他撒謊,一面看著他的新日圓消失在拉鍊口袋內。
「一拿到你的錢,凱斯,盡快去找維吉。」
「再見,琳達。」他起身。
「一定。」她的瞳孔底下露出一毫米的白。三眼白 。「你自己小心。」
他點頭,急著想離開。
塑料門板在他身後關上時,他回過頭,看見她的眼睛映照在紅色霓虹牢籠中。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神經喚術士(電腦叛客永恆經典全新譯本)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神經喚術士(電腦叛客永恆經典全新譯本)
上承《銀翼殺手》,下啟《攻殼機動隊》、
《駭客任務》系列、《碳變》科幻狂潮,
全新科幻小說類型「電腦叛客」奠基之作。
網路革命、人工智慧、人機結合、太空殖民地……
當代人類科技發展預言書,
一九八四年出版至今,
永不褪色的科幻經典全新中文版重裝上市!
【本書特色】
★《神經喚術士》是充滿革命性的小說,真正的文化現象。──《出版人週刊》
★1984年一出版,即勇奪菲利普.K.迪克獎、星雲獎、雨果獎三大科幻權威獎項,科幻小說史上第一本三冠王!
★「電腦叛客」聖經解密,最專業全面的專文解說!
中興大學外文系林建光副教授專文解說,帶領讀者理解威廉.吉布森與《神經喚術士》何以在科幻小說史上獲得如此崇高的地位。
★電影、文學、漫畫,深深影響後世大眾流行文化,絕不能忽略的科幻浪潮開創者!
若你喜愛《攻殼機動隊》、《駭客任務》抑或對《銀翼殺手》、《碳變》難以自拔,那麼千萬不能錯過《神經喚術士》!
★科幻迷盛讚,最貼心、最到位的全新譯本。
翻譯《神經喚術士》是一項相當大膽、艱鉅的工作,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耗費的心力想必不足為外人道矣。
非常高興能看到這麼一本相當到位的中譯本,如果翻譯本身也是創作,
我相信它也是經典。──林建光
廿年來,這大概是我讀過的第七個中文譯本。
是我認為譯筆最信達雅的版本,也是我最喜歡的版本,沒有之一。──難攻博士
【故事簡介】
數千年來,人類夢想著與惡魔訂下契約,直到現在才有可能成真。
而你以什麼支付?幫助這東西獲得自由、成長,你的價碼是什麼?
在千葉市混濁得有如電視收播後顏色的天空下,失意的駭客凱斯始終懷念著那段曾經以牛仔身分馳騁於「母體」(網際空間)的日子。
他因為一時鬼迷心竅,遭到雇主懲罰,失去了進入母體的能力,自此過著與藥物為伍的日子。
某日,一名打扮詭異的神秘女子莫莉出現在他眼前,帶著凱斯見了她的雇主,名叫阿米堤、來歷不明的男子。
此人告訴凱斯只要接下他的委託──一場母體內的偷竊行動,竊取引領凱斯進入母體,已經死去的天才駭客留在網際空間的意識。
事成之後,凱斯將可以恢復重回母體的能力。
重回朝思暮想的母體,對凱斯而言,是太過巨大的誘惑,
於是明知事情絕對不是如此簡單,他仍舊接下了這個委託。
然而,阿米堤擺了凱斯一道,他的生命開始倒數計時。
如果要活下去,凱斯只能繼續深入母體,一直深入到見到那個惡魔……
一場又一場危險又瘋狂的偷竊行動,
一個又一個難以拒絕的惡魔的誘惑,
凱斯能否擺脫死亡,重獲回到母體的能力?
而這個惡魔真正的目的又是什麼?
【得獎紀錄】
1984年菲利普.K.迪克獎
1985年星雲獎
1985年雨果獎
史無前例的得獎紀錄,第一部囊括三大科幻獎項的作品。
【各國權威媒體盛讚】
.《神經喚術士》是充滿革命性的小說,真正的文化現象。──《出版人週刊》
.新鮮的想像力、引人入勝的細節,以及隱藏其中,令人不寒而慄的意涵。──《紐約時報》
.電腦叛客的精髓之作──《華盛頓郵報》
.卓越的創作與遠見,吉布森開創了全新的領域──《舊金山紀事報》
.史詩般的傑作,閃閃發光──《華爾街日報》
.在新興的資訊時代流行文化當中,吉布森是最閃亮的明星──《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
【各界狂熱讚譽】
AMAZON、Goodreads讀者★★★★評價
6tan(遊戲實況主)、GEEK-BASE POPO(美漫達人)、waiting(文字工作者)、亞次圓(影音創作者)、臥斧、馬欣(作家)、馬立軒(科幻、奇幻研究者)、陳栢青(作家)、龍貓大王(龍貓森林通信)、難攻博士(【中華科幻學會】會長兼常務監事)──狂熱推薦!
.比你年紀更大的超經典 Cyberpunk 作品!──6tan
.讀《神經喚術士》的感覺,就像是嘴裡被塞進滿滿一把迷幻藥,接著用200倍速無間斷地反覆播放《銀翼殺手》、《駭客任務》與《攻殼機動隊》的所有相關作品與各種版本,就這麼眼睛都不閉地足足看上三天三夜。──waiting
.在硬派科幻的同時,又帶給人腦神經的刺激。愛好者會不知不覺陷入作者奇特的寫法,流暢的就像裡頭的髒話般平順自然而突兀。──亞次圓
.母體、複製人、企業壟斷、義體改造、記憶與人格置換,以及黑色電影風格……所有Cyberpunk的要素,在類型誕生之初的《神經喚術士》中皆已存在!──馬立軒
.直接說重點:其一,關於原著。如果Cyberpunk是一門宗教,那Neuromancer絕對就是它的聖經,無可質疑;其二,關於譯本。廿年來,這大概是我讀過的第七個中文譯本,是我認為譯筆最信達雅的版本,也是我最喜歡的版本,沒有之一。──難攻博士
作者簡介:
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美國/加拿大科幻小說家。
1948年生於美國。
1982年發表短篇小說〈燃燒的鉻〉〈Burning Chrome〉,開始獲得注目。
1984年發表了立基於80年代科技發展,並佐以對人類未來驚人的想像力,發表了《神經喚術士》,一舉成名,正式確立電腦叛客(cyberpunk)此一文類。同為電腦叛客一派的代表作家,布魯斯.史特林(Bruce Sterling)盛讚,此作告別了科幻小說中陳腐、老舊的未來。
《神經喚術士》中源自電影《銀翼殺手》,頹廢、破敗與灰暗的未來景象,替之後的科幻作品開創了全新的創作方向。而對於肉體與意識的輕重、虛擬和真實的界限的叩問,吸引往後各種領域的創作者不斷提出屬於自己的答案,出版多年仍然是小說、電影、漫畫、電玩等大眾文化創作的靈感來源。
吉布森至今仍創作不輟,最新作為2014年發表的《邊緣世界》(The Peripheral)。
譯者簡介:
歸也光
讀書、四處玩。另開設週末文字加工廠,譯作有《孤獨癖》、《狂暴年代》、「星辰繼承者」三部曲等等。gabbybegood@gmail.com
章節試閱
港口上方的天空是電視收播頻道的顏色。
「不是說我有在用,」凱斯(Case)聽見有人這麼說;他正用肩膀頂開擠在「喳呼」(Chat)旁的人群,從中間穿過。「比較像我的身體自己生出嚴重的藥物缺乏症狀。」蔓生(Sprawl)口音說著蔓生區的笑話。喳呼的正式名稱是 茶壺酒吧(The Chatsubo),專為外國專業人士而設;在這裡喝上一週也聽不見兩個日文字。
照料吧檯的是瑞茲(Ratz)。他往一托盤的玻璃杯倒入麒麟生啤酒,義肢手臂單調地抽動。他看見凱斯後微笑,露出一口混雜東歐鋼與棕色蛀痕的牙 。凱斯在吧檯找到位置坐下,一邊是朗尼‧左恩(...
「不是說我有在用,」凱斯(Case)聽見有人這麼說;他正用肩膀頂開擠在「喳呼」(Chat)旁的人群,從中間穿過。「比較像我的身體自己生出嚴重的藥物缺乏症狀。」蔓生(Sprawl)口音說著蔓生區的笑話。喳呼的正式名稱是 茶壺酒吧(The Chatsubo),專為外國專業人士而設;在這裡喝上一週也聽不見兩個日文字。
照料吧檯的是瑞茲(Ratz)。他往一托盤的玻璃杯倒入麒麟生啤酒,義肢手臂單調地抽動。他看見凱斯後微笑,露出一口混雜東歐鋼與棕色蛀痕的牙 。凱斯在吧檯找到位置坐下,一邊是朗尼‧左恩(...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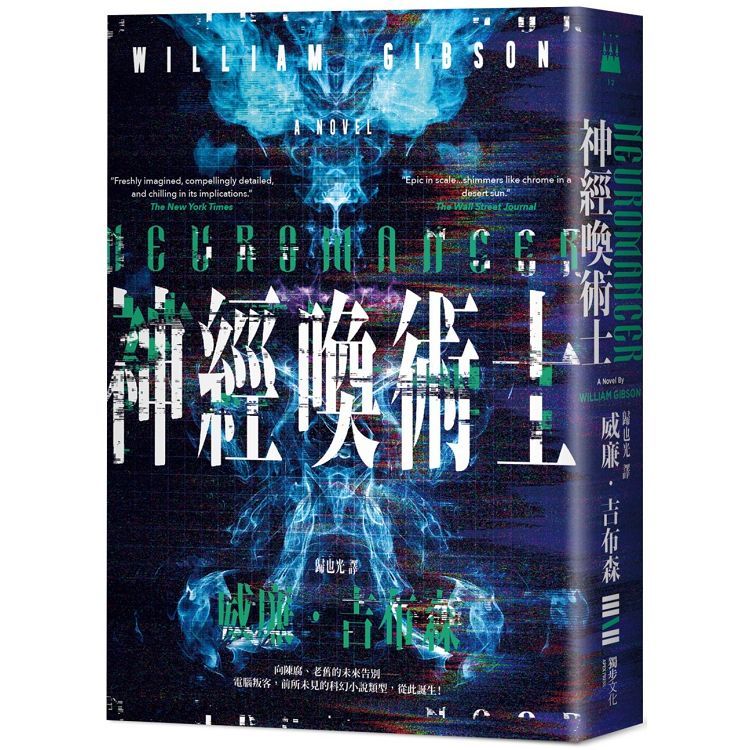
 2021/10/30
2021/10/30 2021/07/01
2021/07/01 2020/01/03
20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