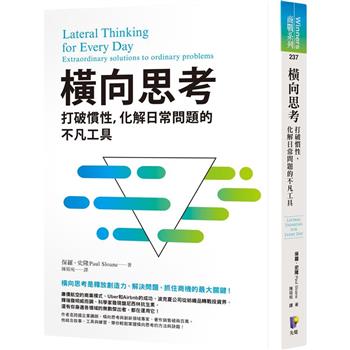再現《迷霧之子》閱讀震撼、挑戰當代奇幻經典高度
|只要用對方法,你就能重新編寫現實|
「現實」無法改變,但魔法可以欺瞞現實,只要你找到正確的語言……
《全面啟動》犯罪商戰+《刺客教條》華麗動作+《駭客任務》顛覆真實
|只要用對方法,你就能重新編寫現實|
「現實」無法改變,但魔法可以欺瞞現實,只要你找到正確的語言……
《全面啟動》犯罪商戰+《刺客教條》華麗動作+《駭客任務》顛覆真實
★《迷霧之子》布蘭登.山德森:準備好迎接遠古謎團、耳目一新的魔法及讓你心跳加速的刺激劫案!
★《鋼鐵德魯伊》凱文‧赫恩:創造力十足的作品、身歷其境、令人發顫!
★《時代雜誌》《衛報》《紐約時報》書評報導
★《出版人週刊》《柯克斯書評》《書單雜誌》強力推薦
它不止會說話,還是一把史上最嘮叨的魔法鑰匙!
女賊桑奇亞瞪大眼睛,看著手中會說話的鑰匙,
這金色的小東西聲稱自己叫克雷夫,可以打開世上一切的鎖!
但桑奇亞聽而不聞,她正在腦中細數今天到底惹出多少麻煩,又被捲進什麼駭人陰謀中……
桑奇亞又窮又髒,住在空無一物的鑄場畔小閣樓,四周都是貧困得會為了一點小錢割開你脖子的鄰居,她滿腦子只想活命和賺錢。數日前,桑奇亞從犯罪仲介人那兒接到可疑的案子,要她偷一個放在碼頭倉庫中的寶物。雇主身分成謎,而通常動有錢人東西歪腦筋的下場都是一命嗚呼,但這次的報酬多到她願意賣掉自己的靈魂。況且桑奇亞是賊中好手,她發揮「天賦」潛進藏保險箱的倉庫,儘管不慎炸毀半棟建築,惹毛大群衛兵,仍完成任務。只是沒料到讓她差點送命的戰利品,居然是一把「會說話」的金色鑰匙!
老實說,這不是她第一次聽到物品「說話」。
她偷遍天下仰賴的正是「聽見物品訊息」的天賦──鎖如何開、馬車輪滾過何處、走哪裡會找到沒人的路、建築中有什麼密道,她一碰物品便知。但這把自稱「克雷夫」的鑰匙不止如此,閃亮亮的小東西與她聊天鬥嘴、急著證明它的能耐,宣稱可以打開全世界的鎖。而此時的桑奇亞,還不清楚這把鑰匙的力量大到足以改變這座城市,這個世界……在這個當下,她只想著保命。
引介她的犯罪仲介人下落不明、住處留下大攤血跡,幕後黑手躲在陰影裡伺機而動,四處出現身懷異能的恐怖殺手,就連她所認知的「現實」也被徹底顛覆……鑰匙克雷夫,到底把她推進什麼樣的災禍中?她的天賦,又究竟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黑暗祕密?
身手不凡的聰敏女賊,落入翻天覆地的巨大陰謀;身世成謎的魔法鑰匙,帶她展開難以想像的驚天冒險;這座藏汙納垢、四大商家掌控的城市將面臨改變,誰可以成為這座城市、更甚至是世界的下一個主人?
【各界推薦】
把《潛龍諜影》、《阿基拉》、與《JoJo的奇妙冒險》丟進料理機攪碎之後,倒進《迷霧之子》 的 大鍋裡細火慢熬。
──龍貓大王
精細紮實的魔法設定、立體而多樣的人物,不但不會讓《階梯之城》的讀者失望,更有挑戰《迷霧之子》成為新一代奇幻當代經典的高度!
──廖培穎 (臉譜出版編輯)
令人期待的嶄新奇幻史詩系列,讓人興奮的序幕。準備好迎接遠古謎團、耳目一新的魔法,以及讓你心跳加速的劫案!
──布蘭登‧山德森
我們曾在無數科幻作品中看過奇幻元素的身影,但《銘印之子:鑄場畔的女賊》朝著你逆向而來,為現實世界中的各種科技物品披上一層以「銘印」為名的奇幻外衣,讓你看見智慧家具、電動車,甚至是無線基地台這類物品會如何出現在奇幻小說中,而且妥切到彷彿本應如此。這本小說不僅有趣,而且爽快到令人難以置信,讓你在看完的瞬間,就像大腦被刻上了銘記,不斷呼喊著:〈續集,續集,需要續集。〉
──WAITING(文字工作者)
複雜立體的角色、是科技也不是科技的神奇魔法、受制於敵對商業王朝的世界:等你想起該呼吸,班奈特將讓你佩服得五體投地。
──塔馬拉•皮爾斯
絕對引人入勝的虛構世界奇幻……我徹底被本書的概念吸引,事實上還因為主要角色們的不同與他們之間極度生火的摩擦而愛上他們,太敬佩班奈特的描繪了。我讀到很晚才上床,一大早又起來把它讀完。波瀾壯闊、深入人心,而且我渴望至極的系列作首卷。
──阿瑪‧埃─莫塔,紐約時報書評
班奈特有望再度全壘打的系列中出色的首卷,特色是老練的文筆、複雜且獨特的角色,還有一座有趣、致命、美好的新城市;這座城裡的現實能夠像撲克牌那樣洗牌,只要你能自圓其說。
──Tor網站
史詩、令人屏息的小說,身為奇幻作品,同時具備電腦叛客的風格……班奈特展開一個奇幻故事,裡面充滿絕佳的角色,不過最突出的還是他對魔法的觀點。
──The Verge網站
班奈特的創造力永無止盡,同等熟練地描繪出帝汎的世界、魔法、桑奇亞的混亂內心與神祕過往,更別提還有一批立體的次級角色。就連在黑暗的時刻,這個故事依然透露歡樂。
──Vulture雜誌
有趣刺激、步調快、令人發毛,這本了不起的小說預言更棒的故事即將出現。
──每日郵報 Daily Mail
有關權力與誤用權力的論述令人讚嘆。
──衛報The Guardian
魔法加上汙穢感的工業化,設定特殊,魔法的新奇科技。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有趣、發人深省、不可思議……結合動作場面、暑期強檔電影的奇想笑鬧,兼具複雜的人物,以及堪稱奧斯卡得主的銳眼社會批判
──奇幻宗派Fantasy Faction
才氣煥發的娛樂之作……
這個扭轉類型的故事起始於一場奔逃,而且不曾減速。
──邦諾書店奇科幻部落格 Barnes & Noble Sci-Fi & Fantasy
《鑄場畔的女賊》的主要物質元素──發臭的水道、愛聊天的鑰匙、神經質的鎖──並不是典型的奇幻代表物。班奈特以大量的魅力與表象的輕鬆大加利用這些元素,目的是傳遞這本小說的核心議題:繼承權力的不公,以及財富令人耽溺的特質。
──尼西‧蕭,西雅圖時報Nisi Shawl, The Seattle Times
創造力十足的史詩之作,令人欣喜的閱讀體驗。
──SFF世界網站
創造力永無止境的班奈特推出又一令人驚嘆的奇幻作品……生氣勃勃、怪得美妙地融合了科幻、奇幻、奪寶歷險,並深刻地論述身處沉迷於科技、金錢與權力的文化中,身而為人的意義。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星級評論)
蒙娜‧麗莎遇上駭客任務……偉大的娛樂之作,開展另一個創造力十足、極其獨特的奇幻小說系列。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星級評論)
多變、多樣的人物,一絲不苟的世界觀,複雜的家族間鬥爭,將吸引讀者進入這個嶄新、充滿動作場面的奇幻系列。
──書單雜誌Booklist(星級評論)
錯縱複雜的世界觀、神奇的魔法,還有魅力十足的人物。再給我更多!
──菲莉西雅‧黛Felicia Day,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在《鑄場畔的女賊》中,銘印魔法是現實的祕笈,而班奈特是大師級玩家。令人耳目一新的魔法觀點──主角是所有讀者都會想為她加油的女孩──出自就我所知最聰明的作家之一。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紐約時報暢銷小說魔印人系列作者
創造力十足、身歷其境、令人發顫,《鑄場畔的女賊》以迷人的觀點探討我們最好的意圖如何可能遭腐化──還有重力腰帶是多麼邪惡地美妙又駭人。幫你自己一個忙吧,拿起這本書。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紐約時報暢銷小說鋼鐵德魯伊系列作者
步調快速、機智、有趣,酷得難以想像的魔法系統。等不及想讀下一本了。
──布萊恩‧麥克萊連Brian McClellan,作家
《鑄場畔的女賊》把你拉進這個步調快速的冒險故事,再用創新的魔法系統把你打倒。從封面到封底都有趣、引人深思且刺激,劍與魔法師遇上電腦程式。
──詹姆士‧L‧蘇特James L. Sutter,開拓者角色扮演遊戲Pathfinder Roleplaying Game共同創作者
班奈特編織出一個令人聯想到山德森的非凡故事。《鑄場畔的女賊》是一個迷人的故事,有聰明的人物、吸引人的情節,以及壯麗的世界觀。
──夏莉‧荷伯格Charlie Holmberg,幻紙魔法師系列作者
年度最佳史詩奇幻兼年度最佳電腦叛客。你多常有機會說出這句話?
──丹‧威爾斯Dan Wells,作家
令人無法抗拒、步調快速的歷險,非奇幻讀者也能輕鬆進入,揭開一個魔法與陰謀交織的非凡世界。沒完沒了的轉折、一群令人讚嘆的人物,還有創新的魔法系統,《鑄場畔的女賊》是一場好得沒話說的閱讀體驗。
──賽巴斯欽‧狄卡斯泰爾Sebastian de Castell,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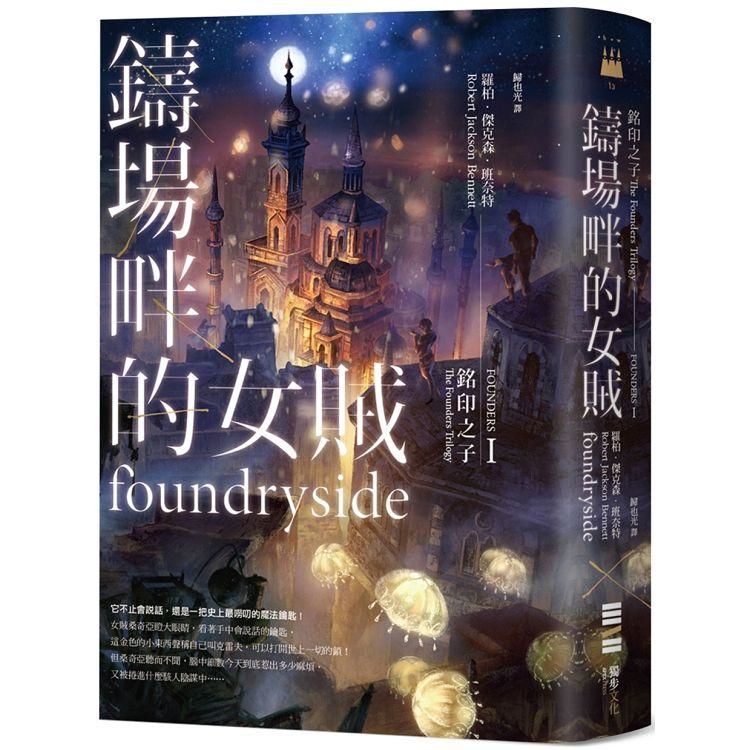
 2022/01/07
2022/01/07 2021/02/10
2021/02/10 2021/01/02
2021/01/02 2020/04/17
2020/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