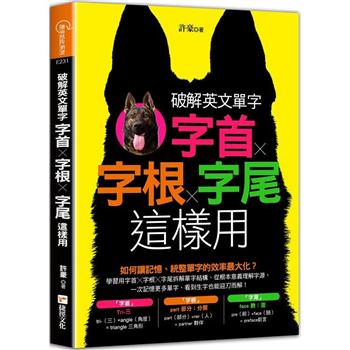圖書名稱:德文女老師
為什麼相愛?相愛的人為何分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作者這樣布局:
一對昔為戀人的男女多年後偶然再會,
男人向女人傾訴自己將動筆的小說,
女人告訴男人「我」誘拐了男孩的故事……
★臺灣罕見奧地利文學,2014年德國推理作家協會得獎作
★2020年日本寶島社「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國外選書
★2020年早川書房「好想讀這本推理小說!」國外選書及新人獎
★柯映安(作家)、馬欣(作家)、張茵惠(MPlus主編)、晨羽(作家)
廖梅璇(作家)、廖輝英(作家)──誠摯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列)
電子郵件、對白、兩人彼此傾訴的故事、警局筆錄、
一段一段手術刀般切割出來的人生──多種敘事手段,
奧地利作家以舞台劇般的詩意及真實人生的凡庸,
回答關於「相愛」和「故事」的謎題。
透過緊湊的詰問揭露一段感情破滅的真相,懸疑長在愛情當中,非常好看。
──柯映安
一段純粹從文字展開的冒險,即使內心沒有浮現任何圖像也能進行推理解謎的神奇故事。
──張茵惠
激情容易,延展成绵長的愛,卻需要一往無悔的相知,包容和寬待。十六年同居,獲得的是一封不告而别的絕情信。十四年後她回報救贖與重生的機會給他,這也是愛情的别型。
──廖輝英
穿渡真實與虛構,在生死的冷硬現實前,戀人的創作接力綻放浩瀚可能性,如繁花蔓延。
──廖梅璇
【故事介紹】
▍一切都很順利,沒有什麼驚奇,也不怎麼熱切,沒有相思之苦,也沒有浪漫的追求。不翹首以待,也不提心吊膽。我們都不再是十七歲的慘綠少年了,我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薩瓦爾
▍她愛他愛得如此深刻,愛得全身發痛。她愛他,也愛自己如此愛他。她是這麼地愛他,愛到時時忘記自己。──瑪蒂達
十六年前的五月十六日,薩瓦爾離開了。家中沒有他的咖啡杯、藍色雨傘、在羅馬尼亞拍的相片,沒有拖鞋和外套,沒有兩人日夜暢談的書,東西全不見了。瑪蒂達痛苦不已,她對「家」的渴望如此強烈,即使這念頭已經落伍,可是能讓她自豪的職業、孩子及可以共度人生的男性,是她兒時起在母親斥罵陰影下自心底長出的夢。
現在瑪蒂達是優秀的德文老師,深受學生愛戴。她的學校舉辦寫作工作坊,駐校作家是不告而別的薩瓦爾。這個不留隻字片語拋棄她的男人,如今寄出封封熱情如火的郵件,但瑪蒂達回應冷淡,薩瓦爾轉而苦苦哀求,想聊兩人分別後的種種。
沒有溫情敘舊,只有刀鋒上的舞。兩人信件暗潮洶湧、針鋒相對:刨挖彼此缺陷和人生痛楚、翻出謊言和背叛,嘲弄記憶不清與失敗婚姻、瑪蒂達突然說起關於監禁與愛的露骨故事。她說「我」抱走某個男孩、與「他」發展出危險關係。她說得那麼真實,幾乎逼瘋了薩瓦爾,因為他也有個失蹤的孩子,至今仍是懸案……
【編輯致讀者的話】
這是簡約又似帶著成人童話風味的愛情懸疑故事,作者有意思地選擇浪漫濫情的男女,筆觸則截然相反地理性冷然,帶有分析之意,採取數種敘事手段來書寫兩人的人生和神祕的動機。主角二人彼此懷有背離的價值觀,卻受到對方吸引,像有缺角的碎片彼此化做圓滿的圓。但在兩人關係最後一刻,留下了普世懸念,為什麼相愛的兩人最終走向別離?
十數年後,昔日戀人再會,都有不同祕密,兩人最初因對「故事」的喜愛相逢,如今再藉「故事」對話,為了隱瞞祕密,為了揭露祕密,交換分不清真假的言語。故事呼應人生,人生也呼應故事,男女時而凶狠針鋒相對,時而煽情藕斷絲連。薩瓦爾似要求取諒解,瑪蒂達卻似要直刺對方罩門,選擇一個「我誘拐了一個男孩」當作故事起頭。書名為何取《德文女老師》,讀完後每一個人應該會有自己的答案,或許,這個故事要講述的不只是一對心懷祕密的戀人,而是一名女子希望為自己故事留下想要的結局,窮盡生命所踏出去的一步。
作者簡介
尤蒂特.W.塔須勒Judith W. Taschler
1970年生於奧地利,大學主修德文與歷史,現職為教師,同時也是自由作家,創作過劇本,2011年出版首本小說,並於2014年以《德文女老師》一書獲得德國推理作家協會獎(Friedrich-Glauser-Preis,德國推理文學深具代表性的獎項)的肯定。
譯者簡介
劉于怡
旅居德國,現為自由譯者。


 2021/03/22
2021/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