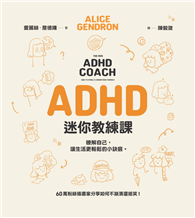第十八章
許風夢見鋪天蓋地的紅色。他醒過來時夕陽西下,霞光漫天,正如血色一般。許風擁被而起,覺得心間撲撲跳著,眼前朦朧一片,看什麼都像浮著一層紅。
隔一會兒慕容飛推門而入,見他醒了,不由欣然道:「許兄弟,你可算是睡醒了。你餓不餓?我去拿些吃的過來。」
「不用,」許風搖搖頭,瞇起眼睛打量四周,料想自己是在慕容府中,問,「我睡了多久?」
「整整一天一夜。」慕容飛在桌邊坐下來道,「你昨日跟那魔頭鬥劍,一劍刺出之後,忽然就倒了下去,可將我嚇了一跳,還當你跟他同歸於盡了。還好智空大師精通醫術,說你只是心力交瘁暈了過去,身體並無大礙。」
許風的記憶只到那一柄沒胸而入的長劍,後面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原來他是暈了過去。後來怎麼樣了?那人……是生是死?
許風還沒問起,慕容飛已先說了起來:「這回能擒住那極樂宮的大魔頭,許兄弟你可是立了大功。」
聽得「擒住」兩個字,許風一直惴惴的心終於歸於平靜,問:「那宮主沒死麼?」
「你那一劍刺得倒是夠狠,可惜差了些準頭,未能傷及心脈。」慕容飛邊說邊倒了杯茶,緊接著想起許風才是病患,忙把茶遞了過來,「照我的說法,當時就該再補上一劍,乾脆結果了那魔頭的性命,也免得夜長夢多不是?可我爹偏說現在還不能殺他。」
許風接了茶杯,嘴上雖然不說,心裡卻知道慕容慎為什麼這麼做。極樂宮勢大,光殺一個宮主濟什麼事?倒不如利用他的身分,將餘下的人一網打盡。
只是那人何等驕傲,就算重傷被擒,亦不會任人擺布,慕容慎這回怕是白費心機了。
天色漸漸沉下去,許風眼前浮著的那層紅霧也跟著散開了。他抬眼望向窗外,目光慢悠悠地蕩開去,忽道:「我想見他一面。」
慕容飛一時沒反應過來,直愣愣問:「誰?」
許風語音艱澀,說:「那宮主應當是關在慕容府中的地牢裡吧?」
「不錯,就是從前關那楚堂主的地方,不過看守的人可比上次多了許多。說來也怪,那楚堂主被抓的時候,極樂宮不知派了多少人來打探消息,如今換成宮主了,外頭竟一點動靜也沒有。我爹恐防有詐,等閒不許人再進地牢了……」
「我只想進去問他一句話,問完就走,絕不會叫慕容公子為難的。」
「此事倒也不難,只是不知你要問他什麼?」
許風動了動嘴唇,卻沒有作聲。
好在慕容飛也不追問,只說:「明白了,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不過今日天已黑了,我明天再想法子吧,你先吃些東西,好好休息一下。」
說罷叫人送了吃食過來。
許風其實沒什麼胃口,不過在慕容飛的催促下,多少還是吃了一些。但他已睡了一天一夜,可實在是睡不著了,待慕容飛走後,便仍舊在床邊呆坐著。
窗外一輪殘月在雲層中時隱時現,許風算了算時日,這才發現又是一個月過去了,再過幾天便是月初,也是他體內蠱蟲發作的日子。前幾個月他都是靠周衍的血熬過去的,至於這次……
月色蒼茫,許風心中木然地想,大不了疼死罷了。
他這一夜幾乎沒睡,到天亮前才迷迷糊糊地躺了一會兒,等醒來時,慕容飛已拿到了他爹的腰牌。只這回牢房的戒備森嚴得多,慕容飛沒法陪他混進去,只能讓他一個人進地牢了。
地牢裡那條路仍是陰暗潮溼的,許風一路走過去,見別的牢房都已搬空了,只盡頭處那間還有人把手著。因沒了那偶爾傳來的慘叫聲,反顯出另一種陰森的味道來。
可能是慕容慎事先打過了招呼,許風揚一揚手中的腰牌,兩個看守的人就放他進去了。鏽跡斑斑的鐵門打開時,發出一種怪異又刺耳的聲響,牢房裡暗得很,許風走得近了,才見水裡浸著一個人。那人因為傷重,只一條右臂被鐵鍊鎖著,他整個人就伏在那隻胳膊上,靠著這點力道勉強站立。他身上還穿著原來那件衣裳,胸口大片的血漬早已乾涸,變成了一種黯淡的深褐色,若非胸膛還微微起伏著,簡直讓人以為他已經死了。
許風從未見過他這樣狼狽的樣子,像畫中人落進凡塵裡,被狠狠踩進了汙泥中。他心中騰起一點近乎疼痛的快意,剛踏前一步,那人就抬起了頭來。
那人散下來的黑髮遮住了半邊臉孔,剩下一半也沾了血汙,只一雙眼睛透著微芒,有點像他易容時的樣子。
有些像……他的周大哥。
許風恍惚了一下,卻聽那人開口道:「風弟,你來了。」
像是早料到許風會來。他聲音雖然低得很,卻不似假扮周衍時那般沙啞,顯然是撤下了所有偽裝。
許風霎時清醒過來,深恨自己鬼迷心竅,到了這個地步還要來見他。但他心頭那點疑問如同卡在喉嚨裡的刺,實在不吐不快,於是道:「我今日來此,只是要問你一句話。」
「問什麼?」
許風沒去看他的眼睛,只盯著他衣襟上那一片暗紅,問:「為什麼教我那一招劍法?」
明知自己要找他報仇,為何還要親手教他殺人的劍法?若只是為了利用他,何必做到這個地步?若是為了別的……許風想不出還有別的理由。
許風等了許久,才聽那人道:「我說過的,一切都會如你所願。」
這話他聽周衍說過不止一次,當時聽著只覺甜蜜,如今卻又是另一番滋味了。他捏住拳頭,終於抬頭與那人對視,仍是問:「為什麼?」
那人低聲笑起來。這一笑牽動傷口,笑聲中便夾了些咳音,到最後斷斷續續的,幾乎不成調子了。他笑過之後,方半闔著眸子,緩緩道:「這已是第二個問題了。」
許風被他氣得不輕,上前一步揪住了他的衣領。那人閉了閉眼睛,輕輕喘了一下。許風這才覺得不對,拉開他衣領一看,只見他身上布滿了各式傷痕,除了胸口那處劍傷潦草包紮過之外,其他幾無一塊完好的皮肉。許風的視線順著那些血肉模糊的傷口看下去,最後沒入渾濁的水中,這樣的傷浸在水裡,滋味可想而知。
許風怔怔看了會兒,突然想到一事,伸手去碰他遮在臉上的頭髮。
那人抬手攔了一下,有些吃力的說:「風弟,別看。」
但他手上沒什麼力氣,根本也攔不住。許風撥開那頭烏髮,藉著牢房外的微弱火光,看清他臉上一道血淋淋的鞭痕──從眼角一直蜿蜒到下巴處,將半張臉都毀了。
許風眼底映著駭人的血色,問:「他們對你用刑了?」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麼?慕容慎不殺我,自然是為了從我嘴裡探聽些消息。」那人動了動左手,似乎想抓住許風的手,但終因氣力不濟,慢慢滑落下去,「只我身上這件衣裳曾用特製的藥材熏過,能壓制住我的內力,若打壞了就派不上用場了,倒是因此倖免於難了。」
許風一驚,道:「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就是你生病的那幾日。你平常有什麼心事都寫在臉上,那幾天……裝得實在不像。」
許風背後沁出一層冷汗。
若這人當時就發難,豈非功敗垂成,一切都不一樣了?
「既然你早知那是陷阱了,為何還要孤身前來?為何要穿我挑的衣裳?」
「你送我的東西,無論什麼我也喜歡。」
那人面容蒼白,臉上更有一道猙獰鞭痕,原是奄奄一息的樣子了,但是望向許風的眼神裡,仍舊透著一股溫柔多情的勁兒,道:「風弟,我對你說過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心的。若非不小心被你發現了真相,我原本是想瞞你一輩子的。」
許風只覺可笑。
「堂堂極樂宮的宮主,難道就只會坑蒙拐騙嗎?一面說著真心,一面又打算一直瞞我,當真是好手段!」
他說著說著,不由自主地按住了自己的右手。
那人也跟著望過來,靜了一會兒才道:「確實是我對不住你,你恨我也是應當。那一劍可夠解恨麼?若是不夠……」
他頓了頓,眼睛瞥向牢房的角落裡。
許風轉頭看去,見地上扔著一根鞭子,鞭上生了倒刺,俱是烏沉沉的顏色,也不知沾過多少人的血。許風明知那人是故意挑釁,還是克制不住自己的脾氣,衝過去拾起了鞭子。而後一步步走回來,舉高了鞭子對著那人。
若只是極樂宮中的三年折辱,那一劍也抵得過了,許風真正恨的,是這世上唯一待他好的周大哥,竟然也是假的。
他瞪著那人身上的傷痕,舉得手都痠了,這一鞭才重重落下。卻是「啪」的一聲打在了水面上,激起來一陣水花。
那人詫異地望他一眼。
許風卻沒看他,扔下手中的鞭子,徑直出了牢房。他腳下走得甚快,沒多久就穿過那條長長的甬道,走出了陰暗的地牢。
外頭豔陽高照,一下落在身上,刺得人眼睛疼。許風這才緩住腳步,停下來按了按眼角。
一切如他所願麼?
許風從未說過,除夕那夜他許下的心願,是歲歲年年都與周大哥相伴。
……以後亦無機會再說了。
慕容飛一直在外頭等著,見許風出來,便迎上來道:「許兄弟,怎麼樣?問著你想問的話了嗎?」
許風有些走神,點點頭又搖搖頭,最後歎了口氣,說:「是我想得太多,根本也沒必要去問。」
他頓了一下,道:「我見那人……那魔頭身上似乎有傷,不知慕容前輩打算如何處置他?」
「我爹自然是想一口氣滅了極樂宮,只是拿那宮主作餌,極樂宮的人卻並不上鉤,如今只能另想辦法了。我爹說只要留著那魔頭一條命就行,別的也顧不得了。畢竟那些被擄走的女子至今下落不明,總得救她們回來不是?」
許風原本極不贊同慕容慎的做法,邪道之人手段殘忍,他們正道中人若也一般行事,又何來正邪之分?只是想到那些女子被擄去極樂宮,也不知要受多少欺辱折磨,登時又沒了說話的立場。
他跟慕容飛聊了幾句,便回自己房間休息了。
接下來幾日風平浪靜,極樂宮像是一夜間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再不聞半點消息。越是如此,慕容慎越不敢掉以輕心。許風聽慕容飛說起,知道他後來又對那人動了幾次刑,但始終沒問出想要的東西。
許風因那日又救了慕容飛一回,在慕容府中被奉為上賓,不僅慕容飛每日揀好吃好玩的送過來,連慕容夫人也給他送過幾次東西。許風原只是心力交瘁暈了過去,這些天裡早把身體養好了,但他自己也說不出為什麼,仍是一日日的在慕容府裡住了下去。
這天夜裡全府的人都已睡下了,到半夜裡卻被一陣喧譁聲吵起來,原來是慕容慎連夜找了幾個大夫進府。許風披衣起身,站在視窗望了望,遠遠看見慕容府的管家舉著火把,引著幾個人往西南角的地牢走去。火光照亮那些人的臉,許風看著眼熟,認出來是自己假裝生病那會兒,周衍找來的蘇州城的名醫。
這一行人走入地牢,那一點微弱的光芒很快就被濃重的夜色吞噬了。
地牢裡如今只關著一個人,慕容慎半夜找大夫來是為了什麼,不用猜也知道了。
許風在視窗立了會兒,直到風起得大了,撞得窗櫺匡匡響,他才伸手關了窗子,和衣躺回了床上。他這幾日精神不濟,原是倦得很了,這時卻無論如何也睡不著了,只睜大了眼睛瞪住床頂。
夜裡靜得可怕,許風獨個兒躺在那裡,總覺得聽見地牢那邊傳來了聲響。待他急匆匆地跳下床時,卻發現不過是虛驚一場,除了靜夜裡偶爾的一、兩聲犬吠,根本什麼也沒有。
他的心提起來又沉下去,到最後索性不睡了,只坐在床邊等著。直等到天際泛白,也不見什麼動靜,倒是府裡的小廝丫鬟們輕手輕腳地起來幹活了。
許風熬了一夜,這時也不打算再睡了。他穿戴齊整後,瞥一眼桌上的鏡子,看見鏡中一張蒼白麻木的臉,臉上絲毫生氣也無,簡直將他自己嚇了一跳。
過一會兒服侍他的小廝送吃的過來,許風含含糊糊地問起昨夜府裡出了什麼事。那小廝甚是機靈,知道他想問的是什麼,回道:「西邊的事情咱們打聽不到,不過聽馮管家的語氣,昨夜府裡可沒有死人。」
許風聽罷,也說不清是不是鬆了口氣。
他賞了那小廝一塊碎銀子,小廝喜滋滋地去了,剛出得門,就聽見外頭喧鬧起來。許風忙把人叫了回來,問:「出了什麼事?」
那小廝也是一頭霧水:「像是有人在府外鬧事,我出去瞧瞧。」
許風心神不定,乾脆也跟了出去。半道上遇見慕容飛,他倒是知道些原委,一面走一面同許風說:「還不是為了那魔頭的事!我爹留他一命,可有許多人為此不滿。」
許風到了門口一看,果然見許多人聚在慕容府的大門外,有些是曾經見過的,有些則陌生得很,亂哄哄的鬧成一團,嘴裡嚷著什麼「除魔衛道」、「誅殺魔頭」。
極樂宮作惡多端,在江湖上樹敵無數,如今宮主被擒,自然有不少人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這會兒群情激奮,管家出來勸了幾次也勸不住他們,只好叫護衛牢牢守住大門,免得有人衝殺進來。
倒是慕容慎閉門謝客,任外頭鬧得天翻地覆了,也是不理不睬。
到了傍晚時分,才有一人進了慕容慎的書房。這人許風也認得,正是林公子的爹林嘯。聽聞這林莊主乃是慕容慎的摯交好友,兩人年輕時闖蕩江湖,彼此都救過對方的性命,後來相繼成親,更是早早的定下了兒女親事。慕容飛的妹妹就是聘給了林莊主的次子,只因極樂宮一事耽擱了親事,兩人至今還未完婚。
林莊主這時前來,也不知要談些什麼?
慕容飛膽子大得很,拉了許風去書房外頭偷聽,只是他倆不敢離得太近,只隱隱約約聽到幾句話。
「……林兄說這等話,實在是叫小弟為難。」
「慕容兄將那魔頭關在府內,可是擔著天大的干係,與其將來招來禍事,還不如現在就……」
兩人在書房裡密談了半個多時辰,慕容慎才出門送客。他城府甚深,明知慕容飛在外頭偷聽,臉上卻是半點聲色不露,直到送走了林莊主,方把慕容飛和許風一塊叫進了書房。
「飛兒,我跟你林伯父已經談妥了。」慕容慎在書房裡來回踱了一陣,而後轉過頭來,一字字道,「三日之後,當眾誅殺那極樂宮的宮主。」
慕容飛挑眉道:「如此說來,三日後就是引那些魔道妖人出來的最好時機了。」
慕容慎笑笑,說:「若他們並不上鉤呢?」
慕容飛噎了一下,道:「那、那殺了極樂宮的宮主,也算是大快人心了。」
慕容慎目光一轉,落在許風身上,問:「許少俠覺得如何?」
許風眼皮急跳,沒聽清他說了什麼,直到他再問一遍,才點頭道:「如此……甚好。」
那人十惡不赦,當有此報,沒有什麼不好的。
要當眾誅殺極樂宮宮主的消息一傳出去,又陸陸續續地有不少江湖人士趕到了蘇州城來,慕容府的大門外人滿為患,來來去去的都是些佩刀佩劍的江湖漢子。還有人覺得一劍殺了那宮主太便宜了他,叫嚷著要什麼凌遲處死、五馬分屍。若非慕容家在蘇州城頗有根基,上上下下打點好了關係,這些人怕是早被官府捉去了。
三日忽忽而過。到了最後一天的夜裡,慕容慎突然將許風請去了書房。他也不說旁的,只把一壺酒遞給了許風。
許風一時沒反應過來:「慕容前輩這是何意?」
「那人臨死之前,想要見你一面。你跟他畢竟有些交情,說不得能勸他一勸,只要他答應同我合作,我自然有辦法保他性命。」
許風道:「酷刑加身也無法令他點頭,我又如何勸得動他?」
慕容慎意味深長地瞧著許風,說:「那可未必。」
許風推脫不過,只好答應下來。
這一日已是月末,天上無星無月,夜色濃得像是要擇人而噬。許風得了慕容慎的腰牌,提著壺酒進了地牢。他沒拿火把,摸黑走完了那一條甬道,到盡頭處才看到一點火光。
牢房裡那人的樣子比前幾日更為淒慘,兩條手臂都被鐵鍊吊了起來,身上舊傷疊著新傷,胸口包紮過的傷處往外滲著血。他穿著的衣裳也被血染透了,若不是許風親手挑的布料,根本辨不出原來的顏色。
許風腳步一滯,覺得他可能撐不到明日就要斷氣了。
但是當牢房的鐵門發出聲響時,那人還是勉強抬了抬頭。見來的人是許風,他暗沉沉的眸子裡像是多了些生氣,只是他連說話的力氣也無,便僅是輕輕牽動一下嘴角。
許風腦海裡空白了一下,才明白那人是朝自己笑了笑。他胸口堵著一口氣,過了會兒才說:「慕容前輩叫我來送你一程。他說你若是肯改邪歸正,他自有辦法留你一命。」
事關生死,那人卻是聽而不聞,只專心致志地盯著許風,像是要把他的臉刻進眼底。待看得夠了,那人才動了動嘴唇,聲音嘶啞的說:「你知道不可能的。」
是了,正邪不兩立,唯有你死我活這一條路可走。
許風早料到答案了,因此不再相勸。他開了手中那壺酒,而後移步上前,將酒壺遞到那人嘴邊,道:「明日之事,你應當已經知曉了?若你只是周大哥,我原本……」
他聲音低下去,終於沒能把話說完,只是道:「可惜你不是。」
那人正就著許風的手喝酒,聽了這話,忽地咳嗽起來,酒液滲著血水從他嘴角淌下來。
許風見了那刺目的紅色,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擦,觸著那人的嘴唇時,那人竟側了側頭,趁勢親了一下他的指尖。
許風的手一顫,連忙撤了回來。
那人的眼睛裡透出一點笑意,啞聲道:「風弟,你靠近一些,我有句話同你說。」
不要聽。
沒什麼好聽的。
許風在心裡這麼說,人卻已經湊了過去。他俯下身,那人的唇就貼上他耳邊,親暱得猶如親吻,緩緩說道:「再過幾日就是月初,你身上的毒又快發作了。我那日動了真氣,蠱蟲已入心脈,若是我死了,你就將我的心挖出來……」
「砰!」
許風手中的酒壺落下去,在地上摔了個粉碎。他往後退了一步,不肯聽那人再說下去。明明這人身受重傷,被鐵鍊鎖著動彈不得,在許風眼裡卻如洪水猛獸,逼得他步步後退。
他退到了鐵門邊上,才想起自己是來替慕容慎傳話的,該勸的已經勸過,那人既然不聽,自己也沒必要再留下去了。
許風轉身欲走,卻聽那人叫了聲:「風弟。」
許風的身形僵了一下。
那人的聲音其實離得有些遠了,卻又像近得就在他耳邊:「風弟,我明日就要死了,你不再回頭看我一眼麼?」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為兄(下)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為兄(下)
落子無悔,不可能重新來過,
有些事情,再沒有後悔的餘地,
賀汀州多希望自己從未傷害過許風,
這厭惡著他的青年,是他的執著,
也是唯一的溫柔,而他心甘情願。
這是他心心念念、最想保護的弟弟,
他可以放手讓許風離開自己身邊,
可以教許風如何殺了「極樂宮宮主」,
但若這孩子始終狠不下心讓他死,
就只能緊緊抓住他,再不放手。
TOP
章節試閱
第十八章
許風夢見鋪天蓋地的紅色。他醒過來時夕陽西下,霞光漫天,正如血色一般。許風擁被而起,覺得心間撲撲跳著,眼前朦朧一片,看什麼都像浮著一層紅。
隔一會兒慕容飛推門而入,見他醒了,不由欣然道:「許兄弟,你可算是睡醒了。你餓不餓?我去拿些吃的過來。」
「不用,」許風搖搖頭,瞇起眼睛打量四周,料想自己是在慕容府中,問,「我睡了多久?」
「整整一天一夜。」慕容飛在桌邊坐下來道,「你昨日跟那魔頭鬥劍,一劍刺出之後,忽然就倒了下去,可將我嚇了一跳,還當你跟他同歸於盡了。還好智空大師精通醫術,說你只是心力交瘁...
許風夢見鋪天蓋地的紅色。他醒過來時夕陽西下,霞光漫天,正如血色一般。許風擁被而起,覺得心間撲撲跳著,眼前朦朧一片,看什麼都像浮著一層紅。
隔一會兒慕容飛推門而入,見他醒了,不由欣然道:「許兄弟,你可算是睡醒了。你餓不餓?我去拿些吃的過來。」
「不用,」許風搖搖頭,瞇起眼睛打量四周,料想自己是在慕容府中,問,「我睡了多久?」
「整整一天一夜。」慕容飛在桌邊坐下來道,「你昨日跟那魔頭鬥劍,一劍刺出之後,忽然就倒了下去,可將我嚇了一跳,還當你跟他同歸於盡了。還好智空大師精通醫術,說你只是心力交瘁...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困困 繪者: WEHIP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8-08 ISBN/ISSN:978957957849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13*21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