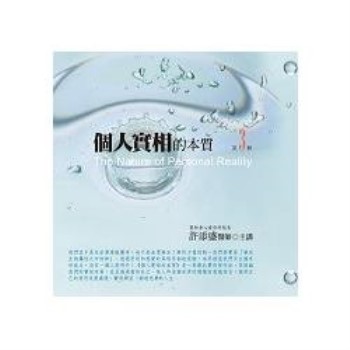作品全球總印量突破2,000,000冊
第一個、也是唯一蟬聯兩屆愛倫坡獎最佳小說得主
每本作品均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
約翰.哈特全新巔峰代表作《贖罪之路》
第一個、也是唯一蟬聯兩屆愛倫坡獎最佳小說得主
每本作品均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
約翰.哈特全新巔峰代表作《贖罪之路》
˙《出版者週刊》年度推理選書
˙甫上市即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獨立書商選書
˙日本早川書房「這本推理小說最想讀」選書
˙奧克拉2016年春季推薦作品
˙亞馬遜網路書店超過千位讀者4顆半星擊節好評!
˙版權已授:英國、德國、挪威、日本、荷蘭、丹麥、法國、土耳其、西班牙、捷克、波蘭
名叫紀登的男孩帶著槍,等待著殺害他母親的男人出獄……
女警探伊麗莎白成功營救出被鎖困在地窖裡的少女,但她以殘暴的手法擊斃兩名兇殘綁匪,兩具屍體上有十八發子彈,執法過當遭到社會輿論嚴重譴責。背後,她有不能公開真相的理由……
曾被視為警界明日之星的艾爵恩因認罪殺人而入監服刑,歷經十三年終於重獲自由。伊麗莎白堅信她尊敬的男人是清白的,但隨著他出獄的同時,森林深處一座廢棄教堂的祭壇上,一具蓋著白色亞麻布的屍體逐漸冷卻。犯案手法及地點與十三年前艾爵恩的犯行如出一轍……
這是個瀕臨險境的小鎮。
這是條贖罪之路。
全書交織著緊張對峙、秘密以及背叛,精采重現美國小鎮荒景風情,以及被世界遺棄、殘敗孤絕之人的真實樣貌。這是一部令人膽顫心驚的懸疑之作,曲折離奇,讓人忍不住一氣呵成看完!獲選日本週刊文春推理小說BEST 1、愛倫坡獎雙冠王作家,暢銷文學懸疑小說大師約翰.哈特以《贖罪之路》再創全新巔峰代表作!
名人盛讚
壯闊、無畏,令人欲罷不能。《贖罪之路》從第一頁就擄獲我的心。約翰.哈特是說故事大師!──哈蘭.科本(Harlan Coben)
出版界人士都知道約翰.哈特是文壇的拚命三郎。他激切又優美的筆觸不禁讓人聯想到詹姆斯.李.伯克的文風。這本《贖罪之路》也讓哈特晉升到更高層次,光是序曲就讓人揪心,而其後的章節更把你逐步拉進黑洞。這本作品絕對必讀,接下來,一定要再回頭找出他所有的舊作,一本都不能放過!──大衛.鮑爾達奇(David Baldacci)
約翰.哈特寫起來像個詩人,我讀得欲罷不能,這本小說刻劃犯罪及其對人類心理產生的廣大影響,完全令人上癮。我本來就是約翰.哈特的長期粉絲,而《贖罪之路》,更是他的巔峰之作!──麗莎.史考特萊恩(Lisa Scottoline),《紐約時報》暢銷榜作者
約翰.哈特每一部新作,都為他的寫作成就再添新的一筆。他以交出的五本作品,提高了商業小說的高度。其中巧妙融合了古典驚悚小說的緊張、節奏、懸疑,加上刻劃豐富的角色和優美的文筆,達到了純文學的高度。在《最後的守護人》和《鐵山之家》之後,我就等不急要看哈特的下一部作品。我沒有失望,《贖罪之路》是一部成功之作!──科爾班.艾迪生(Corban Addison),全球暢銷書A Walk Across the Sun作者
在這本表現突出的犯罪小說當中,愛倫坡獎得主約翰.哈特深入探討了面對悲痛背叛之際、人心還能剩下多少的痊癒力與信任……雖然約翰.哈特擅長營造劇情轉折,但真正能讓讀者銘記在心的還是他筆下遍體鱗傷、但依然強韌又勇氣十足的主角。──《出版人周刊》(星級評論)
在這場宛若歌劇的文字展演中,舞台上的角色、衝突、秘密、故事支線飽滿豐富──而且,從交響樂團到包廂區的每一名觀眾都看得感動不已,眼眶霧濕。──《柯克斯評論》
約翰.哈特強勢回歸的爐火純青之作,懸疑性十足,打從第一頁就讓人目不轉睛!──《每日快報》
精雕細琢的傑作!──《愛爾蘭獨立報》
這本書真是不簡單:《贖罪之路》寫得太了不起了!──布拉德.梅爾策Brad Meltzer
他是個手法嫺熟的作者,能夠同時令眾多人物角色的靈魂震顫,同時用錯綜複雜的情節營造緊張的氛圍,揭露故事的背景…… ──《圖書館期刊》
我已經很久沒有過這樣的感受了,從讀第一個字開始便被牢牢吸引住,看著作者緩慢構築情節,接著一口氣看到最後令人驚心動魄的結局……《救贖之路》基本上講述了一個有關失去的力量與記憶的故事。這本書將哈特稱為『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故事以最耀眼的方式呈現出來。 ──《公開信月刊》
哈特再次證明,只要是文學推理小說,他便躋身最優秀作家之列。那些小說將犯罪、懸疑與調查之光融入到人類的思想與靈魂之中。 ──Greensboro News & Record網站
當今最優秀的驚悚小說家之一——可以與大衛.鮑爾達奇、約翰.葛里遜、弗瑞德里克.福賽斯與李.查德相媲美。當哈特優美的文字躍然紙上時,或許只有詹姆斯.李.伯克可以相匹敵。令人過目難忘!──英國《每日郵報》


 2018/01/25
2018/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