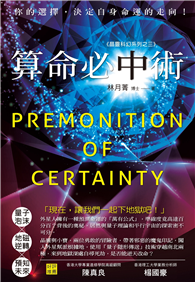1
她尖叫過,但是從來沒有哭。 有關這一位,他將會記得的就是這一點,他心想。不是她頭髮或眼珠的顏色。不是她歪斜的臀部,嘴唇的弧度。完全不是這一類事情。甚至不是她的名字。 她尖叫過。朝著星光點點、無動於衷的天空尖叫。他們全都會尖叫,每個都會。 但是她沒有哭。 反正哭也沒有用。他無論如何都會殺了她,所以她做什麼都沒有用。但這件事他老是忘不掉:沒有眼淚。沒有哭泣。女人總是愛哭。那是她們最終的、最好的武器。只要一哭,男朋友就會道歉,丈夫就會把她們擁入懷中。只要一哭,老爸就肯為她們的高中舞會禮服多花點錢。 她尖叫了,她的尖叫聲好美。 但是,老實說,他想念女人的哭泣。
稍後,等到完事了,他往下看著她。這個清晨——早得太陽都還沒升起——很溫暖,空氣中有淡淡的機油味。現在死去的她沉默不動,他再也想不起自己為什麼要殺她。有短暫的片刻,他想著這樣是不是很奇怪,但立刻就拋開疑慮。她將只是眾多人中的其中一個而已。之前還有一些人,往後還會有更多。 他跪在她旁邊,從刀鞘裡拔出一把短而鋒利的刀子。指尖在她身上摸了一會兒。 他決定挑左臀,然後開始刻。
2
這個垂死男子的名字是…… 唔,無所謂。再也不重要了。兇手知道,名字是事物的標籤。只是個名詞,代表人、地、事、想法——就像你在學校學過的。你看到我用來喝水的這玩意兒了嗎?我給了它「杯子」的標籤,那又怎樣?你看到我用來遮蓋身體的這玩意兒了嗎?我給了它「襯衫」的標籤,那又怎樣?你看到我切開來面對黑暗天空、讓美麗的月光照進來的這玩意兒嗎?我給它「哲若姆.海靈頓」的標籤,那又怎樣? 兇手站起來伸展四肢,背部往後彎。扛著這個標籤為哲若姆.海靈頓的玩意兒爬五層樓梯可不容易;害他肌肉痠痛。幸好,他不必把這個標籤為哲若姆.海靈頓的玩意兒再扛下去了。 這玩意兒的頭左右扭動,眼睛直直瞪著前方,沒眨眼。眼睛不眨是因為沒辦法——兇手已經先把他的眼皮割掉了。他向來先割掉眼皮的,這個非常重要。 兇手在那玩意兒頭部旁蹲下,低聲說,「我們現在接近了。非常接近。我會幫你開膛剖腹,而且我必須說——你在月光下很美。太美了。」 那標籤為哲若姆.海靈頓的玩意兒什麼都沒說,兇手覺得這樣很沒禮貌。但兇手並不憤怒。兇手知道憤怒是什麼,但從來沒有體驗過。憤怒是浪費時間和精力。憤怒是無用的。「憤怒」只不過是一種標籤,貼在一種毫無功用的情緒上頭。 或許這個標籤為哲若姆.海靈頓的玩意兒就是無法欣賞自己的美。兇手考慮了一會兒,然後伸手往下,從那玩意兒破開的腹腔內撈出一把血淋淋、滑溜溜的腸子。月光照得那一圈圈紅灰交雜的腸子發出閃光。 這個標籤為哲若姆.海靈頓的玩意兒發出呻吟,帶著深切而持續的痛苦。這玩意兒竭力抬起頭,彷彿想要逃離,但只能勉強舉起腦袋。 這玩意兒大哭,試著想說話,淚水滑下臉頰。 兇手笑容滿面。這玩意兒聽起來很開心,這是好事。 「快弄完了,」兇手保證道,放下腸子。同時,那玩意兒的脖子沒力氣了,腦袋摔下。先是吭!一聲,然後是嘶噗! 兇手從靴子裡抽出一把鋒利的小刀。「我想是額頭,」他說,然後開始刻。
3
比利.丹特盯著鏡子裡。他不太認得出自己,但這也不是新鮮事了。比利向來覺得鏡子裡的自己好陌生,從小就是這樣。一開始他好恨又好怕這個鏡中人,似乎走到哪裡都死跟著他不放,透過鏡子和商店櫥窗跟蹤他。但最後,比利總算明白自己在鏡中看到的,就是其他人望著他時所看到的樣子。 不知怎地,其他人沒看到真正的比利。他們看到的是個跟他們差不多的人類,是個凡人。看起來就像個礦藏。 屋外傳來壓縮式垃圾車的機械輾磨聲。比利拉開窗簾往外看。三層樓下,一輛垃圾車正在壓縮回收空瓶罐。 比利咧嘴笑了。「啊,紐約,」他輕聲說。「我們一定會玩得很開心。」
第二部 四個玩家,三方 4 那是個寒冷、晴朗的一月天,他們相聚在這裡,要埋葬爵士的母親。 埋葬這個字眼大概不對;因為沒有屍體。在爵士八歲那年,也就是九年多之前,珍妮絲.丹特就失蹤了,從此再也沒有人看過她。全世界都知道她死了;法庭也在必要的七年等待期之後宣佈她的死亡。只不過之前爵士始終無法鼓起勇氣,進行最後的步驟。 那就是舉行葬禮。 身為全世界最惡名昭彰連續殺人兇手的唯一小孩,爵士從小就深入了解死亡的種種機制和成因。但是說來奇怪,他之前從來沒有參加過葬禮。 就某種層面來說,這是一種詩意的正義:爵士的老爸比利.丹特手下的許多被害人,也都舉行過沒有屍體的葬禮。當然,那些被害人會有更多人來送葬。而比利的妻子珍妮絲.丹特,她的葬禮只有不到一打人參加。至於媒體,幸好都被擋在墓園的大門外。 今天不會有人為珍妮絲.丹特而哭。她沒有兄弟姊妹,雙親也老早過世。據爵士所知,她沒有任何朋友還住在婁波納,至少他們宣佈要舉行葬禮後,沒有人跑來自稱是他母親的朋友。爵士猜想這樣也很合理;當初她孤單地消失了,現在她也會孤單地被埋葬。 爵士的女朋友康妮站在他旁邊,緊握住他的手。站在他另一邊的紀威廉.譚納是婁波納的警長,也是四年多前將比利.丹特繩之以法的人。他同時還是爵士生活中最接近父親形象的人,比利要是知道,大概會嘲笑其中的諷刺意味。這個狀況正好符合比利的幽默感。 「親愛的天主,」神父說,「懇求在您的國裡繼續照看我們親愛的姐妹珍妮絲。她已經離開我們好一段時間了,啊天主,我們知道您這段時間也一直在照看著我們。現在我們懇求您在我們為她悲傷之際,也繼續照看我們。」 爵士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奇怪的狀態,希望眼前這件事盡快結束,期待著神父趕緊把一切進行完畢,放他們所有人離開。自從兩個月前婁波納遭到「印象派」(一個崇拜比利.丹特的模仿者)攻擊、然後比利越獄成功後,爵士就感覺到一種迫切的需要,想把他過去的一切盡量封鎖起來。他知道未來將會有可怕的報應(比利越獄後一直沒有消息,但這個狀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的),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過去做個了斷。終於承認他母親的死亡,就是他到目前為止所採取最重大的一個步驟。 爵士不在乎要用哪種宗教的儀式埋葬他母親;但是鎮上教堂的麥坎神父是最願意幫他主持葬禮的,於是爵士就採取了天主教的儀式。現在,正當神父單調的聲音說個沒完之際,爵士想著自己當初是不是該找個比較不囉唆的宗教。他嘆了口氣,握緊康妮的手,往前盯著棺材。裡頭裝了幾個嶄新的絨毛玩具,類似爵士記憶中小時候他母親買給他過的那些。另外裡頭還放了爵士烤好的一批檸檬糖霜杯子蛋糕。那是他對於母親最深刻的記憶——她以前常烤檸檬糖霜杯子蛋糕。他可以舉行個宗教儀式、立塊墓碑就好,但他希望有一整套葬禮,能有完整的體驗。他想親眼見證,名副其實地埋葬自己的過去。 這是多愁善感嗎?大概吧。那又怎樣?把記憶和感傷全部埋葬,然後繼續往前走。 他知道,在墓園周圍,部署了超過一打的警察和聯邦探員。有關當局一聽說爵士打算要替他母親舉行葬禮,就堅持要來監視,確定(或只是希望)比利會無法抗拒這個機會,從隱匿狀態中浮現出來。這是浪費時間,爵士一直這麼告訴他們,但他的堅持有如拿著長柄大錘去敲打潮浪,一點用處都沒有。 像葬禮這樣無趣又可預測的事情,比利絕對不會冒險出現的。他以前偶爾會參加他被害人的葬禮,但那是在新聞節目把他的臉傳遍全世界之前。「屠夫比利」太聰明了,不會在這裡秀出他那張有名的臉,也不會出現在任何地方。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監視,」一個聯邦調查局探員曾告訴爵士,而爵士只是聳聳肩說,「你們想浪費納稅人的錢,大概也是你們的特權。」 神父終於說完了,然後問在場有沒有誰想來墳前說些話,擺明了看著爵士。但爵士沒什麼要說的,至少不是在公開場合。他好幾年前就已經接受母親的死。如今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 然而,讓他驚訝的是,神父點點頭,指著爵士的肩膀後方。爵士和康妮都轉頭——他也看到她一臉驚訝——望著爵士最要好的朋友霍伊.葛司登小心翼翼地穿過紀威廉和爵士之間,刻意避開爵士的目光。他穿著一身黑西裝,打著樸素的橄欖綠領帶,十七歲就有兩百公分的身高,讓霍伊看起來就像爵士印象中海地巫毒教的枯瘦死神「星期六男爵」(Baron Samedi)的模樣,只不過是個白人男孩版。那件西裝外套對於四肢長得荒謬的霍伊來說有點太短了,露出至少兩吋長的白襯衫袖口和蒼白的手腕。 「我叫霍伊.葛司登,」霍伊走到墓碑旁之後便開口說。爵士差點爆笑出來。在場每個人都早就知道霍伊是誰了。「我不認識丹特太太。但我只是真心覺得,當你埋葬某個人,要道別的時候,你就該說點話。而我想,身為爵士最要好的朋友,這就是我的責任。」霍伊清了清嗓子,這才第一回看了爵士。「別火大,老哥,」他誇張地用氣音說。 在場的人紛紛笑出聲來。康妮搖著頭。「這小子……」 「總之呢,」霍伊繼續說。「重點是:我小時候老是被欺負。我有血友病,所以隨時都得很小心,加上我個子又高瘦得像根四季豆,那就是成天自討苦吃,懂吧?但願我能告訴你們,說丹特太太生前對我很好,說在我經歷這一切的時候,她總是對我講一些好心和鼓勵的話,但就像我之前說過的,我不認識她。等到我認識爵士時,她已經,呃,不在了。 「不過我要講的重點是,雖然我覺得很明顯,但有件事還是得有人說出來。我們都知道,呃,爵士的老爸不是什麼好榜樣。但是我大概十歲的時候,有天幾個小孩又照著老慣例,跑來戳我的手臂戳得很高興。然後爵士出現了,他個子比其他人都小,對方人數又比較多,而且,我們就面對現實吧——我根本幫不了什麼忙——」 另一波笑聲響起。 「可是爵士就跟那些王八蛋打了起來——對不起說粗話,神父。他就是跟他們打架,狠狠踢了他們的,呃,臀部,我知道這種行為不太有基督徒精神,但我要告訴你們,從我的位置看過去,那幅景象真是美好。而我想,我之前提到過很明顯的事情,就是我從來不認識丹特太太,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個好人,因為我很確定比利.丹特不會教爵士看到血友病患者被欺負,就出手去援救。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我想念你,丹特太太,即使我從來沒見過你,但我真希望能認識你。」他正要走進人群中,又忽然停下來說,「呃,上帝保佑你,還有阿門,還有其他等等。」這才匆忙回到自己的位置。 然後棺材降入墓穴中,墓碑上刻著珍妮絲.丹特,母親。沒有日期,因為爵士不確定比利到底是什麼時候殺了她的。 他從神父手中接過小鏟子,鏟了些泥土扔進墓穴,發出嘩啦啦的聲響。 接著,紀威廉和康妮和霍伊也照做。然後他們後退,好讓墓園工人接手把泥土填入墓穴。 工人們鏟了泥土,扔到那具沒裝著他母親屍體的棺材上,此時爵士意識到自己直盯著那些鏟子看,直到康妮戳戳他,他才別開眼睛。她朝他遞出一張面紙。 「做什麼?」他問,但仍不自覺地伸手接過來。 「你的眼睛,」她說,然後爵士才很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正在哭。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謀殺遊戲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謀殺遊戲
這位是爵士.丹特:全世界最惡名昭彰的連續殺人兇手的兒子。
幾個月前,爵士.丹特協助婁波納警方逮到化名為「印象派」的連續殺人兇手。此後每一天,爵士都滿心罪惡感,因為他知道父親的越獄成功,自己也有責任。現在比利.丹特依然在逃,準備要再度殺人。
爵士聲名大噪,名氣傳到了他寧靜的家鄉之外的遠方。一個堅決的紐約市警探跑來敲爵士的門,要求他協助一個新案子,爵士無法拒絕。帽狗兇手造成了紐約市的恐慌,警方也非常擔心。
爵士已經解開過一宗犯罪,但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幾個無辜的人因為他而被謀殺。這回的帽狗兇手,會是他贖罪的方式嗎?或者爵士會陷入一個兇手的謀殺遊戲中?
而且在某處,比利正在觀察……以及等待。
備受讚譽的作者貝瑞.萊加,在令人心跳停止的《我,專獵兇手》之後推出本系列作,而這回,賭注和屍體數量都更高了!
作者簡介:
貝瑞.萊加 Barry Lyga
著有多本備受讚譽的青少年小說,包括處女作The Astonishing Adventures of Fanboy and Goth Girl,他現在對於丟棄人類屍體的知識已經過分豐富了。現居紐約,網站是www.barrylyga.com
譯者簡介:
尤傳莉
生於台中,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著有《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政治、權力》,譯有《達文西密碼》、《天使與魔鬼》、《依然美麗》、《過得還不錯的一年》、《骸骨花園》、《喀邁拉空間》等小說與非小說多種。
TOP
章節試閱
1
她尖叫過,但是從來沒有哭。 有關這一位,他將會記得的就是這一點,他心想。不是她頭髮或眼珠的顏色。不是她歪斜的臀部,嘴唇的弧度。完全不是這一類事情。甚至不是她的名字。 她尖叫過。朝著星光點點、無動於衷的天空尖叫。他們全都會尖叫,每個都會。 但是她沒有哭。 反正哭也沒有用。他無論如何都會殺了她,所以她做什麼都沒有用。但這件事他老是忘不掉:沒有眼淚。沒有哭泣。女人總是愛哭。那是她們最終的、最好的武器。只要一哭,男朋友就會道歉,丈夫就會把她們擁入懷中。只要一哭,老爸就肯為她們的高中舞會禮服多花點錢。 她尖...
她尖叫過,但是從來沒有哭。 有關這一位,他將會記得的就是這一點,他心想。不是她頭髮或眼珠的顏色。不是她歪斜的臀部,嘴唇的弧度。完全不是這一類事情。甚至不是她的名字。 她尖叫過。朝著星光點點、無動於衷的天空尖叫。他們全都會尖叫,每個都會。 但是她沒有哭。 反正哭也沒有用。他無論如何都會殺了她,所以她做什麼都沒有用。但這件事他老是忘不掉:沒有眼淚。沒有哭泣。女人總是愛哭。那是她們最終的、最好的武器。只要一哭,男朋友就會道歉,丈夫就會把她們擁入懷中。只要一哭,老爸就肯為她們的高中舞會禮服多花點錢。 她尖...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貝瑞.萊加 譯者: 尤傳莉
- 出版社: 春天 出版日期:2018-02-01 ISBN/ISSN:978957960919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80頁 開數:15*21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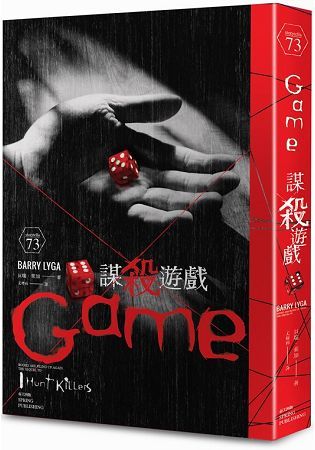
 2018/07/05
2018/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