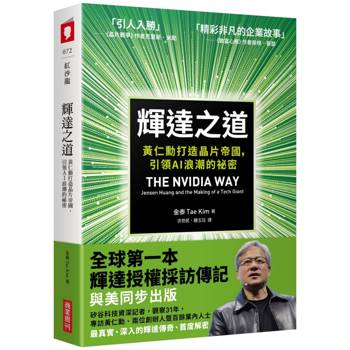第一章
在一個晴朗的四月午後,攀附在大貨車頂的無心被交警發現了。當時他被牽連不清的繩網牽扯糾纏了住,否則憑著他的身手,他絕不會趴在車上束手就擒。大貨車滿載貨物,長寬高已經幾乎相等,跳車等於跳樓。交警費了老大的勁,蹬著梯子往車上爬。司機早下了車,手搭涼棚往上望,一邊望一邊和身邊的交警解釋:「我真不認識他,我能把我認識的人往車頂上放嗎?哎喲我操,你們說他是怎麼上去的?」
爬上車頂的交警解開了無數半死不活的大繩扣,讓無心的胳膊腿兒得了自由。無心跪坐在了大貨箱上,怔怔的望著面前的小交警。小交警有懼高症,一邊四腳著地的往後倒退,一邊怒道:「你是猴兒哇?」
話音落下,交警眼前一花,無心沒了。
然後小交警在自己的驚叫聲中,看到一個灰撲撲的人影刺斜裡穿越國道,剎那間衝入路旁樹林,從此消失無蹤。
無心一路狂奔,在穿越了一片小樹林後,他上了一條柏油路。路邊立著個大鐵牌子,上寫六個大字:火星鎮歡迎您。
無心仰頭望著牌子,又發了半天的呆。簡化字在他眼裡總像是缺胳膊少腿,怎麼看怎麼不對勁,六個字讓他翻來覆去讀了好幾遍。末了心裡明白了,他惶惶然的邁開步子,向前走入了火星鎮。在大興安嶺的深山老林裡隱居了將近四十年,如今驟然回歸人間,他發現人間竟然大大的變了模樣——變化之劇烈,簡直要讓他驚恐了。
山外的人們已經不認得他手中僅有的幾張舊人民幣,糧票也成了天方夜譚般的往事。他的假介紹信假證明更是一分錢不值,現在的人可以隨便走隨便住,而且都有身分證。他穿著一身幾近襤褸的舊軍裝走在人群中,引得人們紛紛對他行注目禮,看一個濃眉大眼的小白臉子,竟然穿戴成了乞丐模樣,而且還是怪模怪樣的乞丐,像是從革命時期穿越而來的。
他難得的懵懂怯懦了。扒著一輛運輸木材的火車走了一段路,火車到站,他茫茫然的也到了站。在火車站外爬上一輛大貨車。貨車司機無知無覺的上了路,帶著他疾馳了將近一天,直到交警發現了他。
無心此刻饑腸轆轆,決定去火星鎮打食。千變萬化的新人間雖然嚇得他左一跳右一跳,但還是要比山裡強。白琉璃徹底被大貓頭鷹哄住了,一鬼一妖合作欺負他一個,橫豎知道他死不了,所以下手格外狠辣。大貓頭鷹當年一臉忠厚老實相,原來也不是個好東西。山中日月成全了一個他,幾十年中他妖術大有長進,已經敢和無心蹬鼻子上臉了。
於是無心自作主張的下了山,不和他們過了。
無心沿著柏油路往前走,路是好路,路兩邊有田地有房屋,乃是火星鎮周邊的一處大村莊。此時正是四月時節,待種的田地都被翻過了,黑土被曬了一整天,此刻已經乾爽鬆軟。無心一邊走一邊東張西望,心想野地裡不會有野菜野果,自己還是得往人的身上打主意。要說人,眼前倒是有現成的一個,看背影是個年輕人,打扮得西裝革履,然而雙臂環抱在胸前,腰也弓著,顯然是在摟抱著什麼。年輕人步伐匆匆,越走越快;無心連跑帶跳的追上了他,側著臉想要和他搭話,然而定睛一瞧,他心中一驚,原來青年雙眼通紅,滿面淚痕,嘴唇緊緊的抿成了直線。西裝前襟只繫了一枚鈕扣,下襬偶爾隨風飄起,無心瞪大了眼睛,懷疑自己是看到了一圈炸彈。
看到的是一圈,看不到的,被青年雙臂環繞著的,不知還有多少。一條穿著桃紅背心的白哈巴狗從前頭顛顛的來了,伸著舌頭且顛且喘,又對著青年「汪」了一聲。
未等白狗閉嘴,柏油路上爆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巨響。無心、青年、白狗瞬間化為烏有,道路兩邊的大樹也被氣浪摧成了骨斷筋折。附近的房屋玻璃全起了共鳴,連遠方一座小樓內的史高飛都被震得打了哆嗦。一哆嗦,手裡的毛巾紙失了準頭,他上面望著電腦螢幕裡的南波杏,下面一波接一波的射了一褲子。
一驚之後,史高飛慌忙低了頭。褲子被他褪到了大腿處,如今前門拉鍊已經被他的萬子千孫徹底糊住。匆匆忙忙的用紙擦了,他心懷鬼胎的提了褲子往窗口跑。「嘩」的一聲拉開拉窗,他探出上半身向外張望,想要查看巨響的來源。然而窗外風景一如往常,只有一隻大灰雀趁虛而入,撲啦啦的飛進了房內。
史高飛來不及驅趕鳥類。轉身出了房門穿越客廳,他推開向外的樓門,幾大步竄進了院子裡。院子是大院,一半鋪了水泥地,一半種了花花草草。另有一棵吃裡扒外的老果樹緊挨院門,每年都要無私的向院外奉獻出幾枝子沙果。史高飛別有心事,一味的只往大門口跑。然而未等他打開左右合攏的黑漆鐵柵欄門,他的眉心之間忽然落了一滴暖暖的雨。下意識的抬手一摸,他隨即對著手指頭直了眼——不是雨,是血!
猛然抬頭向上望去,在老果樹的密集枝杈之間,他看到了一顆白色的狗頭。狗頭保持著齜牙咧嘴的神情,脖子往下一無所有,只垂了絲絲縷縷的幾條鮮紅筋肉。狗嘴毫無預兆的上下一張,一小塊粉紅色的肉垂直落到了黑土地上。
在和狗頭對視了片刻之後,史高飛和狗頭一樣齜牙咧嘴了,噁心得恨不能就地嘔吐一場。舉起一根竹竿捅下狗頭,他揪著狗耳朵將其扔到了院外。隨即跟著狗頭一起出了門,他一路小跑的看熱鬧去了。
史高飛本名史鴻鵬,乃是本鎮首富之子。他幼年兼生了傾國傾城的貌以及多愁多病的身,把他上面的一個姐姐比得狗屁不如。不過一個男孩子一味的嬌弱也不是長久之計,後來經過高人相看之後,他換湯不換藥的改了名字——由具體的「鴻鵬」,改成了抽象的「高飛」。
名字一改,果然立竿見影,史高飛改頭換面,從小病殃子變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精神病患者。從十五歲瘋到了二十五歲,他堅信自己是一名外星遺孤,有朝一日必將回歸母星。他媽趙秀芬為他嚎得肝腸寸斷,並且在丈夫史一彪心中徹底失寵——當年在趙秀芬年輕貌美之時,史一彪忘了趙秀芬的媽和妹妹曾經先後聲稱自己是狐狸大仙和九天神女。趙家八輩貧農,全國勞苦大眾都翻身了他家也沒翻身,留給子孫後代唯一的遺產就是精神病。史一彪重男輕女,恨不能練就神功,把兒子的精神病轉給女兒。女兒三十了,生得花容月貌,嫋嫋娜娜,曾經是火星鎮的林黛玉,還念過三年大專,可如今硬是沒人敢娶,因為都怕她會隨了她媽,再養出個瘋兒癡女。
史一彪對於家庭徹底失望,尤其恨老婆恨得牙癢,常年不肯回家。他身為本鎮的娛樂業巨頭,經營著今夜星辰夜總會,明日之星KTV,快樂時光咖啡屋,以及酷龍連鎖網咖三家。既然擁有如此可觀的家業,他自然不會無處落腳。而趙秀芬進入更年期,天天在家要死要活,專跟著女兒較勁。女兒名叫史丹鳳,既沒事業也沒愛情,連她媽都不肯高看她,甚至認為她一個人也挺好,將來正好照顧兒子一輩子。反正兒子瘋得全鎮出名,想必也找不到媳婦伺候他一生。史丹鳳看她媽把心偏到了胳肢窩裡,自然也有意見。總而言之,史家全體成員之中,只有史高飛的痛苦程度較輕——他一心等待母艦降臨接他回家,對於家中三個地球人,他一般懶得搭理。
在柏油路上的村民群中湊了半天熱鬧,因為警察封鎖了現場,所以他也沒看到什麼,只知道路面被炸出了一個大坑。傍晚時分,觀眾們紛紛回家做飯,他也跟著回了自己所住的小樓。小樓一共有二層,當初史一彪想在農村發展一點副業,才蓋起了小樓大院。後來副業胎死腹中,小樓空著沒人住;而史高飛去年年末被家人強行送進精神病院住了一陣子,出院之後和地球人越發勢不兩立,索性獨自進了村,要安安靜靜的過幾天田園生活。
沒滋沒味的鎖了院門進了樓,他穿過客廳往臥室裡走,一邊走一邊自己嘆息:「我還以為是飛船來了呢!」
電腦螢幕上的影片已經播放完畢,不速之客大灰雀也早沒影了。他牢牢騷騷的蹲到電腦桌下,想要清理白天亂扔的毛巾紙團。不料在一團半乾半黏的毛巾紙下,他意外的發現了一枚大豆子。此豆十分古怪,竟然是個心形,如果把它比作人的話,必定是個連體嬰。史高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道豆子也會畸形。捏著豆子端詳了半天,他捫心自問:「我白天射豆子了?」
隨即他把褲子一脫,仔細檢查了自己的先天條件,最後認定這應該是不可能,因為他的那條播種的道路長而狹窄,不足以孕育出尺寸如此壯觀、形象如此美好的種子。拈著豆子站起身,他忽然打了個激靈,心裡又生出了邪主意:莫非方才自己的臥室內有人來過了?莫非這豆子承載著母星傳遞給自己的訊息?光天化日的,總不會無端的發生大爆炸,必有玄妙在裡面!
可他馬上又犯了難:母星的使者也太不體諒人了,他在地球過了二十多年,現在哪裡還能和同類心有靈犀?掂著豆子出了許久的神,他坐臥不安,實在是揣摩不出豆中的深意,又不敢貿然把豆子剖開或者嚼碎。抓心撓肝的熬到午夜,他終於浮想聯翩的思索出了眉目:「這是一顆種子啊!」
午夜時分,眾人皆睡,唯有史高飛獨醒。站在土質最為肥沃的老果樹下,他揮舞著一把大鐵鍬,挖了個半公尺多深的圓坑。恭而敬之的把心形豆子放入坑底,他雙膝跪地,親自伸手捧土填坑,一邊填一邊又默默祈禱:「種子啊,你快長大快顯靈吧。他們都不相信我的話,還喪心病狂的誣陷我,說我是精神病。你一定要長成個了不起的寶貝,好向他們證明我的身分!」
虔誠的撒下最後一把土,他雙手合十又拜了拜。最後意猶未盡的站起身,他垂著兩隻泥手仰望蒼穹,心想滿天的星星有明有暗,不知道哪一顆才是我的家。人在異星,沒個知音,真是遭罪啊!
村口柏油路上的爆炸案上了各大網站的頭條,捎帶著火星鎮一起出了名。一個月後,案子基本破了,原來是場未遂的情殺——一男一女搞對象搞出了仇,男方是個亡命徒,綁了一身炸藥往女方家去,本意是要趁著傍晚女家人齊全,點燃導火線來個一鍋端。沒想到炸藥本身出了問題,走到半路,自行炸了,炸得什麼都不剩,導致警察須得四處走訪調查,一點一點的拼出事實真相。
村裡常年太平,近幾年連去世的老人都少有,所以一樁爆炸案足以讓村莊沸騰許久,唯有史高飛極其冷靜,滿眼滿心只裝著他的種子。在等待種子發芽的期間裡,他連愛情動作片都沒心思下載了,成天無欲無求的蹲在樹下,直勾勾的只盯著土地使勁;飯也時常是一頓管一天,餓得他一百九的身高只有七十五公斤,扛著寬肩膀垂著頭,他支起後背兩大片肩胛骨,乍一看好像一隻禿毛又折翼的大天使。
勤勤懇懇的澆了兩個月的水,他天天對著一片土地望眼欲穿。如此熬到了七月,頭頂的果樹已經結出了纍纍的小綠果子,可是他的種子依舊毫無動靜。
他等不得了。在一個狂風大作的夜晚,他欲哭無淚的蹲在樹下,預備對種子做出一番控訴,然後把它挖出來就地踩扁。然而在他頂風開口之前,空中忽然裂過一道閃電。隨即在震天撼地的雷聲中,史高飛睜大眼睛,發現一貫平坦的地面竟然隱隱鼓突,彷彿是有什麼東西將要破土而出了!
顫巍巍的伸出一隻手,史高飛輕輕的撥開了最表面的一層浮土。浮土之下露出了一小塊粉紅的皮肉,皮肉中鑽出幾根東倒西歪的白毛,正在暴雨來臨之前的疾風中微微抖動。
史高飛忽略了地上的風與天上的雷。他屏住呼吸張大了嘴,用十根手指又挖又掘。末了在第一顆大雨點子砸向他時,他從土裡刨出了一隻半人長的大毛毛蟲。「撲通」一聲跪在泥水之中,他激動得又哭又笑,又捶大腿又甩泥巴。原來母星的同胞並沒有忘記他,原來同胞所給他的,真是一粒種子!
脫下身上的T恤裹住大毛毛蟲,他在大雨之中站起了身,抱著毛毛蟲趿著人字拖,他一路劈里啪啦的跑進樓裡去了。
史高飛盤腿坐在臥室內的大床上,一件襯衫被他當成圍裙繫在了腰間。大毛毛蟲剛被他送到浴缸裡洗乾淨了,此刻正長條條的橫在他的大腿上,大腿瘦成了兩根粗大的骨頭棒子,越發襯得大毛毛蟲粉嫩嫩軟顫顫,彷彿一把能掐出水。只是蟲體表面凹凸不平,並且白毛叢生。
史高飛認為它很可愛,連它身上甜腥的氣味都忽略不計了。
從頭到尾的摸了一遍,史高飛沒有找到它的頭也沒有找到它的尾,同時感覺毛毛蟲是軟中帶硬,彷彿嫩肉裡面也有骨骼。手指劃過蟲身,史高飛的動作忽然一滯,因為感覺大毛毛蟲彷彿是在他的腿上抽搐了一下。
慢慢的俯下身去,他幾乎把鼻尖湊上了一叢白毛:「寶寶,你怎麼了?疼了?還是怕了?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爸爸。我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二十五年,是個老地球人了。以後我會保護你的,不過你是打算長住呢?還是要帶我回家?」
話音落下,他感覺自己說的沒毛病。從把毛毛蟲抱進樓內開始,他的腦筋就像上足了發條一樣,一直沒停轉:臥室這麼寬敞,豆子落到哪裡不好,非要擠到髒兮兮的衛生紙下面?可是如果把豆子想像成一顆來自母星的卵子,一切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非得如此不凡的大號卵子,才能自行找到他的衛生紙受精,並且在兩個月內長成半人多長。
所以他封了自己為毛毛蟲之父。雖然他是這樣的,他的毛毛蟲寶寶是那樣的。
史高飛徹夜不眠,想要找到毛毛蟲的嘴。沒有嘴,他怎麼給牠餵食呢?
徒勞無功的忙了一夜,他一個哈欠都不打,腦筋繼續高速運行。既然實在是找不到嘴,那索性就把牠當成花花草草來養。把它埋回土裡是捨不得的,於是他無師自通的開始進行無土栽培。蓄了一浴缸的溫水,他找出家中所有的維他命藥片,全磨碎了溶入水中。自認為一缸溫水已經十分富有營養了,他調動了他的大長胳膊大長腿,顫巍巍的把大毛毛蟲放進了浴缸裡。
然後他不走,捧了一臺筆記型電腦坐在浴缸旁,他為大毛毛蟲播放鋼琴曲,權當遲來的胎教。紋絲不動的從早坐到晚,他直到餓得眼前發黑了,才東倒西歪的起了身,想要找點食吃。家裡已經沒有存糧,他把樓門院門裡三層外三層的鎖嚴實了,草上飛似的跑去村口超市,買了許多餅乾泡麵。氣喘吁吁的回了家,他進門之後先往浴室跑,見大毛毛蟲還怡然自得的躺在水裡,才長長的吁出一口氣,一顆心也落回了腔子裡。
史家的大門又關上了,院裡無論晝夜,永遠清靜的連個人影都沒有。村民們知道史高飛的底細,平日恨不能繞著史家走路,他是死是活,自然也無人關心。如此過了一個多月,史家門外終於有人駐了足——史丹鳳來了。
史丹鳳穿著一身雪紡連身裙,為了防曬,頭上又戴了一頂大黑簷遮陽帽。上下活動的帽簷比臉還大,放下來把臉扣了個嚴絲合縫。窈窈窕窕的推著一輛小機車,她看身體飄飄欲仙,看腦袋神祕莫測,正是史高飛最瞧不上的人類形象。抬手連摁了幾下大門門鈴,她單手扶著機車,車後座上捆了個大紙箱,箱子裡是她給弟弟帶的援助物資。長姐如母,雖然史一彪趙秀芬二人偏心偏得人神共憤,但是她身為大姐,並沒有遷怒於弟弟的打算。好好一個弟弟,男明星似的英俊瀟灑,偏偏瘋頭瘋腦的不說人話,她看在眼裡,疼在心裡,連自身的痛苦都暫時淡忘了。
門鈴響了一長串,樓內絲毫沒有回應。史丹鳳從身上的小皮包裡掏出手機,正想給弟弟打個電話;不料未等她開始按鍵,身後忽然起了一串叮叮鈴鈴的響動。回頭一瞧,她看到了一頭大汗的史高飛。而史高飛騎著自行車猛一按剎車,見了鬼似的瞪著他姐,也不打招呼,只欲言又止的張了張嘴。
史丹鳳收起手機,張口就是牢騷:「小飛,你剛跑哪兒去了?我還當我撲了個空。大熱天的,我來一趟是容易的?我告訴你啊,現在爸媽慣著你,我可不慣著你。有本事你滾回太空去,否則我作為你姐,我就敢揍你!」
史高飛握著車把,支支吾吾的不肯靠近她:「我……姐,妳來幹什麼呀?」
史丹鳳從鎮子騎到村裡,快被曬得融化噴火。此刻伸手一拍車後座的紙箱,她躲在黑面罩後面急赤白臉:「你快開門!冷凍的餃子快要化了!」
史高飛下了自行車,猶猶豫豫的推車上前,一邊走一邊把手伸到短褲口袋裡掏鑰匙。史丹鳳一眼看清了他掛在車把兩端的大包裝袋,立刻又起了高調:「你買嬰兒奶粉了?」
史高飛停好自行車,慢吞吞的去開大門鎖頭:「嗯……」
史丹鳳擁有賢妻良母的一切素養,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她當即針扎火燎了:「你多大了還喝嬰兒奶粉?十五塊錢一袋的不夠你喝嗎?嬰兒奶粉一桶得一百多人民幣吧?」
史高飛開了院門,轉身去推自行車:「兩百多呢,我挑了最好的買。」
史丹鳳雙臂運力,把機車推入院內:「小飛,你個不聽話的,氣死我了。」
史高飛也跟著他姐進了院。摘下車把上的兩個大紙袋,他把他姐帶入樓內。史丹鳳記得弟弟一貫很講衛生,然而此刻進了門,她猝不及防的吸了一鼻子怪味——又甜又腥的,不算臭,然而越聞越不舒服。客廳裡擺著舊沙發和舊茶几,她一邊催促史高飛把紙箱裡的冷凍食品往冰箱裡放,一邊摘了遮陽帽坐上沙發。低頭摸了摸皮沙發的表面,她摸到了幾根細長的白毛。
「小飛!」她高聲質問:「你養狗了?」
史高飛離開廚房進入客廳,意意思思的站在沙發一旁:「沒、沒有。」
史丹鳳一抬手,向他展示白毛:「你養狗我不管你,可是千萬別讓狗咬了。」
史高飛心神不寧的看著她,鼻子裡「嗯」了一聲作答。
史丹鳳不和他一般見識,起身往臥室裡走,要給他收拾房間,順便洗洗刷刷。雖然家裡有洗衣機,但是史丹鳳對洗衣機信任的有限。來都來了,她總要給弟弟出把子力氣。然而未等她走到臥室門前,史高飛已經背靠房門,阻住了她的去路:「姐……不用打掃了。」
史丹鳳看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不是個正經顏色,不禁起了疑心:「小飛,你緊張什麼?屋子裡有什麼怕人看的?」
史高飛義正詞嚴的正視著她:「沒有!」
史丹鳳伸手拽他,拽了一下沒拽動:「真沒有?你讓我進去瞧瞧!」
史高飛提高聲音:「不行!」
他嗓門大,中氣十足的吼出一聲,把史丹鳳嚇了一跳。吼聲過後是短暫的寂靜,史丹鳳的耳朵忽然一動,彷彿聽到房內有活物在唧唧的叫。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無心法師第四部(上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0 |
中文書 |
$ 190 |
神怪/推理 |
$ 190 |
推理/驚悚小說 |
$ 204 |
靈異/推理 |
$ 216 |
幻奇冒險 |
$ 216 |
文學作品 |
$ 25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無心法師第四部(上卷)
無心待在大興安嶺四十年,
和白琉璃吵架下山後,
才發現世界已經跟他想像的不一樣了!
可惜還來不及體驗一番,
一顆炸彈將他粉身碎骨,
他又得從一塊肉的狀態開始長起。
不過這一回,他的運氣不錯。
一個自認是外星人的精神病患史高飛發現了他,
把他當成兒子,好吃好喝的供養長大,
不僅如此,他的「爸爸」還有一個有點勞碌命,
卻單身成熟的美麗姐姐史丹鳳,
可以讓他三不五時,吃點美女的豆腐。
正當他覺得生活真幸福之時,
「爸爸」卻帶著他離家出走了。
他們在新的落腳地遇到一個神棍,
三人合夥正準備在風水捉鬼界闖出名號之時,
第一個送上門來的案子,卻凶險至極……
本書特色
◎感動數億觀眾的電視劇原創小說,精采完結篇堂堂登場!
◎驚心動魄的情節,刻骨銘心的愛戀,讓人讀了便難以釋卷!
光怪陸離的現代世界,雞飛狗跳的捉妖日常。
作者簡介:
尼羅,筆鋒詭譎老辣,於不經意間讓人捧腹大笑。筆下人物嬉笑怒罵皆趣味。
喜歡寫美人之間的愛恨情仇,喜歡寫縱馬江湖、快意人生的傳奇故事。
主要作品有《無心法師》《風雨濃胭脂亂》《妖僧與妖》《殘酷羅曼史》《義父》等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在一個晴朗的四月午後,攀附在大貨車頂的無心被交警發現了。當時他被牽連不清的繩網牽扯糾纏了住,否則憑著他的身手,他絕不會趴在車上束手就擒。大貨車滿載貨物,長寬高已經幾乎相等,跳車等於跳樓。交警費了老大的勁,蹬著梯子往車上爬。司機早下了車,手搭涼棚往上望,一邊望一邊和身邊的交警解釋:「我真不認識他,我能把我認識的人往車頂上放嗎?哎喲我操,你們說他是怎麼上去的?」
爬上車頂的交警解開了無數半死不活的大繩扣,讓無心的胳膊腿兒得了自由。無心跪坐在了大貨箱上,怔怔的望著面前的小交警。小交警有懼高症,...
在一個晴朗的四月午後,攀附在大貨車頂的無心被交警發現了。當時他被牽連不清的繩網牽扯糾纏了住,否則憑著他的身手,他絕不會趴在車上束手就擒。大貨車滿載貨物,長寬高已經幾乎相等,跳車等於跳樓。交警費了老大的勁,蹬著梯子往車上爬。司機早下了車,手搭涼棚往上望,一邊望一邊和身邊的交警解釋:「我真不認識他,我能把我認識的人往車頂上放嗎?哎喲我操,你們說他是怎麼上去的?」
爬上車頂的交警解開了無數半死不活的大繩扣,讓無心的胳膊腿兒得了自由。無心跪坐在了大貨箱上,怔怔的望著面前的小交警。小交警有懼高症,...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尼羅
- 出版社: 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17-12-11 ISBN/ISSN:978957961403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大眾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