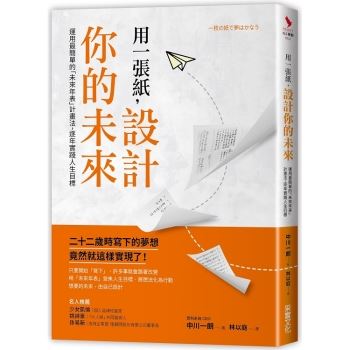無心被綁架了。
就在史高飛與史丹鳳急白了頭的時候,
無心卻被人關在冰櫃裡,一路送到了雲南。
綁架他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身體裡擁有兩個靈魂的小老頭。
一個靈魂,是幾十年前有過緣份的小丁貓。
一個靈魂,則是對他又愛又恨,殘忍嗜殺的岳綺羅。
無心讓人折磨得不成人形,
覺得自己對「人」這種生物,已然不敢接近之時,
史家姐弟卻不遠千里地來救他。
不僅如此,就連白琉璃也下了山來,
為了他所受到的殘忍對待,決心幫他復仇。
這場跨越百年的恩怨情仇,
將在雲南的深山野林當中畫下句點。
而無心以他的不死之身,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的存在,
卻能在這現代社會當中,
找到屬於自己可以依靠的港灣,屬於他自己的「家」。
本書特色
◎感動數億觀眾的電視劇原創小說,精采完結篇堂堂登場!
◎驚心動魄的情節,刻骨銘心的愛戀,讓人讀了便難以釋卷!
光怪陸離的現代世界,雞飛狗跳的捉妖日常。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無心法師第四部下卷 完的圖書 |
 |
無心法師第四部下卷 完 作者:尼羅 出版社: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17-12-1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56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9 |
幻奇冒險 |
$ 190 |
中文書 |
$ 190 |
神怪/推理 |
$ 190 |
推理/驚悚小說 |
$ 204 |
靈異/推理 |
$ 216 |
文學作品 |
$ 25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無心法師第四部下卷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