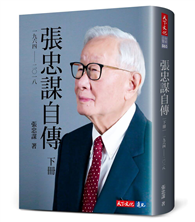在萬錦榮的帶領之下,
江爍、秦一恒與白開組成的三人小組,
到達了一個藏匿於深山之中的「圍城」。
這城從進入開始,就充斥著各種謎團,
人餌拖出的道路,渴死的屍體,再度出現的壁畫,
三人憑空猜想背後的關聯,卻依然猶如身處雲裡霧裡。
然而就在此時,那眾多乾涸而死的屍體,
竟像活了一般,開始攻擊他們!
秦一恒與白開為了保護江爍,受到重傷。
而敵我難分的萬錦榮,
卻指引了江爍進入一個懸空的櫃子當中避難。592
江爍在萬錦榮刻意的引導當中,
打開了一道不知關押了什麼的鎖,
而想像中被關押的怪物尚未出現,
這神祕的空間竟憑空出現大水!?
這一次,換他來保護兩個重要的朋友了。
就算耗費他所有的力氣,甚至要付出他的生命。
至少他們可以死在一起。
本書特色
萬眾矚目,詢問度爆表的完結篇,震撼登場!
◎首刷贈品:塑膠書衣
◎華文網路連載最火熱的懸疑小說,在天涯、貓撲、人人網、百度貼吧等網站上瘋狂流傳,引起百萬網友瘋狂追捧,擁有上億的點擊量!
◎書中運用大量的風水奇術、算命占卜、陰兵換魂、驅鬼密術等情節,恐怖懸疑的故事,讓人讀來欲罷不能,無法停止!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凶宅筆記 第五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75 |
二手中文書 |
$ 442 |
華文驚悚/恐怖小說 |
$ 442 |
推理/驚悚小說 |
$ 476 |
小說/文學 |
$ 504 |
華文驚悚/恐怖小說 |
$ 504 |
中文書 |
$ 504 |
文學作品 |
$ 504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凶宅筆記 第五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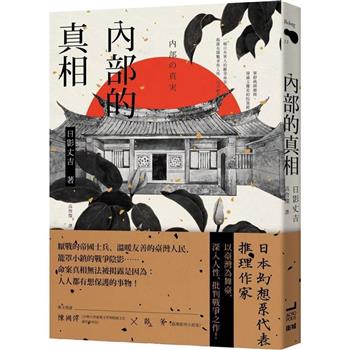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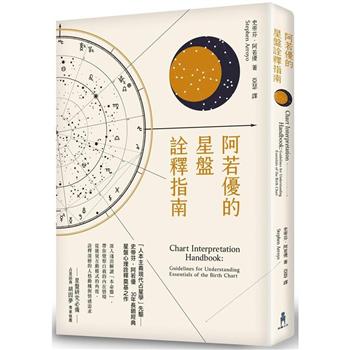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