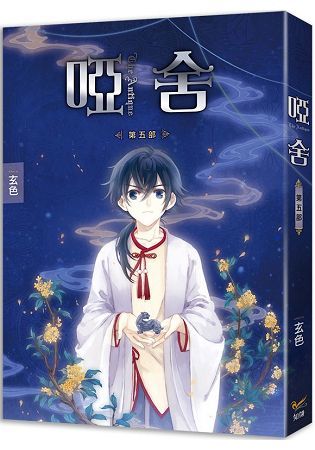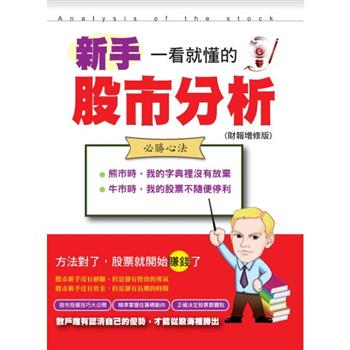它們在歲月中浸染了成百上千年。
每一件,都凝聚著工匠的心血,傾注了使用者的感情。
每一件,都屬於不同的主人,都擁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件,都那麼與眾不同,甚至每一道裂痕和缺口都有著獨特的歷史。
誰還能說,古董都只是器物,都是沒有生命的死物?
這是一本講述古董故事的書,既然它們都不會說話,那就讓我用文字忠實地記載下來。
歡迎來到啞舍,請噤聲……
噓……
玄色
第一章銀魚符
刺耳的鬧鈴聲在屋中響起,湯遠過了好一陣才揉著眼睛從床上爬起來,睡眼惺忪地打著哈欠往廁所走。他動作麻利地踩著小板凳放了水、沖了手、刷了牙、洗了臉後,又拿著梳子對著鏡子扒拉了兩下頭髮,這才滿意地對著鏡子裡那個可愛的小正太露齒一笑。
「臭美什麼呢?快讓地方。」一隻大手毫不客氣地拍上他的頭,破壞了他剛弄好的髮型。
「啊!叔你好壞!」湯遠炸毛,捂著自己的小腦袋從小板凳上跳了下來,氣呼呼地鼓起腮幫子。
「乖,小湯圓,我早餐都買回來了,在餐廳的桌子上,有豆漿、油條、餡餅還有兩碗小餛飩。」醫生完全不把小朋友的小脾氣放在眼裡,悠然地拿起了香皂。
果然他的話音剛落,湯遠小正太就如他所想的那樣,一聲歡呼便衝向了餐廳,隨後就傳來了叮叮匡匡的碗筷聲。
醫生有著些許職業潔癖,導致他在家洗手的時候都喜歡多花費一些時間。當然不至於像進手術室那樣需要八步洗手法,也用不到醫用洗手刷就是了。他低頭仔仔細細地把雙手洗乾淨,洗完再修剪了一下稍微長出來一點點的指甲,這才滿意地用毛巾擦乾。所以等他走進餐廳的時候,發現桌上的早餐已經下去了一小半,湯遠正左手餡餅右手油條吃得狼吞虎嚥。
「慢點吃,細嚼慢嚥對身體好。」醫生暗嘆了一聲,心想這孩子被他從大街上撿到、送到醫院救回來後,也說不清楚自己的身分,只知道自己叫湯遠,有記憶以來就是跟師父一起生活,而他的那個師父也不知去向了。
想到這裡,醫生也不由得暗罵那個不靠譜的師父,這孩子肯定是從小被拐賣的,他甚至偷偷拍了湯遠的照片發到微博上,請網友幫忙擴散下,期望能找到他的父母。可是若是據這孩子的說法,他很小就跟著那個師父了,兩三歲的小孩兒和十歲的小孩兒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找到這孩子父母的可能性很小。
湯遠當時只是被凍得厲害,救醒了之後壓根也沒什麼醫藥費,在醫院也沒辦法安排住院。一般來說按照這種情況,就應該去上報地區派出所警察,開了證明之後聯繫育幼院收留湯遠,然後警方會在龐大的資料庫之中尋找有可能是湯遠父母的人選。
而這是一個漫長的等待過程。
醫生當時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想的,看著神情怏怏的湯遠,就心一軟,跟前來登記資料的警察溝通了一下情況,就讓湯遠先在他家住著了。
好在湯遠特別乖巧,也很懂事,一點兒都不會給醫生添麻煩,甚至還有種在家裡養了寵物等他回家的感覺,讓醫生特別有成就感。當然,說到寵物,醫生至今依舊不習慣那條在他家裡神出鬼沒的小白蛇。
吃油條吃到一半,醫生臉色難看地從褲筒裡拎起擅自爬上他小腿的小白蛇。
「哈哈……小露露本來是在冬眠,可能屋裡暖和,就醒過來了。」湯遠一邊乾笑著,一邊從醫生手裡接過那條通體白色的小蛇。
看著湯遠懷裡那條正懶洋洋吐著紅色信子的小白蛇,醫生心裡不受控制地升起了驚懼之感。他下意識地皺起了眉。
他小時候在鄉下長大,早就見慣了田間流竄的草蛇,已經可以做到熟視無睹了。他從不知道怎麼現在的自己居然還會怕蛇?
可是就算他怕蛇吧,就這樣手指頭粗細的蛇,他一手就能捏死,怎麼還會害怕?太荒謬了吧!
對,蛇是冷血動物,一定是剛剛冷不防地爬上他小腿,那股寒氣激得他嚇一跳而已。
那邊醫生正在給自己找藉口,湯遠就連忙跳下餐桌,抱著小白蛇跑到客廳的角落裡,那裡放著那個古樸的藤編藥簍。湯遠一邊把小白蛇放回去,一邊低聲告饒道:「我的小祖宗唉,求你不要再搞狀況了,萬一這小叔發脾氣,把我們掃地出門了怎麼辦?外面冰天雪地的!你可以冬眠,我沒那能力啊!」
小白蛇優雅地在藥簍裡盤了幾個圈,但並未睡覺,而是略帶高傲地微抬頭,吐出鮮紅色的信子,發出嘶嘶的聲音。
「啊?妳說什麼?我可不像哈利‧波特那樣會爬說語。」湯遠為難地用手指刮了刮臉頰。
小白蛇無語地翻了個白眼。
「難道是餓了?我看師父平時也不餵妳吃東西啊……」說到這裡,湯遠忽然打了個冷顫,因為他想起這白蛇確實是不吃普通東西的,而是偶爾會咬上師父的脖頸,並不是吸血,而是吸食靈氣。現在師父不在,他要找誰給這美女蛇當儲備糧?湯遠訕笑了兩聲,決定當什麼都不知道,同手同腳地走回餐廳,繼續解決他那碗還沒喝完的豆漿。
見湯遠回來,醫生正從廁所重新洗了手出來,順便監督著湯遠也再洗了遍手,一大一小再次坐回餐桌的時候,都悶頭繼續解決剩餘的早餐。
風捲殘雲之後,醫生收拾了一下餐桌,見離他上班還有點時間,便推了推眼鏡,對湯遠認真嚴肅地說道:「小湯圓,你這樣下去不行啊,我昨天聯繫了那位警察,他說你這種情況是可以去學校插班上學的。我這幾天幫你去附屬小學問問,就離我們家一條街的距離。」
湯遠被醫生口中的「我們家」感動了一下,但隨後小腦袋便搖得像是撥浪鼓一樣:「上學?我不需要上學。」
醫生愣了一下,因為湯遠並沒有說他不想上學,而是說他不需要上學:「胡鬧,哪有小孩子不去上學的?」
湯遠指著書架上的那摞書,理直氣壯地說道:「這些書是我用你的圖書證去市圖書館借的,你覺得普通小學能教得了我什麼嗎?」
醫生順著湯遠指的方向看去,瞬間就被那一摞看起來高深莫測的書震得半晌都說不出話來。小學生都已經可以研究什麼星占學、震盪學說、陰陽五行風水學……醫生的嘴角抽動了兩下,拿他沒辦法,笑道:「挑這些看不懂的書回來,怪沉的,你能拿得動嗎?」
關注的重點完全不對啊!湯遠忍著掀桌的欲望,鼓著腮幫子跳下桌子,登登登地跑到書架前把那摞書放到醫生面前,揚起下巴驕傲地宣布:「隨便考!」
醫生狐疑地拿起最上面的陰陽五行風水學,翻到一頁,剛說了幾個字,湯遠就順順暢暢地接著背了下去。醫生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不敢置信地連續考了幾處,換了幾本書詢問,除了三本沒看的書,其他的湯遠都一字不差地背誦下來。
「你過目不忘?」醫生合上書,用一種羨慕嫉妒恨的目光看著面前可愛的小正太。他一直以為過目不忘的人是小說裡寫出來騙人的,沒想到現在在他面前就站著一個!
「馬馬虎虎吧。」湯遠謙虛地撓了撓頭,事實上他臉上的表情可不是這樣的,簡直鼻子都要頂上天了。
醫生想了想,這樣逆天的正太連他都受不了,就不要放出去禍害和刺激祖國的花朵了。「乖,叔去上班了,好好在家待著,中午餓了就打電話叫外送,錢在玄關的抽屜裡,除了去圖書館不要亂跑。」
湯遠忙不迭地點了點頭,外面那麼冷,他才不想出去呢!
◎
雖然已經到了陽春三月,但外面的天氣還是冷得讓人難以接受。
醫生加快了腳步,簡直是小跑步地衝到了醫院,換上了白袍便跟著主任巡病房。已經來了一陣的淳戈落後了兩步,把一個病歷夾遞了過來,低聲道:「昨天晚上那個程竹竿又來了。」
醫生聞言皺了皺眉,很快地接過病歷翻閱起來。
程竹竿是那些小護士們給一個病人起的外號,能讓護士們都有印象,還到了起暱稱的地步,也就說明對方是醫院的常客。程竹竿原名叫程驍,是一個很有氣勢的名字,但卻得了很難治好的限制型心肌病。心臟本來就是人體最重要的一個器官,一旦有什麼問題,都會引起各種併發症。就算是限制型心肌病中最輕的病症,最多也只能活二十五年,而程驍的病非常嚴重,才二十歲剛出頭的他最近十年來已經進出醫院好幾回了。
「原來不是我負責他的啊,怎麼這回給我看病歷了?」醫生一邊看著病歷中的脈衝多普勒心臟超音波照,一邊不解地問道。程驍的手術一般都是各個心胸外科的醫生搶破頭要去見識的,畢竟一個人的心臟能脆弱到這種地步還堅強地跳動著的實例,還真是舉世罕見,醫生覺得他沒什麼實力能獲此殊榮。
「還不是你去年年初參加過他的那次二尖瓣成形術,你獨立完成的逆行途徑技術簡直完美!完全看不出來是第一次做,所以主任才叫上你一起。」淳戈的語氣略帶羨慕嫉妒恨,用拳頭捶了一下醫生的肩膀,輕哼道,「你這小子,非要我再這麼詳細地誇你一遍嗎?放心,程竹竿這回住院不是你上次手術出了問題,而是又出現了新的併發症。」
醫生翻閱2D心臟超音波照的手僵在了那裡,什麼二尖瓣成形術?什麼逆行途徑技術?他能說他一點都不記得了嗎?
但若是仔仔細細地回憶,他的腦海裡隱約還是有那麼些不連續的手術畫面,可是那些影像畫面就像是蒙上了一層毛玻璃,朦朦朧朧的根本看不清。
抬手按了按微痛的太陽穴,醫生覺得自己最近的精神狀態有點問題,但他上個禮拜特意去健康管理中心檢查了一下身體,並沒有發現什麼異常。可能是他想多了吧。
把注意力放回手中的病歷本上,醫生從上到下掃了一遍程驍密密麻麻的病史,也不由得心生敬佩。
限制型心肌病最終都會引發心力衰竭或者肺栓塞而死亡,除了接受心臟移植外沒有更好更徹底的解決辦法。但心臟移植在國內屬於大器官移植,由於思想保守,捐獻者並不像國外那樣多,有多少人都在排著隊的時候不甘心地閉上了眼睛,程驍也是在生死線上來回掙扎著的其中之一。
「他這回的情況不妙啊……」醫生皺著眉看著檢查結果,超音波造影可見微泡往返於三尖瓣,根據多普勒檢查的結果,估算右心室至右心房的反流程度,這看起來就是三尖瓣關閉不全的症狀啊。
「據說他馬上就要排到移植名單的最上面了,可千萬要挺住啊。」淳戈輕聲道,卻在下一刻牢牢地閉上了嘴。因為他們一行人跟著主任已經到了程驍的病房之中。
程驍家裡還算有錢,只是父母在他年幼的時候已經因為意外而過世,他的爺爺去世前給他留下了一筆基金,他也是因為有了這筆基金才能負擔得起自己巨額的手術費用。程驍的病房是單人間,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那裡看著窗外,整個人的身體因為水腫而虛胖,沒有了往日的竹竿樣子,甚至就像是正常人的體型,卻讓人看了無端端地生出憐憫唏噓之感。
見醫生他們進來,程驍收回了望著窗外桃花的目光,一張英俊的臉容面色寧靜,若是光看臉,就只有發紫的嘴唇和慘白的臉色才能讓人察覺出來他身患絕症,走在外面街道上絕對會因為俊帥而得到超高的回頭率。他甚至還有心情和相熟的主任開了個玩笑,完全不在意自己岌岌可危的身體。
主任輕咳了一聲之後便開始交代接下來的醫療安排,程驍的身體已經不適合藥物的保守治療,只能進行手術,但需要進行什麼樣的手術,還是要根據再次檢查的結果而定。主任在滿屋子的期待目光中,選了醫生和淳戈兩人負責。
醫生在聽到自己是第一助手的時候,便知道主任定是看中自己上次手術的表現。他理應直截了當地把事情說清楚,可是他並不想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只是略遲疑了一下,便點頭應允了。
接下來就是安排程驍再次做各項檢查,醫生和淳戈全程陪護,程驍對如此折騰也渾然不在意,只是在掃到醫生胸前的名牌時,平靜的表情才發生了變化。
「咦?原來是你,據說我上次的手術就是你做的,很完美呢。」程驍勾起紫色的唇,他的紫紺現象已經非常嚴重,甚至在手指的指尖都出現了深紫色。這是心肺疾病引起的呼吸功能衰竭的表徵。
醫生簡直不能想像,一個連每次呼吸都非常困難的人,又怎麼會露出這樣輕鬆柔和的笑容。況且對方的誇獎更令他受之有愧,當下只能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公事公辦地說道:「一會兒我們去MRI室,你身上可有什麼金屬的首飾、手錶,都要摘下來。」
「哦,我經常去檢查,知道的。好在我還沒有安過心律調節器,否則連核磁共振檢查都不能做了。話說,我記得上次你沒有戴眼鏡啊,怎麼換造型了?」程驍一邊說,一邊慢吞吞地從病號服的口袋裡掏東西出來,結果那東西從他指縫間滑落,劃過一道銀色的弧線,伴隨著清脆的聲音掉落在地。
醫生本來下意識地想要去撿,可是卻在聽到程驍的那句問話時,下意識地愣在了原地。
他會不戴眼鏡?儘管前兩年是做了治療近視的手術,但因為常年都習慣了鼻梁上有東西,就算是平光鏡他也時時刻刻地戴著啊。醫生呵呵地乾笑了兩聲道:「可能是我在做手術的時候沒戴眼鏡吧。」
程驍聳了聳肩道:「你覺得我在做手術的時候會看到你嗎?」
的確,每次都是麻醉師先進手術室,等患者徹底麻醉之後他們這些手術醫師才會就位。醫生覺得太陽穴又開始隱隱作痛,他究竟忘記了什麼?
淳戈粗線條地沒有注意到醫生的不妥,他彎腰把程驍掉在地上的東西撿了起來:「哎喲,還是這枚小銀魚啊,你還隨身帶著,居然還沒丟!」
醫生忍不住朝淳戈的手心裡看去,那是一條大概有大拇指長短的小銀魚,正確說來,這只是魚的右側身子,小銀魚的一半身體鼓起,而另一半是扁平的,那一半鼓起的身體雕琢得栩栩如生,只是那魚鱗黯淡無光,一看就是頗有些年頭的物件。那魚嘴處還有一個圓環鏤空,想來應是繫繩子所用的。
「這就是程驍的寶貝小銀魚,據說是他爺爺留給他的古董,他向來都是隨身帶著的。可是這傢伙還是個馬大哈,走到哪裡這小銀魚就被忘到哪裡。好在常照顧他的那些護士們都認識,丟了也就給他送回來。」見醫生感興趣,淳戈也就隨口八卦了幾句,不過他卻沒把這小銀魚給醫生細瞧。對於他來說,這條小銀魚哪裡有什麼好看的,重要的是程驍的身體檢查結果。所以他隨手便把小銀魚放到白袍的口袋裡,笑咪咪地推著程驍往MRI室走去:「小銀魚我先幫你保管了,走,我們要抓緊時間。」
程驍看著淳戈的神色有些不自然的僵硬,在所有人都沒有注意到的時候,他低垂的眼中有一抹陰鬱的寒光閃過。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啞舍(第五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 197 |
華文幻奇冒險 |
$ 198 |
奇幻冒險 |
$ 198 |
科幻/奇幻小說 |
$ 212 |
幻奇冒險 |
$ 213 |
奇幻/科幻 |
$ 225 |
中文書 |
$ 22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啞舍(第五部)
收留了湯遠的醫生,逐漸發覺自己有些不同尋常。
──他似乎失去了某些記憶。
想不起曾動過的完美手術,想不起自己買過房子。
而醫生接著發現,除了失去記憶,
自己的身遭竟還有許多層出不窮,難以解釋的怪事。
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偷取旁人陽壽的〈銀魚符〉;
將會帶給擁有者噩運的〈點翠簪〉;
能觀過去,亦可窺未來的〈燭龍目〉;
一盞〈走馬燈〉,將暗示持有人接下來的福與禍。
另一方面,趙高這些詭異行徑所圖謀的,究竟為何?
這些帶有邪惡之氣的古董,又將對他的計畫起到什麼作用?
本書特色
簡體版單冊狂銷超過150萬本的超人氣幻想奇譚,繁體版強勢登場!
顧漫/《微微一笑很傾城》 蝴蝶藍/《全職高手》《天醒之路》
金牌作家聯合絕讚推薦!
邪穢之物,蠱惑人心。
當擁有邪惡之氣的古董誘人墮落時,
你,是否還能保持本心?
作者簡介:
玄色
中國百萬級青春暢銷書作家,2015年第十屆作家富豪排行榜憑藉1100萬版稅位居第10,也是 TOP10中最年輕的作家。AB血型的射手座,主業宅女,副業碼字,擅長烹飪和幻想,愛好閱讀 和旅行,追求奔放自由的人生,所以遊走於歷史與幻想之間,寫下一個又一個略帶哀傷的美 麗故事,代表作《啞舍》系列、《昊天紀》系列、《守藏》等。
章節試閱
它們在歲月中浸染了成百上千年。
每一件,都凝聚著工匠的心血,傾注了使用者的感情。
每一件,都屬於不同的主人,都擁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件,都那麼與眾不同,甚至每一道裂痕和缺口都有著獨特的歷史。
誰還能說,古董都只是器物,都是沒有生命的死物?
這是一本講述古董故事的書,既然它們都不會說話,那就讓我用文字忠實地記載下來。
歡迎來到啞舍,請噤聲……
噓……
玄色
第一章銀魚符
刺耳的鬧鈴聲在屋中響起,湯遠過了好一陣才揉著眼睛從床上爬起來,睡眼惺忪地打著哈欠往廁所走。他動作麻利地踩著小板凳放了水、沖了手、...
每一件,都凝聚著工匠的心血,傾注了使用者的感情。
每一件,都屬於不同的主人,都擁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件,都那麼與眾不同,甚至每一道裂痕和缺口都有著獨特的歷史。
誰還能說,古董都只是器物,都是沒有生命的死物?
這是一本講述古董故事的書,既然它們都不會說話,那就讓我用文字忠實地記載下來。
歡迎來到啞舍,請噤聲……
噓……
玄色
第一章銀魚符
刺耳的鬧鈴聲在屋中響起,湯遠過了好一陣才揉著眼睛從床上爬起來,睡眼惺忪地打著哈欠往廁所走。他動作麻利地踩著小板凳放了水、沖了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