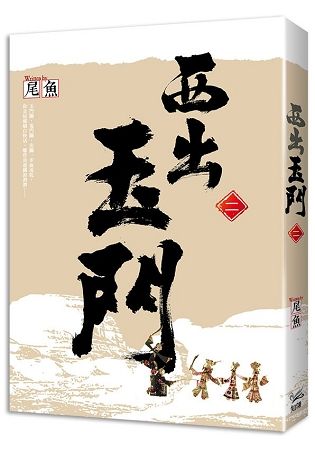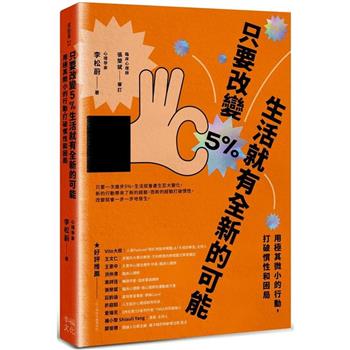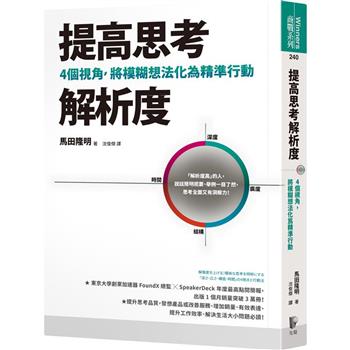第十一章
柳七做事老派,要留三人吃晚飯,說是事情既然談成了,大小細節,酒桌上過,這樣方便拉近感情。
酒樓在棋牌室附近,叫天山客,也是柳七的產業。
離飯點尚早,柳七還要忙點雜事,昌東他們先過去,服務生得了柳七吩咐,引三人進了包廂,裡頭裝修有點舊,俗得富麗堂皇,好大一張圓桌,可以當床。
服務生怕他們等得無聊,上了茶水之後,還送過來兩副撲克牌。
昌東對打牌沒興趣,他仔細看自己的手帳,那些圖確實不好抵賴,那條司馬道上,他甚至標出了灰八被埋的位置。
但好在文字部分的推理,他都寫得簡略,譬如「血、風頭、玉門關」,難怪柳七說看得半懂不懂,不瞭解事情前因後果的人,很難看明白。
看完了,他把那幾頁撕下,扯成條,拿過桌上的火柴,劃火點著了,扔進菸灰缸裡。
葉流西看著白色字紙在焰頭吞吐間瞬間變灰:「字和畫都怪好看的,就這麼燒了,多可惜。」
昌東說:「人家都給你上課了,這個教訓得吃。」
悟性高的人少,大多數人都是吃教訓,然後學精,錯越犯越少,位越登越高。
燒完了,屋子裡散開微溫的煙火味,昌東問葉流西:「真拿柳七的錢?」
葉流西覺得他問得多餘:「不拿白不拿囉。」
「有些錢拿了燙手,妳不能只看眼前,得想想萬一。」
「萬一什麼?這是柳七在投資,真的一無所獲,那也是他選錯了股,投資眼光差,關我什麼事?」
她總是一堆歪理,事情要真能這麼輕易就好了。
昌東沉吟:「柳七這樣的人,做事周全,他不會只出個錢任妳花這麼簡單。」
待會酒桌上的大小細節,可能都是苛刻條件。
葉流西回答:「火燒眉毛就洗把臉,到時候再說唄。」
昌東看了她一眼:「說妳什麼好,心這麼大。」
葉流西糾正他:「這不是心大,這是自信,說明不管什麼狀況,我都能解決。畢竟……」
她手托著腮,朝他眨眼:「呼風喚雨這種事,我能做一半呢。」
昌東無言以對,只能喝茶。
肥唐在邊上聽得一頭霧水:「西姐,什麼叫呼風喚雨,妳能做一半?」
葉流西提示他:「仔細想,要從字面去找。」
肥唐說:「呼風喚雨,做一半,西姐妳是會……呼喚?」
昌東一口茶全噴了。
◎
晚九點開正席,菜在這之前陸續擺上,什麼大盤雞、烤羊排、[食囊]包肉、手抓飯,餐盤和餐量都巨大——昌東沒心思吃,肥唐不敢吃,連葉流西都表示,她光看餐盤子就飽了。
這一桌菜,難免淪為陪襯、氣氛、背景板。
九點一過,柳七就到了,只帶了兩個人。
一個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身材嬌小,穿超短裙、漁網絲襪、短皮衣上無數鉚釘,濃妝,頭髮亂抓個髻,有幾撮染紫,眼睛周圍又是亮色眼影又是睫毛膏又是熬夜的黑青眼窩,進來之後,還先於柳七落座,先打個哈欠,又挑了一筷子皮辣紅吃。
柳七皺了皺眉頭,說:「沒規矩。」
另一個是個寸頭的精壯男人,二十五六年紀,皮膚有點黑,耳廓上方鑽掛了環,挽起的袖口處露著的紋身,居然是叢瘦伶伶的細骨梅花,這讓他的整體氣質突然就從街霸流氓的形象裡跳脫出來,多了點難以言喻的感覺。
相比那小姑娘,這個男人很規矩,幫柳七拖椅子,然後負手站在邊上,目不斜視。
柳七朝昌東他們笑笑:「介紹一下,這個呢,是我乾女兒,丁柳……小柳兒,把菸掐了!」
丁柳正點菸,聽到柳七的話,順手就把菸頭摁在桌布上,然後一抬臉,眼睛沒焦點,也不知道看誰:「幸會啊,我幫我乾爹照看歌廳的場子。」
柳七又指身後的男人:「這個叫高深,幫我做事的。你們幾位我就不介紹了,來的路上,都跟他們說過了。」
「我呢,是這麼考慮的,大家剛認識,互相還不怎麼信任:我這錢出去了,你們胡天海地造掉了,回來跟我說,七爺,什麼都沒找著,我這心裡頭啊,會不平衡。」
「所以我這頭也出兩個人,放心,都是能幫得上忙的,不會給你們拖後腿……小柳兒年紀輕,幫我看了三年場子了,沒人敢鬧事。」
昌東說:「灰八什麼下場,七爺也知道。想派人盯著,可以理解,但把乾女兒都送出來,是不是太捨本了?」
柳七笑笑:「我老啦,這兩年,想把手頭上的事給分出去,交給小柳兒,太多人不服,她缺歷練,心又浮——玉不琢還不成器呢,得找件凶險事磨磨她,現在剛好有這麼個事兒,闖出來了,算她的,折在外頭了,就認命,反正不是親生的。」
昌東忍不住看向丁柳。
她面不改色,不過臉上塗那麼厚脂粉,改了色也看不出來。
昌東考慮了一下:「兩人去可以,分清主次,知道誰是頭——我可以要幫手,但不要太爺。」
柳七滿臉堆笑:「這是當然,你們儘管放手去幹……這位兄弟,我會幫你們照顧好。」
他目光落在肥唐身上。
肥唐打了個哆嗦,這酒桌上,就他分量輕,他滿以為,自己會是從頭到尾都不被想起來的那個……
他嘴唇發乾,倉皇地看左右,昌東皺了下眉頭,似乎想說什麼,葉流西忽然叫了聲:「昌東!」
她把餐碟遞出去:「幫我夾根羊排,我搆不著,要大的。」
昌東欠身,拿筷子幫她拈了一根,大的羊肋排骨,灑滿了顆粒孜然和鮮紅的辣椒粉。
葉流西接回來,一手餐刀一手叉,切肉剮肉,刀叉碟子碰得匡當作響。
這一桌子,只她一人動餐。
吃得旁若無人,後來嫌刀叉費事,索性上手拿。
肥唐看出點端倪來了,覺得葉流西是不想昌東幫他講話。
「西姐……」
葉流西頭也不抬:「叫我幹什麼?你想做什麼,不想做什麼,自己長嘴自己說,自己都不吭氣,別人上趕著著什麼急?還沒吃呢,就撐著了。」
說到這兒,乜斜了一眼昌東。
昌東笑了笑,示意了一下嘴角,她伸出手指去揩,全是辣椒粉,順勢舔了。
一桌的人,都知道她話裡有話。
肥唐也知道,他猶豫了一下,抬頭看柳七,說:「我不想待在這。」
柳七不動聲色:「說大聲點,我聽不見。」
肥唐頭皮發麻,一顆心差點跳出喉嚨,再看到葉流西拿餐巾擦手,忽然就來了勇氣,一巴掌拍在桌面上,吼:「不要你照顧,我不想待在這!」
柳七目光一冷。
高深臉色一沉,手攥成拳,胳膊上肌肉賁起。
丁柳斜著眼看肥唐。
而昌東看葉流西。
葉流西放下餐巾,慢條斯理:「七爺,肥唐確實不適合待在這。」
「你既然喜歡摸人的底,那摸過他的嗎?肥唐生在西安,古玩世家,破銅破瓦,到他跟前,看看樣式,掂掂輕重,就能說得出朝代、值多少錢。我記得……」
她看肥唐:「你是西安文物鑒定評估委員會的高級會員是吧?」
肥唐說:「去年……才加入的。」
說這話時,他都不敢抬頭:他頭一次聽說西安還有這麼個委員會。
葉流西看柳七:「七爺不是想找硬貨嗎?這一趟如果沒有行家,就是一隊瞎子出馬……到時候,我們把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當破銅爛鐵扔掉,捧回一堆花哨但不值錢的,七爺可別怪我們啊。」
……
柳七沉默了一會,忽然哈哈大笑。
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來來來,喝酒,酒肉朋友,不喝酒吃肉稱不上朋友,咱這就算談妥了……」
昌東打斷他:「七爺,還有個事。那個叫神棍的,你現在還有聯繫嗎?」
柳七說:「那怎麼可能啊,就他一個人,神經還不正常,能走出羅布泊,那是虧得有我一路同行,他要真作天作地,又去那些凶險的地方,指不定死多少年了。」
「那分開的時候,就沒留什麼聯繫方式嗎?」
畢竟一路同行的交情。
「留了,到了哈密之後,說是為了紀念這段旅程,拉我專門去照相館拍了張照,他沒手機沒電話,在照片背面給我寫了個QQ號碼,我沒加過,不過照片還在。」
「那麻煩七爺幫忙找一下,我試著聯繫一下,他記了那麼多故事,未必全都給你講,也許關於鬼駝隊、皮影棺,還能問到點什麼。」
……
酒到中途,昌東去洗手間。
出來的時候,看到葉流西也在洗手檯前洗手。
昌東過去,開了另一個水龍頭,又往手上搓了點洗手乳,低頭問她:「看出什麼來了?」
葉流西抽了張衛生紙擦手,對著鏡子整理頭髮:「你呢?」
老酒樓,除了包廂,其他地方的燈光都昏暗,燈下看人,還是在模糊的鏡面裡,自己都覺得很好看。
「柳七還是挺照顧丁柳的,那個高深隨行,應該是專門保護她的。」
葉流西嗯了一聲:「高深跟丁柳的關係不一般。」
昌東抬頭,目光和她的在鏡子裡相觸:「怎麼看出來的?」
「高深進屋之後,基本目不斜視,只有幾次例外,都是去偷瞄她,不過丁柳好像根本不在意,看肥唐都比看他多。」
「偷瞄能說明什麼?」
「管不住心,都是從管不住眼開始的。」
……
兩人往回走,經過一個沒人的包廂門口時,昌東忽然止步,然後食指豎在唇邊,示意葉流西噤聲。
這包廂門半掩,裡頭一片黑,明顯沒人,卻有淡淡煙氣飄出。
頓了頓,有人說話,是丁柳的聲音。
「你覺得,這兩人難搞嗎?」
有個男人回答:「七爺說,都是厲害角色,讓妳客氣點,別亂來。」
昌東直覺這應該是高深。
丁柳鼻子裡嗤笑一聲:「我乾爹嘴上說得好聽,我才不信他會讓別人從他碗裡分飯……那個昌東,和那個女的,是一對嗎?」
高深沉默了一下,說:「可能吧。」
「是一對就好辦了,想讓情侶反目,太容易了。」
◎
出發定在三天後。
柳七有足夠的人手,哈羅公路下去這一段路又好走,昌東畫了地圖,在白龍堆附近一處要了補給點:水、汽油、食品等,每週補一次。
這樣就把越野車從物資載重裡解放出來。
昌東在車裡加多了水箱,另外裝了加熱器,配了車載淋浴頭,只要節約用水,基本能解決洗澡問題。
肥唐的車不太實用,好在哈密距離柳園不遠,請柳七的人幫忙退了車,另要了輛江鈴,除了駕駛座,車裡幾乎拆空,裝了車床墊,車內頂安了拉繩掛環,可以用隔簾按需要拆隔出空間。
工程就在飯店隔壁的汽配店進行,昌東帶著肥唐長時間駐場,葉流西則像個長官,每天都來看進展,且越跑越勤,昌東估計她是閒的——拿到柳七的錢之後立馬不打工了,人生的意義簡直失去了一半。
第三天中午改裝收尾,昌東拿她給車子做檢驗。
布簾拉下,示意她躺平:「舒服嗎?」
葉流西躺了一會,她右手邊靠車,左手邊是布簾:「我左邊睡誰?」
「我。」
她提建議:「我們倆之間,應該焊個鐵柵欄。」
昌東伸手拉她:「給妳買個鐵籠子要嗎?」
葉流西借力起來。
又去試淋浴器。
蓮蓬頭從車裡遞出來,管上有吸壁,可以固定在車上。
一撳開關,水頭嘩嘩的。
「多久能洗一次?」
「一週,一次不能超十分鐘。」
葉流西想了想,沒找碴:在那種地方能有這樣的用水,很奢侈了。
……
中午,在飯店餐廳訂了簡餐自助,肥唐讓兩人先去,說是自己先回房洗澡,遲點到——他一上午鑽了幾趟車底,髒得不能看。
昌東和葉流西坐了張四人桌,食客不多,隔得都挺遠,偶爾傳來刀叉相碰的聲音,不擾人,倒挺悅耳。
葉流西先吃完,刀叉一擱,長長嘆了口氣。
昌東眼皮略掀:「怎麼了?」
「食不下嚥。」
昌東抬起頭,目光在她面前的碗碟上一一掃過。
「流西,食不下嚥多用於心裡有事吃不下飯,妳這種吃撐了的,用這詞不合適。」
葉流西身子一歪,以手支頤:「我們就要被拆散了,你還沒事人一樣。」
昌東說:「我們跟柳七也好,丁柳也好,都是初步接觸,沒什麼了不得的矛盾,這麼短的時間,他們也不可能計畫什麼步步為營的陰謀。」
「丁柳是小姑娘,看到柳七給我們臉,心裡不舒服,想在乾爹面前求表現,自以為什麼都能做成,她想搭臺唱戲是她的事,我們不搭理就行……」
說話間,肥唐托著餐盤過來了。
昌東看著他坐下,忽然想起了什麼:「聯繫上神棍了嗎?」
三個人裡,只有肥唐玩QQ,柳七號碼給過來之後,理所當然交給他跟進了。
不說還好,一說肥唐一肚子氣。
「發了幾遍朋友申請,太高冷了,都沒通過。」
「是不是棄號了?」
「不是!」肥唐連連搖頭,「有一回搜他,我看到頭像亮來著。」
他發牢騷:「簽名也怪裡怪氣的,什麼『為了解放不吃雞』,東哥,這人是不是活在舊社會啊,咱們都解放多少年了。」
「也可能是號碼易主了……你好友申請怎麼說的?」
「就說我是柳七的朋友啊。」
昌東沉吟。
這神棍,如果真如柳七所說,走遍大江南北,尋訪奇人異事,那這麼多年下來,經歷的奇事和積攢的故事都不會少,柳七當年,不過是個捉蛇的,對神棍來說,還真算不上特別,他未必還記得。
「這樣,你再發一條,就說你在玉門關外,白龍堆裡,挖到一口棺材,裡頭是穿著唐裝的皮影人,一共九個,再把那首『披枷進關淚潸潸』的歌謠也發過去,一條寫不下就分兩條發……他再不回覆,就算了。」
十多年了,難說一個人的愛好會不會發生改變。
但如果神棍還是一如當年,有著為了一個傳說故事就跟老人家比手畫腳交談一整天的熱情的話,應該……會回覆的。
◎
第二天早十點,兩撥人在天山客酒樓門口會合。
丁柳那頭兩輛車,一輛是吉普指揮官,這車身軀龐大,線條鋒利,在某些玩家眼裡,僅次於悍馬,另一輛車普通,只是跟過去認路,方便後續送補給。
昌東車子開近,並不停,只撳下窗子,手臂招了招示意跟上,然後直接調頭上路。
肥唐緊跟而上,後視鏡裡,對方的兩輛車明顯沒反應過來,過了好一會兒才駛上來。
葉流西看昌東:「都不說下去打聲招呼?」
「沒什麼好說的,說多了累。」
他專心開車,目不斜視,帽簷在眼睛周圍打下陰影,下巴周圍,仔細看,有淡青色的鬍茬微冒頭。
葉流西說:「你該刮鬍子了。」
昌東伸手摸了一下下巴:「今天刮,明天長,男人鬍子比頭髮長得快……看起來彆扭嗎?」
他轉頭看了葉流西一眼。
葉流西搖頭,目光下意識避開,感覺有些微妙:她覺得這樣剛剛好,不知道摸上去什麼感覺,應該會微扎,如果蹭磨脖頸的話真是要命……
她有點不自在,伸手去理頭髮,指腹蹭到耳根微燙,趕緊撥頭髮蓋住。
車裡忽然有點悶,葉流西說:「停一下吧,下去透口氣。」
昌東靠邊停車。
葉流西下了車,拿手搧風。
頭車一停,後面一長溜的都停了,那輛吉普指揮官這才找著機會往前超,估計一路前不前後不後的,憋屈壞了。
肥唐從車窗裡探出頭:「西姐,怎麼停車了?」
葉流西沒好氣:「熱!」
「不熱啊。」
葉流西摸起塊石子,作勢要扔,肥唐的腦袋倏地縮回去了。
吉普指揮官跟昌東的車並肩停,葉流西聽到開車門的聲音,轉身去看,愣了一下。
裡頭坐著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兒,皮膚白淨,清湯掛麵,眼睛細而略彎,眼尾稍長,笑起來挺勾人,穿白色粗針毛衣,黑色牛仔褲,腳蹬白色滑板鞋,頭髮上還別了個帶黃小鴨頭的壓克力邊夾。
和周圍的一切,荒涼的公路、貧瘠的戈壁山,還有粗獷的車駕,格格不入。
她跟昌東說話:「東哥。」
操,居然是丁柳。
昌東嗯了一聲。
「早上怎麼都不停一下?我乾爹還準備了鞭炮,我們這兒的習慣,出大遠門前放掛鞭,吉利。」
「趕時間。」
丁柳倒是知情識趣,看出昌東冷淡,笑了笑,緩緩關上車門,葉流西注意去看高深:他明顯鬆了口氣,舔了下嘴唇,又拿手背蹭了蹭人中。
昌東有一句話說得不對,搭臺唱戲,戲裡戲外都起波瀾,想不搭理還真挺難的。
她坐回副駕駛座,昌東候著她繫好安全帶,發動車子。
無線電對講機裡忽然傳來肥唐的聲音:「東哥,停停停……神棍回訊息了。」
◎
神棍的訊息其實回得挺早,但估計是這一路訊號不大好,收發有延遲,加上肥唐一門心思開車,沒怎麼看手機,所以直到現在才看到。
那條訊息是:別管它。
肥唐有點忐忑:「東哥,什麼叫『別管它』啊?」
昌東說:「問他為什麼。」
「沒法問啊,這裡訊號不好。」
「你上我的車,咱們往回倒車,哪訊號好在哪問。」
神棍一定知道點什麼,否則不會回答「別管它」。
頭車忽然又調頭,高深有點惱火,探出身子時,昌東的車恰好和他擦身,速度放緩,以便肥唐上車。
昌東撳下車窗,說了句:「想省事就在這等,我們還回來;不放心就跟著,你隨意。」
高深咬牙,正想打方向盤,丁柳說了句:「這是玩兒我們呢,就在這等,我們又不是沉不住氣的人。」
她嘴裡銜了根菸,低頭,喀噠一聲,火苗自手裡的打火機裡竄起,舔著了菸頭。
高深在後視鏡裡看見,猶豫了一下,說:「小柳兒,妳少抽點菸。」
丁柳吸了口菸,過了會慢悠悠吐出:「關你屁事。」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西出玉門(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5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華文驚悚/恐怖小說 |
$ 205 |
推理/驚悚小說 |
$ 221 |
小說/文學 |
$ 234 |
中文書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西出玉門(二)
昌東想找出白龍堆隱藏的真相,
葉流西想找到自己失憶的原因及來歷,
兩人一拍即合,準備備齊改裝吉普車和工具,
回到戈壁找尋那飄渺難覓的「玉門關」入口。
只沒想到臨行前,還被強迫塞了三個夥伴──
少女丁柳、保鏢高深和倒楣的肥唐。
五個心思各異,目標不同的人共乘一車,
不要命似的撞向那古怪神祕的雅丹土堆!
本以為會落個車毀人傷的下場,沒想到這一撞,
真讓他們闖進「另一個白龍堆」當中!
更可怕的是,夜晚還有外表恐怖還會吞食血肉的人架子攻擊!
這是一個人與妖並存的世界。而前路,不知還有什麼正等待著他們……
本書特色
《七根凶簡》、《半妖司藤》作者尾魚,戈壁冒險顛覆想像之作!
作者簡介:
尾魚:熱衷一切奇思怪想的軼聞,相信世界的玄妙大過眼睛,熱愛旅行,尤喜探險,身體跨越不了的險境,就是筆下故事開始的地方。
TOP
章節試閱
第十一章
柳七做事老派,要留三人吃晚飯,說是事情既然談成了,大小細節,酒桌上過,這樣方便拉近感情。
酒樓在棋牌室附近,叫天山客,也是柳七的產業。
離飯點尚早,柳七還要忙點雜事,昌東他們先過去,服務生得了柳七吩咐,引三人進了包廂,裡頭裝修有點舊,俗得富麗堂皇,好大一張圓桌,可以當床。
服務生怕他們等得無聊,上了茶水之後,還送過來兩副撲克牌。
昌東對打牌沒興趣,他仔細看自己的手帳,那些圖確實不好抵賴,那條司馬道上,他甚至標出了灰八被埋的位置。
但好在文字部分的推理,他都寫得簡略,譬如「血、風頭、玉門...
柳七做事老派,要留三人吃晚飯,說是事情既然談成了,大小細節,酒桌上過,這樣方便拉近感情。
酒樓在棋牌室附近,叫天山客,也是柳七的產業。
離飯點尚早,柳七還要忙點雜事,昌東他們先過去,服務生得了柳七吩咐,引三人進了包廂,裡頭裝修有點舊,俗得富麗堂皇,好大一張圓桌,可以當床。
服務生怕他們等得無聊,上了茶水之後,還送過來兩副撲克牌。
昌東對打牌沒興趣,他仔細看自己的手帳,那些圖確實不好抵賴,那條司馬道上,他甚至標出了灰八被埋的位置。
但好在文字部分的推理,他都寫得簡略,譬如「血、風頭、玉門...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尾魚
- 出版社: 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18-09-13 ISBN/ISSN:978957961471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