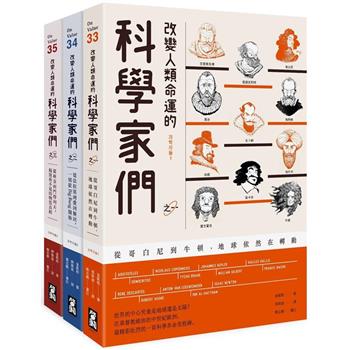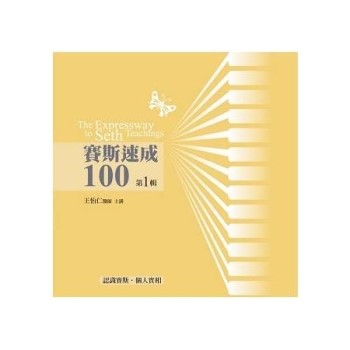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百百怪軼與金魚 卷四 (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82 |
奇幻冒險 |
$ 205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34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百百怪軼與金魚 卷四 (完)
終於明白自己正在「消失」,天使們的態度讓人心慌,
晴河知道自己必須回到裏街,唯有裏街有人能幫助他,
他要湊齊金魚,期望能獲得讓自己「存在」的答案,
然而,當一切過去不肯正視的事情被迫攤在眼前,
付出的卻是鮮血淋漓的代價──
足以摧毀小鎮的巨大暴風雨即將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