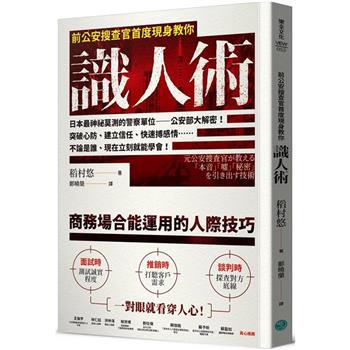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沙林傑:最後的訪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36 |
歐美文學 |
$ 422 |
中文書 |
$ 422 |
世界文學人物傳記 |
$ 432 |
美國現代文學 |
$ 432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43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沙林傑:最後的訪談
有句玩笑話流傳已久,可以將沙林傑的訪談標題下成〈滾出我的草坪〉,
因為他從不願接受採訪。
從於1951年出版《麥田捕手》的那一刻起,沙林傑就被痴迷的粉絲、傳記作家和咄咄逼人的記者跟踪。在這本與這位難以捉摸的文學巨擘的罕見而深刻的邂逅中,沙林傑時而心甘情願、時而勉強地討論了成名的衝擊,他的藝術起源,以及他對作家的建議。這些富有啟發性、挑釁性、甚至有趣的對話,揭示了一位作家對聚光燈的強烈抗拒,但又無力逃避它的眩光。
如果你是沙林傑粉絲,你會對這本書又愛又恨。
有關霍爾頓・考菲爾德,沒有更多可說的了,
再讀一遍。一切都在書中。
——沙林傑談《麥田捕手》
作者簡介
沙林傑(J. D. Salinger)
生於1919年紐約州紐約市;歿於2010年新罕布夏州科尼許鎮。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劃時代著作《麥田捕手》被廣泛認為是二戰後美國極重要的小說。他的著作還包含《九個故事》、《法蘭妮與卓依》、《抬高屋梁吧,木匠;西摩傳》。儘管直到2010年去世為止,沙林傑從未停止寫作,但他過著避世的生活,且自1965年便再也沒有發表新作品。
原文版編輯
大衛.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
《紐約時報》記者。他所屬的新聞團隊榮獲2013年普立茲獎的釋義性報導(Explanatory Report)獎項,主題是蘋果電腦如何改造了經濟型態;2012年他因假書評工廠的報導,榮獲美國商業編輯與作家協會「最佳商業報導獎」(Best in Business)。現在他與家人還有瀕臨崩塌的書堆一起住在舊金山。
譯者簡介
劉議方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後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取得學位,目前從事筆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