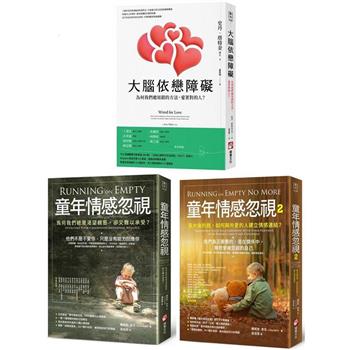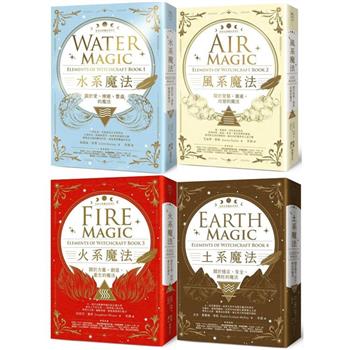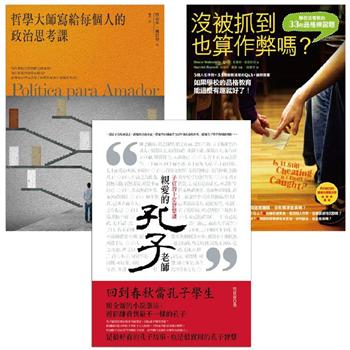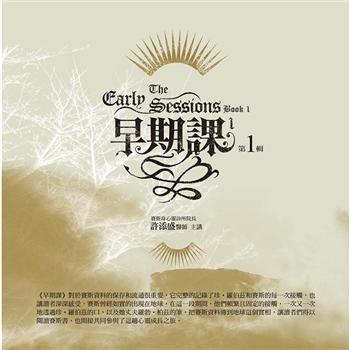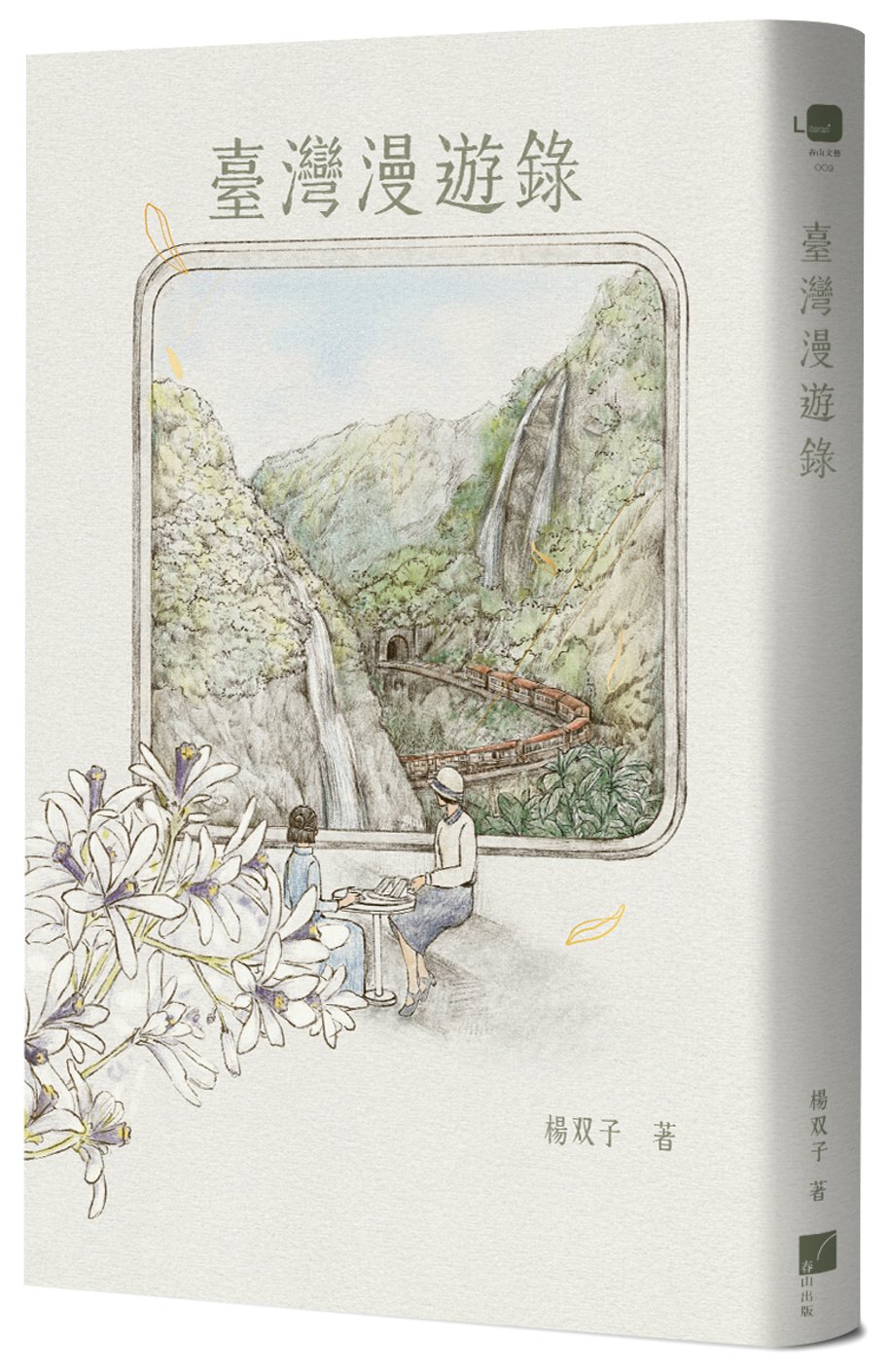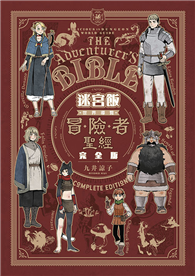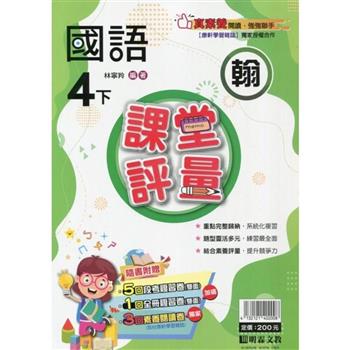現在出版界盛說「品牌」。我輩有時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維護「品牌」的從業者行列。其實,像我這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成長的出版學徒,長期以來,何嘗有過「品牌」觀念,我們只知道聽上面的話,不出上面不中意的書刊。你去自創一個什麼東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豈不是自找麻煩 • 自討沒趣?
這種觀念,我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末。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編 《 讀書 》 雜誌,「品牌」說似乎稍稍有點露頭。但愚魯如我,直到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光景,才開始想到:在那個叫做「生活 讀書 新知 三聯書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該自己設計一點該做的事了。
1992 年 11 月 27 日,鄙人虛度六十又一,已經不主持三聯書店的工作了。這時覺得自己不妨「羅曼蒂克」一些 • 又仗著新領導的縱容,於是斗膽寫了一個意見,報送各方 • 意見第一段謂:
「中國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傳統。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務、中華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說。三聯書店更是以刊物起家,無論本店圖書出版之盛衰,幾大刊物(尤其 《 生活 》 雜誌)總是由店內主要負責人親自主辦和竭力維持,使之成為本店的一種『門面』。和聯繫讀者之手。本店之三個名稱( 「生活」、「讀書」、「新知」)即為三種雜誌之名稱,是為明證。據說,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後的出版總署署長,三聯書店創辦人之一)始終認為出版社應以辦刊物為重點,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實現為憾。一九七九年籌備恢復『三聯』。建制之際,先以恢復 《 讀書 》 入手,迄今十三年,看來也是成功的。因是,無論從傳統經驗,還是從當前實踐看,出版社辦雜誌都是必要的(有些國外經驗也許更可說明此點)。」
寫這段話,是讀了不少文件特別是店史以後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於是突然頭腦更加發熱,居然提出立即要辦十個刊物。當時設計的十種是:
( 1 ) 《 時代生活 》 (月刊) ─ 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對改革閒放帶來的種種新現象展開多角度、多側面、多學科的報道和分析,側重點放在促進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長之基點上。這實際上是 《 生活 》 雜誌的現代版。如果主管機關允許重用 《 生活 》 刊名,則更佳。
( 2 ) 《 開放經濟 》 (旬刊) ─ 對外報道中國經濟之發展,對內指導中國讀者如何從事經濟活動,即使人們懂得經濟事務之重要以及操作、運行之道,又要防止人們成為單純的「經濟動物」。
( 3 ) 《 生活信箱 》 (半月刊) ─ 供一般市民閱讀的大眾性刊物,繼承 《 生活 》 雜誌的優秀傳統,用親切的語言以通信形式為群眾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種種疑難。
( 4 ) 《 讀書快訊 》 (半月刊) ─ 《 讀書 》 雜誌之通俗版,著重在培養讀者對書刊的愛好和興趣。
( 5 ) 《 譯文 》 (月刊) ─ 適應開放改革之需要,譯述國外政經學術文化之重要文章,讓中國讀者瞭解域外最新信息。
( 6 ) 《 東方雜誌 》 (月刊) ─ 如「商務」暫不擬舉辦,擬由本店接手,敦請陳原先生主編。如商務不擬讓出此刊,則易名為 《 新知 》 雜誌,性質仍為綜合性的高級學術文化刊物。如果陳原先生俯允,還以他主編為好,因他原是「新知書店」舊人,有此因緣,較能貫徹「三聯」傳統。
( 7 ) 《 藝術家 》 (月刊) ─ 介紹和鑒賞中國文物及藝術精品,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國人生活品位。
( 8 )少年刊物一種(內容及刊名待設計)。
( 9 ) 藝術攝影刊物一種 《 內容及刊名待設計)。以上九種,加上三聯書店原有的 《 讀書 》 ,合共十種。擬在 2 到 3 年內次第實現。
這種設計,說實話,即使實現,也只是我的「遺囑」。在我本人說,自己「下崗」 在即,自然是一個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這個設想,托人情,走門路,處處請托關說。結果不少人看了覺得是匪夷所思,簡直是神經病。幾次周折,到是年 12 月 8 日,才從神經病稍稍回到現實,把計劃改為出「辦刊理由」是:「本刊為鄒韜,同志創辦的聲名卓著的 《 生活 》 雜誌之現代版,以此向海內外表明: 《 生活 》 雜誌一脈尚存,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光明正大,有道有理。這個計劃總算批准。於是,到 1995 年 1 月,《 三聯生活周刊 》 出刊了。
要說明的是,三聯書店早有恢復 《 生活 》雜誌的意願。1980年─ 1981年,即已開過一試刊些座談會,還出版了 《 生活 》 半月刊試刊。
九十年代末,在自己臨近全面退休之前,大發了一場神經病。湊著好時光,因著三聯書店新領導的敢於承擔風險,總算因而讓我們有了一個好雜誌,讓三聯由此可以對外宣稱:「 《 生活 》 雜誌一脈尚存,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這話翻譯成時髦的語言,無非是說:我們維護住了一塊歷史品牌。
現在,談「品牌 J 不再是發神經病了,也許不要「品牌 J 反而成了神經病。時至今日,我經常想起管理學大師杜魯克的主張:不去算舊賬,趕緊往前看,去創造更多的機會。按現今的說法,就是創造更多的品牌。
這個期望落在時下在三聯書店秉政的諸君子身上,特別是 《 三聯生活周刊 》 身上了。
(原載於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 《 三聯生活周刊十年 》 )
期望時代大刊
《 三聯生活周刊 》 的創刊號上,我寫過一則「編者手記」:
在韜奮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裡推出的這本《三聯生活周刊 》 是創刊也是復刊。
六十八年前韜奮先生創辦並主持的 《 生活 》 周刊 與生活歷史共嗚 積極反映了時代潮流和社會變遷 竭誠服務於千萬讀者 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從這個意義上講 我們是復刊。堅持這個方向 是我們的宗旨。
今天 我們正處於世紀之交的大時代中 這是我們的幸運。如何從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 折照出這個時代 反映出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新課題 提供人們嶄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資訊 當是我們最需努力的關鍵。韜奮同志從來主張 特殊時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糧食。這就需要創新 要前進。 《 三聯生活周刊 》 的創刊就是我們的再出發。
在這歷史的承傳和時代的創新面前 我們惶惶然請益於師友 商討於同志 希望作為一個共同的事業 一起來辦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在這歷史的承傳和時代的創新面前 我們惶惶然請益於師友 商討於同志 希望作為一個共同的事業 一起來辦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這基本反映了我們的辦刊思想,是當時窮得叮叮噹噹、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壯志。
當時真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壠,賬無餘款。但我們分析市場,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周刊形態已是發展的必需,而當時除了 《 瞭望 》 ,並無其他現代性很強的文化性新聞性周刊;分析我們自己,我們有最佳的品牌優勢,有老同志的支持,有當時社委會的一致意見,更有學術文化界朋友們的實際支援,在資金方面也有爭取外援的可能;再則,從三聯的發展戰略說,這也是衝破三聯困境的關鍵一大步。我們只能,也必須義無反顧地衝上去。
決心好下,但執行過程之艱難曲折卻難以想像。創刊、堅守和正式轉為周刊是三個關鍵時期。
創刊階段,在錢鋼帶領下大腕雲集,創意無窮。從 1993 年 3 月批准刊號,錢鋼進入,到 1994 年 3 月遷入淨土胡同前,在當時三聯窩居的大磨坊樓上的平台房裡,日夜燈火通明、熱火朝天。制訂規劃、招聘記者、職業培訓、「空轉」試刊 …… 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憶的日子。
雖然這以後由於資金中斷等種種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這一年的工作明確了辦刊思想、搭好了架構、鍛煉了隊伍、熟悉了出刊的各個環節,不少欄目不但十年來仍在沿用,連外刊都在借鑒。尤其在媒體中的影響力大大增強,為以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從 1994 年 5 月到 1995 年 8 月,這是一個情況多變的守護期。這期間試過幾位主編,換過兩任投資者。真正做了實際工作的是楊浪。他在最困難的時候挺身而出,不講代價地接下了重任,編了一期試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後亦終因資金問題而休刊。
三聯書店的文化精神從來是開放的、包容的,也堅持用人必須不疑,刊物必須是主編負責制。在方針確定以後,總編只管提供平台,解決困難,協調關係和終審稿件。主編應該有最大的自主空間。也因此,我們才有這樣的幸運,能聚集那麼多的師友、同志來和我們一起創編這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個大錯:從一開始就主觀地想請兩個主編合作,一個新聞專長,為主編;一個文化專長,為副主編。結果組合了幾次都完全失敗,也傷害了個別主編,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內疚。
分出經營的這一塊,與社會資金合作。生活周刊應該是做得相當早的。當時一方面自己沒錢,同時也想,試用廣告來養刊物。
我在香港時就調資了很多刊物,都是這種模式,我以為這是值得嘗試、對周刊一定會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廣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內容。編一本三聯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點,這一點,絲毫也不可動搖。
經營模式的改變,資金結構的變化,必然帶來功能結構和人才結構的變化,在原則的基礎上我們為自己爭得了一點自由,這對周刊的持續發展十分重要。
當然,投資方的情況也很不一樣。第一任投資方因政策原因撇走,顆粒無收,我覺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資方撇走則是因觀念不合,在內容上我們不肯讓其干預。第三任則是他們本身的資金出了問題。而每一次的問題又都牽涉到編輯隊伍的穩定,因此這條路真是走得十分艱難。楊浪走後幾個月,一次在機場遇見,他過來招呼,說:「前幾天我媽還在問:你們老董還在堅持著哪?!」我們大笑。
可是過後想想,心裡也有點不好受。為辦這個周刊,我們頭上頂著雷子 《 編按:壓力和風險),因為社會資本參與經營的政策還不清晰;資本未有回報,心裡也覺歉然;平台不夠穩定,更有負主編和年輕的編輯記者;在社裡,由於周刊是體制外的經營方式,工資待遇等與社內不同,也必須向員工解釋、做好工作;對社委會,為了不混淆兩種體制的經濟關係,也為了節省每一分錢花在周刊建設上,不但我自己,而且連社裡,都不許花周刊的一分錢。所以當時就有人問我:既然各方面都沒好處,你還幹什麼?我苦笑,可是心裡總存著期許:或許再咬咬牙,過了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還做著印鈔機的夢,我告訴他們:「是的,好的周刊就應當是印鈔機。」
三聯品牌對一些有看文化情結的投資方還是有影響力的。第四任投資方在 1995 年 8 月後開始進入。為此,我十分緊張,再三再四地講困難、講問題、講風險,當然也講我們的原則。希望他們能想清楚再進入,決心進入就需相對穩定。周刊再也不能折騰了。
作為第三任事,上的主編(真正編了雜誌的),朱偉受命於危難之中。朱偉的進入,使周刊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新時期。這個階段,朱偉、方向明、潘振平三位都功不可沒。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周刊的故事(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傳媒卷)的圖書 |
 |
周刊的故事(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傳媒卷) 作者:三聯生活周刊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社會人文 |
$ 396 |
大眾傳播 |
$ 39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周刊的故事(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傳媒卷)
十五年的中國變化,一本周刊怎樣記錄?
九十年代中,北京出版人借鑒香港的周刊經驗,在內地率先開創用市場化方法運作的周刊。中國傳媒業從此開始一個更快、更好看、更開放、更富有的時代。
這個時代也是中國實力崛起的時代,財經問題、政治問題、社會事件,每一件重要新聞事件被挖開,都有錯綜複雜的關係,敲開這些新聞的門,需要多大的勇氣和獨立的態度?
這本書裡,有一份周刊十五年來對中國話題的選擇,以及新聞背後記者的真實手記。
作者簡介:
《三聯生活周刊》:
《三聯生活周刊》的前身為鄒韜奮先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創辦的《生活周刊》,1995年由三聯書店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於北京復刊,其定位是做新時代發展進程中的忠實記錄者:力爭以最快速度追蹤熱點新聞的前提下,更多關注新時代中的新生活觀,「以敏銳姿態回饋新時代、新觀念、新潮流,以鮮明個性評論新熱點、新人類、新生活」。
「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系列:
《三聯生活周刊》創刊至今逾十五年,而近十五年,恰好是中國發生最大變化的時期。我們從這十五年的封面故事中精選具代表性的文章,分門別類出版,讓讀者回顧中國
章節試閱
現在出版界盛說「品牌」。我輩有時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維護「品牌」的從業者行列。其實,像我這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成長的出版學徒,長期以來,何嘗有過「品牌」觀念,我們只知道聽上面的話,不出上面不中意的書刊。你去自創一個什麼東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豈不是自找麻煩 • 自討沒趣?這種觀念,我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末。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編 《 讀書 》 雜誌,「品牌」說似乎稍稍有點露頭。但愚魯如我,直到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光景,才開始想到:在那個叫做「生活 讀書 新知 三聯書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該自己設計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三聯生活周刊
- 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1-01 ISBN/ISSN:978962043187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大眾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