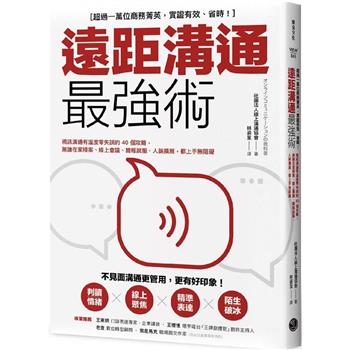增訂版序
(香港)陳平原
說實話,這冊談論日本的小書,既非學術著作,也不是旅遊指南,只是個好奇的讀書人「行萬里路」時的隨筆札記。正如初版後記所說,「不管此前還是此後,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學專家」。此次增訂,雖頗多補充,也仍不脫「清新卻淺陋」的基本面貌。
書中所收各文,寫作時間最早的,當屬撰於一九九〇年六月的〈今夜料睹月華明〉、〈春花秋月杜鵑夏〉、〈書卷多情似故人〉。這三則隨筆,是我第一次旅日歸來的習作,走馬觀花,興奮不已,真誠但淺薄。作為我「閱讀日本」的前史,依舊值得保留。至於「閱讀」之後,偶爾撰寫涉及日本的文章,那都是學術交流的副產品。
幾年前,我在〈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如何與漢學家對話〉中談及:「二、三十年前,中外學者交流少,見面難,一旦有機會,都渴望瞭解對方。於是,努力表白自己,傾聽對方,尋求共同研究的基礎,在一系列誠懇且深入的『對話』中,互相獲益,且成為長期的朋友。現在國際會議多如牛毛,學者們很容易見面,反而難得有推心置腹的對話。不是就文章論文章,就是為友誼乾杯,不太在意對方論文之外的『人生』。至於只看重對方的身份、頭銜、象徵資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第264—2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很高興我「閱讀日本」的主體部分,形成於交流尚屬難得、風氣也未變化的二十多年前,各方的「表白」與「傾聽」都很真誠。那時中日關係很好,普通民眾沒有那麼多解不開的心結,學者之間更是相互理解與支持。
正因此,初版《閱讀日本》整體形象「很陽光」。除了時代氛圍,還有個人經歷。我應日本學術振興會邀請,以北大教授身份赴日,頗受優待,自然更多地看到日本社會及學界美好的一面。也曾聽到留學生吐槽,可我對他們的委屈與憤慨體會不深,無法代言。閱歷如此,加上明確的問題意識──為自家療病,而不是為他人開藥方──致使我更多地談論日本的好處。初版後記中,我引用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後記〉,稱「並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那確實是當初的寫作思路。直到今天,我仍持此立場。其中的關鍵,我並非日本學專家,偶爾「閱讀日本」,主要目的是照鏡子,正自家衣冠。畢竟,「自家有病自家知」。
今天的中國人,不知有多少還記得「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這個詞。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起步不久,中國的經濟實力及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間距離很大,民眾剛走出國門,面對完全陌生的花花世界,往往會有眩暈的感覺。這個詞現在偶爾還在用,但已經沒有那種切膚之痛了。須知八十年代談文化震撼,是包含痛苦、彷徨與反思的,如今則只是旅遊標簽,如旅遊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文化震撼之旅.日本》、《文化震撼之旅.法國》等。
因有錢而不再低調的中國遊客,成群結隊走出去,自然是休閒觀光加購物,再就是對異文化「痛下針砭」。這與我們當初的惶惑與心虛,見賢思齊、臥薪嘗膽、奮起直追,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經過好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國人方才有今天這點挺直腰桿說話的底氣。我不喜歡「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說法,因那好像是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其實,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九曲十八彎,好不容易有了今天這樣的局面,若不體會此前的苦難與屈辱,以為一切都是應該的,也就不怎麼懂得珍惜了。
我受「五四」新文化的影響,始終警惕魯迅所譏諷的「愛國的自大」。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作為大國子民,中國人普遍抱有強烈的自尊心。而且,骨子裏的「傲慢與偏見」,一不小心就會浮出海面的。對於這一點,國人必須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我看來,走出去,面對大千世界,還是以鑒賞為上。以中國現在的發展水平,還不到擺闊的地步;即便真的富裕了,最好也能做到波瀾不驚。若「一闊臉就變」,未免顯得太沒文化、也太沒出息了。理解並尊重那些跟你不一樣的國度、民族、文化、風景,這既是心態,也是修養。
記得很清楚,一九九四年四月的某一天,從小樽開往敦賀的海輪上,我連猜帶蒙地讀報,驚嘆日本人無時不在的危機感―報上稱,換一種統計方式,中國的經濟實力已超過日本。過了十多年,具體說是二〇一一年,這預言終於實現。這只是數字,可我深刻體會到兩國民眾心理的巨大變化。不說中國人為此「第二」所付出的代價(包括環境污染與貧富差距等),就說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及舒適度,與日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大城市不明顯,你到鄉村走走就明白。這也是我不改初衷,願意修訂重刊《閱讀日本》的緣故。
在我看來,日漸富裕的中國人,需要自信,也需要自省,方才能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至於我自己,在很愜意地享受上幾代人根本無法想像的生活便利的同時,「越來越懷念那種個體的、可辨認的、有溫度且有感情的學術交流,以及那種劍及履及的低調的學術合作與教誨」(參見〈「道不同」,更需「相為謀」〉,2015年5月13日《中華讀書報》)。說這段話,是有感於時代風氣的變化。某種意義上,這個時候刊行增訂版《閱讀日本》,是在向多年前啓迪過我的日本文化或幫助過我的日本學者致意。
當初為寫《閱讀日本》,我擬了好多題目,也做了不少資料準備。如今翻閱諸如「和服與羊羹」、「東洋車與博覽會」、「大相撲與歌舞伎」、「水戶黃門」、「泉岳寺裏的說書碑」、「夏目漱石遺跡」、「徂徠碑與福澤墓」、「江戶名所百圖」、「作為遊記作家的貝原益軒」、「櫛塚、遊女與三味線」等題目,以及相關筆記,依舊興趣盎然。只是當初沒能一鼓作氣,回國後雜事繁多,匆匆將手頭文章結集,再也沒有時間與勇氣續寫。再說,時過境遷,年輕一輩的學識、見解與文采,均超過我當年的水平,也就不好意思再表演下去了。說到底,那是特定時間、特定境遇、特定心情下的產物。
此次增訂,保留初版的序言及後記。夏君的序言光彩依舊,自然隻字未動;我的後記則頗有蛇足,因新書篇目調整,最後一段自我辯解顯得多餘。只是為了保持原作風貌,同樣未作刪改。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附記:此文本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將刊行的《閱讀日本》增訂版序,移花接木的理由是,北京版更多呈現作者的寫作歷程,香港版則側重讀者的閱讀趣味,二書的結構及篇幅有較大差異,但基本立場與思路是一致的。當然,考慮到香港版有不少調整,序言也做了若干刪節。經過這麼一番騰挪趨避,相信港版更適合一般讀者的口味。
初版序
夏曉虹
讀書人真是不可救藥,「周遊日本」最終變成了「閱讀日本」,而且讀後有感,寫成文字,結集成書,這確是平原君一貫的作風。我不知道,假如在一個世紀前,我看到的會不會是「竹枝詞」一類的紀事詩,當年出遊日本的文人學者,沒少為我們留下這些東西。如今,我們還可以借助黃遵憲等人的詩作,探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曾經給予中國怎樣的衝擊。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必須即席賦詩的時代已經過去,若要說清楚對於異國的感受,我覺得散文還是好過詩歌。黃遵憲之所以只能以《日本雜事詩》為《日本國志》的副產品,恐怕原因也在此。
據說,地球正在變小。「地球村」的說法使遠隔重洋的國家都成了我們的近鄰,傳播媒介的進步,更讓我們打開電視機,便可「目遊」全球。古語所謂「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好像確已成為現實。如此說來,瞭解他國在今日並非難事。但這其中不無誤會。距離感的接近其實只令我們對別國平添了一份親近,以為在地球上任何一處發生的事情,都非與己無關。而對植根於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深處的文化基因,書本和畫面原有力不能及之處。更何況,個人的體會乃是人生經驗的一部分,非足履其地,親接其人,不會有真感動。儘管臨行前購買了許多介紹日本文化思想以及風土人情的書籍以備查考,平原君顯然還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與心智。
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是個能寫好多本書的大題目,不必我說,也非我所能道。平原君從一些小開口進入,借談日本,反省中國,屬他的別有會心,有此書在,也無須我饒舌。既然「閱讀日本」無論大題小題均可不作,只有另尋門徑。好在我本與平原君同行,且嗜遊勝於善讀,故而對於「周遊日本」的話題尚可發言,正不妨權充導遊,以明行蹤。
差不多一個世紀前到過日本的康有為有一方長文別章,在其門人友生的回憶文章中常見提起:「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歷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四十萬里。」不說氣魄,單是行跡,便令我輩望塵莫及。「歷遍四洲」不易做到,追蹤前賢,經一國,遊四島,應可實現,誰知還是功虧一簣。雖有大半載的光陰,四國卻只在新幹線的高速列車上,隔着車窗,隱沒在瀨戶大橋的另一端,引人遐想。即便如此,我們的遊興之高,已使日本友人驚嘆不已。
說是同行,我實比平原君遲到三個月。當我取道香港抵達東京時,節令已進入冬季。大約是東京僅見的窗外那株紅楓也不再能堅持,三兩日後,葉片便黃萎凋落。整個冬天,只得蟄伏東京,在市內各處遊蕩。好在學會了乘車,可以看地圖認道路,穿行小巷,尋找僻寺,遊走大街,領略繁華,原也樂趣無窮。東京作為世界屈指可數的一流大都市,國際化程度自是極高。聖誕節銀座高雅精緻的櫥窗藝術、表參道學自巴黎的聖誕燈樹、靜靜等待參觀西方印象派畫展見首不見尾的長龍隊伍、為迎接新年而舉辦的幾十場爆滿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演出,都是在日本其他各處無法得見的景象。依靠熱心朋友的指點,我們有幸一一領會。不過,即使在東京,日本的傳統仍未被國際化淹沒。印象派繪畫之外,此時最多參觀的便是浮世繪畫展,特別對《名所江戶百景》的作者安藤廣重尤有好感。原先在國內難以接受的相撲,易地東京卻有了新體認,每年照例舉辦的新年後開始的大相撲初場及四季重大賽事,竟成為收看最多的電視節目。而大有機會贏得力士最高級別「橫綱」之稱的,反是來自美國、入籍日本的曙。所謂「越是民族化,越是國際化」,在此似乎也得到了證明。
進入三月,梅花初綻,預示着春季的來臨,我們的株守東京也告結束。第一次遠足,便是去以觀梅聞名的水戶。日本人的酷愛自然,也許因了高度現代化都市生活的阻隔,而更形強烈。電視中日日報道梅花又開幾分的訊息,使東京後樂園中的遊人陡增。花瓣微張的梅枝,已牽惹得遊客駐足不去;幾株散漫開放的野花,竟也被精心地以竹絲圈起。待到得見水戶偕樂園沿水漫山紅白紛呈的梅林,千姿百態,不修邊幅,不禁為其蓬勃的生氣而傾倒,東京園林的精緻中所透現的雕琢實無法與之相比。
三月底,在伊豆半島突見櫻花,又是另一番情致。只因此地較東京偏南,兼之海風和暖,花期先在此登陸。不過,伊豆更讓人着迷的還是山嵐海色與舞女走過的天城隧道,散落平川的櫻樹倒也無意爭奇。此後,好像成心追隨櫻花線(櫻花在各地的開放,一時間成為電視關注的焦點),從伊豆到東京,一直尋跡至札幌,半個日本的櫻花盡收眼底。此中,最為壯觀的究屬東京,上野公園、千鳥之淵與多摩川邊如雲如霞的櫻花與如癡如醉的賞花人,夜以繼日地互相廝守,自花開到花落,使得恭敬有禮的日本人,在這幾日間忽爾脫略形跡,縱情飲樂,迥異平常。
身居東京,橫濱、鐮倉只算近在肘腋,可小小不言。伊豆途中,一位精通中文的日本朋友以「不到長城非好漢」解「不到日光,莫說最好」的日語俗諺,倒勾起了我們對日光山的好奇心。一百多年前,王韜東遊至此,寫下一篇〈遊晃日乘序〉,極力描摹山水之勝及日友護送登山的盛情,成為其扶桑之行結束時最精彩的一筆。而此遊的發生,即是因聞說該處「土木丹青之盛,窮工極美,甲於天下」,「西人來日東者,無不往遊日光,否則以為闕典」(《扶桑遊記》卷下),可見「最好」之說由來已久。百年過後,東照宮仍是那般巍峨壯麗(或許更加修飾一新),華嚴瀑仍是那般氣勢磅礴(其實因岩崩高度已略有減損),中禪湖仍是那般煙波浩渺(不知面積比前如何),連一路開車送我們登山、觀瀑、遊湖,直至天黑盡方抵達其長野山中的別墅款待我們住宿的日本朋友,也是那般周到熱心。
按照預訂計劃,五月初,便當由東京轉移至京都。但不過十日,我們又沿新幹線原路返回,且更驅向東北,目的地是北海道的札幌。大約一國之中,北方人總較南方人顯得豪爽,風光也自不同。而北海道的開發不過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所取法的美國德克薩斯州城鎮格局與建築風格,使得北海道大學中兩行茂盛沖天的白楊樹,竟成為札幌的代表物。港口城市小樽,也以厚實堅固的石頭倉庫構成獨特的地方景觀。這多少給我們留下一些荒野的氣氛,並感覺其中充盈着活力與沛然不可禦的氣勢。北海道大學也不例外,校園裏大面積的丘陵綠地,在日本當真是首屈一指,對於一個島國來說顯得頗為奢侈。更引人入勝的是夜幕降臨以後,草地上便聚集着一叢叢的人群,燒起成吉思汗火鍋,歡呼痛飲,烤羊肉的香味瀰漫在空氣中,處處可聞。我們無緣加入這些快樂的人群,卻沒有錯過品嚐美味的機會。在札幌啤酒廠附設的啤酒園裏,大塊吃肉的同時,我們也暢快地大口喝着泡沫四溢的新鮮啤酒。熱情的日本「北大」的老師,還領我們見識了如同家庭般親切隨便的小酒館。
作為一次難得的經歷,北海道之行在交通工具的選擇上也不同尋常。日本國土不算大,新幹線列車的運行速度又極高,被稱作「寢台列車」的夜間火車只在很少的線路開行。乘此種車去札幌的一段路程,成為我們整個日本漫遊中最闊綽的旅行。從仙台上車,坐的是帶有電視機與桌、櫃的頭等車廂,但這仍然不能使我安睡,火車車輪碾壓鐵軌的雜音一如往常。回程改乘輪船,從小樽出發,走日本海。一路觀日落日出、海浪海島,否則歪倒床上看電視錄像,雖三十餘小時,亦不難度過。
從京都去北海道,魯迅留學過的仙台本為路經,自不可不遊。將魯迅上課的教室、借宿的民房以及各處建立的紀念碑一覽無餘之後,心心念念便只在松島。早已聽不只一位日本友人朗誦過俳聖松尾芭蕉的一首名作,若譯成漢文,不過是翻來覆去的幾句:「啊!松島!啊!啊!松島!!」據說,當年芭蕉目睹松島,心中生大感動,所有的語言都顯得貧乏無味,不足以傳美景於萬一,便只能反覆詠嘆其名,使此作在俳句體中別具一格。乘船遊行在數以百計綠意葱蘢卻又姿容各異的大、小島嶼之間,駐足岸邊遠眺這星羅棋佈、總名「松島」的海上奇觀,所能做的便是頻頻舉起照相機與攝像機,感謝自然造化的神奇與人類文明的創造。
松島以其美貌,入選「日本三景」之一。既得其一,便思佔全,免得辜負了好山水、好時機。北上之後,南下已很便捷。六月下旬,即使是海洋性氣候的日本,天氣也夠炎熱。此時向南,頗有苦中作樂的意味。在前往九州的路上,我們照例沿途遊觀,而橫豎說來,廣島都是最重要的一站。
歷史上軍國主義勢力的集結地,使廣島在歷次對華戰爭中均充當了橋頭堡;原子彈的爆炸,又讓人們在面對廢墟時心情複雜。與殘酷的戰爭景象相對照,廣島市附近的宮島則提供了美妙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宮島的山光海色固然佳勝,不過,若沒有嚴島神社,其能否入選「三景」大成問題。讀《平家物語》時,對歷史上曾經叱咤一時的平清盛家族所信奉的嚴島神社留有深刻的印象。舉行大戰的前夕,到這裏祭拜守護神的儀式總給我以悲壯感。而遠遠從海上看到藏在海灣深處的這組紅色建築的第一眼,便證實了我的感覺準確無誤。嚴島神社不像一般的神院寺廟建於平穩的陸地,偏偏選址在海灘。來時雖已落潮,但留在巍峨的神社大門附近的水跡,令人自然生出浪擊底部支柱、整個神社浮動海面的遐想。最近一次颶風造成的若干殿宇傾覆的後果,至今尚未消除乾淨。無法把握的不安定狀態,與迅速覆滅的平家的命運一樣,為壯觀的嚴島神社塗上了一層悲劇色彩。
彷彿由此設定了基調,悲壯成為我們九州之行的總體感覺。當然,在長崎建造的海外最大的孔廟中,徘徊於七十二賢人的石像群間,引發的只是自豪感。而在佐世保的山巔眺望煙雨朦朧的九十九島,下山行經日本最大的美國軍事基地;遊長崎而品嚐那首著名的歌《長崎今日又下雨》的況味(初聽此曲的日語歌詞,是在札幌的小酒館),瞻仰將近四個世紀前為基督教而流血的二十六聖人殉教紀念青銅像;在驕陽似火的日子,登上為消耗各地諸侯實力而修建的堅固的熊本城,憑弔烽煙遍地的古戰場遺跡;於阿蘇山火山博物館觀看在此地無數次上演的火山噴發、熔岩溢淌的場景,遊目火山地區長流不斷的河水、綠草茵茵的牧場;漫步福岡市區,邂逅抗擊元軍的歷史遺存……幾乎每一空間與時間裏,充塞胸中的都是既悲且壯的旋律。九州不愧為日本勇士的出產地,連至今盛行不衰的相撲運動,獲勝的大力士們也仍以到熊本的吉田司家領取證書為榮典。
而除了東京,在日逗留期間居住最長的地方便數京都了。正好趕上百年難遇的平安建都一千二百周年,各類慶祝活動競相開場。能樂演出、插花展覽、茶道表演一時紛集,雖無法細細品味,卻足大飽眼福。散佈京都各處大大小小古老的寺院,自有一種擋不住的誘惑,我們也如同所有的國外遊客,一邊抱怨着門票的昂貴(一般五百日元即相當於人民幣近五十元一張票),一邊仍不自禁地進出。為配合建都紀念,例行的城市遊行娛樂活動「三大祭」也準備得格外賣力。兩年前的十月來京都,機緣恰好,觀看過以追溯歷史為主題的「時代祭」。剩缺的兩次,便要靠此行補完。五月舉行的「葵祭」,係由春季祈求豐年的儀式演化而來,尚顯得頗為簡樸。七月進行的「祇園祭」,在神社排練,歷時既久,人們的熱情也更高。十六日晚間,如潮水般的人流,擁聚在四條烏丸的大街上觀看高大的花車。次日,填街塞巷的人群又立於烈日下,等候一輛輛裝飾繁華、名目繁多的花車在器樂的吹打聲中通過京都的主要路口。這項活動最能顯示寺院神社在京都市民生活中的地位,其所以為「三大祭」之首,道理或許也在此。
而在等待「祇園祭」的間歇,我們終於不負此行,抽空圓了「三景」之夢。安排行程的京都大學朋友,先引領我們遊覽國外來客極少觀光卻很古樸有味的出石小城,繼而乘旅遊車沿丹後半島欣賞海礁斷崖與下層置船上層住家的舟屋,終點站便是赫赫有名的天橋立。與宮島的得益於人工建造的嚴島神社不同,天橋立純然以自然力取勝。特殊的港灣走向與潮汐作用,使泥沙反覆衝擊形成為一道天然的長堤。除去一段小小的缺口以鐵橋填補,天橋立渾然一體的結構橫亘海灣,猶如一條縱貫兩岸的天生橋樑。從船艙裏賞玩海上落虹,踏足在這帶狹長而堅實的土地上,登臨山頂遠眺封鎖海灣的堤防,我們從各個角度把天橋立看了個夠。
應該感謝日本的習俗,喜用「三」這個數目字,而不是如同中國的偏好「八大」與「十全」,我們才得以毫無遺憾地佔盡日本的美景。其他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名勝也不在少,「三名園」中水戶的偕樂園與岡山的後樂園,「三名城」中的大阪城與熊本城,「三大建設奇跡」中的新幹線與津輕海峽的海底隧道,我們均曾身臨其地。我不敢說在日本讀了幾本書,倒確實是走了萬里路。所經歷的名山勝水、市景鄉風,足以讓我感覺良好。
不過,平原君日本歸來,寫下了近十萬字的閱讀筆記,我則只在東京與京都分別郵寄過兩則應命短文,真令我這位與平原君結伴的遊客愧煞。好在此為後話,出遊的當時,我可是樂不思其他。
平原君囑我寫一兩萬字的長序,以充(「充」與「光」形近)篇幅,誰知長行短說,五千多字便已打發掉「周遊日本」這個大題目,實在太沒本事。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自日歸來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