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樣年華》的「對倒」藝術(摘錄)
時空交錯的複調敍事
王家衛將劉以鬯的小說《對倒》的意念搬上銀幕,入圍法、德、英、意、澳電影界的「最佳外語片」獎,被美國CNN評為「十八部最佳亞洲電影」第一位,是歐美影評界綜合評價最高的華語電影之一。一部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經過影像的轉換成為世界電影史上頗受矚目的華語電影,不得不說是改編的成功。
從情節上看,《花樣年華》講述一個簡單的婚外情故事,除三處字幕引自《對倒》外,人物形象、情節均與原著沒有相似之處。但在電影語言方面,導演參照小說原著的敍事結構和文學技巧,通過敍事、剪輯、配樂、場面調度等電影語言構成聲音/畫面、時間/情感、歷史/記憶以及人物之間的平行或交錯,在豐富的形式與風格中蘊涵深刻的思想。王家衛談到:
我對劉以鬯先生的認識,是從《對倒》這本小說開始的。《對倒》的書名譯自法文Tête-bêche,郵票學上的專有名詞,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對倒》是由兩個獨立的故事交錯而成,兩個故事的主要人物分別是一個老者和一個少女,故事雙線平行發展,是回憶與期待的交錯。對我來說,tête-bêche不僅是郵票學上的名詞或寫小說的手法,它也可以是電影的語言,是光線與色彩,聲音與畫面的交錯。Tête-bêche甚至可以是時間的交錯,一本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小說,一部二○○○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一九六○年的故事。
這種借鑑原著的敍事結構加以發揮的「意念」式改編,恰如電影理論家安德魯(Dudley Andrew)所肯定的那一類改編,即「原著的『組織』和『美學』受到極大程度的尊重而沒有被吸收到改編過程中」。這給導演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發揮空間,最終形成獨具個人風格的「作者電影」。可以說,《花樣年華》革新電影藝術的表現形式,為文學到電影的改編提供多樣的探索路徑。在這一過程中,當代藝術電影如何「消費」文學?電影與文學結構如何對話?文學改編電影折射出當代香港怎樣的文化政治變遷?
劉以鬯的《對倒》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開始在香港《星島晚報》連載,是一部約十一萬字的長篇小說。一九七五年作者將其改寫為短篇小說,在《四季》發表。跟長篇《對倒》相比,短篇刪減了情節和冗長的意識流動,縮小篇幅,但結構沒有較大改變。小說講述來自上海的移民淳于白、香港本土少女亞杏一老一少在街上相對而行,兩人都有綿密的意識流動,老者回憶過去,少女憧憬未來。兩人偶然在同一個電影院、公園同一張長椅上比鄰而坐,互相猜測對方,最後一南一北遠去。小說自由出入於虛實之間,無論時空上還是人物身份或意識流動上,都構成平行或交錯、相對或相反的關係,謂之「對倒」。
《花樣年華》的三處字幕來自長篇《對倒》,影片結構上的「對倒」首先表現為男女主角的命運及活動空間的交錯或平行。「一九六二年香港」,報社主編周慕雲(梁朝偉飾)與蘇麗珍(張曼玉飾)同時搬進一幢上海人居住的公寓,某天,周、蘇兩人發現自己的配偶暗地裏結合,他們猜測、試探、扮演那對戀人如何開始,卻不知不覺愛上對方。迫於世俗輿論的壓力,兩人不得不壓抑熾熱的愛情。最終,周慕雲選擇離開,前往新加坡工作;蘇麗珍則留在香港繼續生活,彼此再無交集。「對倒」一方面是男女主角愛情與命運的錯位,另一方面是兩人時空上的平行或交錯。在抒情式的緩慢節奏中,男女主角的邂逅、錯開,正貼近片頭引自《對倒》的文字:「那是一種難堪的相對。她一直羞低著頭,給他一個接近的機會。他沒有勇氣接近。她掉轉身,走了。」這是以形式製造戲劇的張力:昏暗的樓道、悶熱的空氣、纏綿的雨水、男女主角愛情的錯位,表現出一種欲言又止的含蓄情感。
影片突破線性敍事技巧,有意製造重複的場景,藉此表現時間、人物情感的緩慢變化過程。與劉以鬯小說原著中男女主人公的生活/意識時空從平行到相交的變化一樣,影片最具標誌性的場景是男女主角多次一上一下、一前一後擦肩而過,配合背景音樂大提琴協奏曲Yumeiji’s Theme,四分之三拍的節奏,複調調式,低婉迴旋,內斂中透著淡淡的哀愁和傷感。此處鏡頭多次定格在同一個昏暗的樓道,拐角處一盞白熾燈,燈下牆面上貼著舊報紙的廣告──典型的一九六○年代香港街角。在不變的場景中,通過女主角蘇麗珍旗袍的變更表現時間的流動,使重複的同一個場景、同一個動作飽含時間的縱深感和連續性。這集中體現了王家衛的「對倒」意念和日常生活美學,成為「有意味的形式」。
通過重複同一場景,一方面表現男女主角相似的處境(受自己配偶背叛的疑慮),以及因同樣的憂鬱、孤寂而產生惺惺相惜的心情;另一方面從錯過、擦肩而過到同行的細微變化,表現他們在日復一日重複的生活中漸行漸密。王家衛認為:「日常生活總是固定不變的—同樣的走廊、同樣的樓梯,同樣的辦公室,甚至同樣的背景音樂,但我們可以通過不變的背景看見這兩人的變化。重複反而使人更加看清楚這些變化。」影片在重複的場景中通過細節的變化,推進情節的發展,同時也在緩慢的敍事節奏中營造一種詩意、抒情的氛圍。伴隨Yumeiji ’s Theme優雅的律動,大提琴華麗而憂愁的曲調,將男女主角的落寞、傷感如泣如訴般演繹出來。此時,人物心理活動、情感成為敍事的主體,取代傳統電影中的情節。
銀幕敍事的主體:時代
影片還通過精緻的現代物品還原時代現場,女主角二十多套搖曳的旗袍、男主角復古的服飾(和髮型)、咖啡館、出租車、公寓、電話機、收音機,加上經典的老歌,在在喚醒人們的記憶和懷舊情緒。譬如通過一九六○年代典型的電台播音形式插入「金嗓子」周璇的歌曲《花樣的年華》,鏡頭在蘇、周兩人之間移動,兩人背靠著,中間隔著一堵厚厚的牆,再次呈現空間「對倒」般平行。周璇的歌曲是老上海典型的代表,不僅營造出濃郁的懷舊氣息,也以音樂的抒發代替情節的敍事,傳達出兩人難以言說的愛,表現出含蓄的美。從情節上看,周璇《花樣的年華》在時空中流淌時,鏡頭在蘇、周兩人所處的空間中流動,而陳先生在廣播中隱形地「出現」,顯示了女主角處在丈夫/情人、家庭/愛情之間的拉鋸中。這裏將人物的意識流動與時間的流淌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音樂和畫面有效傳達出來。此外,周璇的歌曲作為民國上海的典型代表,使影片帶有濃重的上海懷舊意味。
影片尾聲再次將「時代」作為主體推向高潮。「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透著對一個時代深深的眷戀和懷念,鏡頭切換到一九六六年殖民地時期的柬埔寨,戴高樂總統到訪、萬民夾道歡迎的歷史片段。帶著對蘇麗珍難以忘懷的回憶,周慕雲在吳哥窟的斷壁頹垣中,對牆上的石洞傾訴秘密。長鏡頭下矗立的巨型石窟成為時光的見證,有一種地老天荒之感。如洪荒世界般沉寂後,背景音樂Angkor Wat Theme緩緩傳來:循環的複調曲式,三拍子舞曲,風格莊重;主奏大提琴深沉而空靈,小提琴漸次加入,旋律婉轉,三度不完全諧和音程,造成共顫的效果,具有神性之美。此時鏡頭轉為俯拍,前景是一個僧人的虛化背影,順著他視線的方向,周慕雲專注地對石洞傾訴──毋寧說是冥想。高處的僧人是佛性的顯現,見證周淨化自己,抵達性靈之境。在這個穿越了數世紀時空的古老石窟,周將逝去的愛情和所有的回憶永遠留在洞中,塵世的一切隨光與影的律動裊裊飄散,最終重歸生命的原初──空無。最後影片字幕顯示:「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在對逝去時代深深的歎惋中,在憂傷和肅穆、頓悟和超然中,一切戛然而止。周蕾指出,《花樣年華》結尾展現的吳哥窟場景與《春光乍泄》中的尼瓜拉瀑布具有相同的「能指」,即「超越人類世界界限的持久和永恆」。確實,相對日常生活(影片著重表現的對象)而言,吳哥窟、尼瓜拉瀑布遊離於時空之外,表現出相對的永恆性。這種永恆,也是時空乃至宇宙的恆常,相比之下,轉瞬即逝的人生和愛情顯得如此卑微、渺小。從這個層面來看,王家衛的電影是關於時間的哲學。
從《阿飛正傳》(一九九○年)、《花樣年華》(二○○○年)到《二○四六》(二○○四年),王家衛一以貫之地講述一九六○年代香港的故事。這三部電影的人物、情節具有延續性,類型和風格也相對一致:鬆散的結構、瑣碎的生活細節、慢節奏的敍事、開放式的結局,著重表現人物的情感、意識以及對時間、回憶的執著,稱得上是王家衛的「六十年代香港三部曲」。
王家衛為何對一九六○年代情有獨鍾?除彼時的文化氛圍、美學精神讓他著迷以外,深層原因或許還在於一九六○年代能夠成為一九九○年代的鏡像,藉助兩個時代的交錯折射當代港人的懷舊情緒和政治文化觀。譬如,影片結束在一九六六年本身就頗有深意。對此,王家衛指出:「一九六六是香港歷史轉折的標誌。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有許多連鎖反應,迫使港人艱難地思考他們的未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四十年代末從中國移民過來,度過近二十年的平靜期,建立了自己的新生活──這時突然感覺到政治環境的改變迫使他們再次遷徙。一九六六年是一些事物的終結,同時也是另一些事物的開始。」他同時也指出,「戴高樂是殖民歷史的一部分,一個即將遠去的歷史。」殖民地時期的終結、中國內地政局的影響、港人對何去何從的思考、二○四六(從一九九七年算起「五十年不變」後的期限),諸如種種都是香港回歸的隱喻,也是王家衛對殖民地時代終結的反思。
阿巴斯(Ackbar Abbas)用déjà disparu(還沒發生卻成為過去)來形容「新香港電影」,並指出在王家衛的電影中,「這種消失的空間也對更大的時間和歷史經驗產生作用」,「影片並不是從一九九○年代看一九六○年代,而是給我們更易理解的結構:一九六○年代的人看一九九○年代,就像一九六○年代之前的人看一九六○年代一樣,依此類推。」簡言之,九七到來之前,所有的疑慮、不安都是對未來的「預設」,而一旦這個時刻真正到來,對當時的狀態卻不復記憶,人們反而試圖想像此前那個逝去的時代,製造虛擬的回憶。在《二○四六》中,王家衛講述一趟開往二○四六的列車,人們在那可以尋找失去的記憶,沒人想離開二○四六,除了一個名叫Tak的人。如果說《阿飛正傳》、《花樣年華》是從一九六○年代看一九九○年代,那麼,二○四六則從未來看當下。這是對時間、記憶的隱喻性思考,也是對殖民地時代的理性審視。
正如《花樣年華》結尾意味深長的景深鏡頭:周慕雲穿越一道又一道的拱形石窟長廊,猶如穿越長長的時間隧道,與過去告別,回到未來。影片以豐富的藝術形式與不同的文學結構、不同類型的電影中進行跨文化對話,在詩性敍事中展現其對時空、記憶,情感、人生的形而上思考—這正是藝術電影的魅力所在。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香港電影的文化記憶:從文學到電影的跨媒介轉換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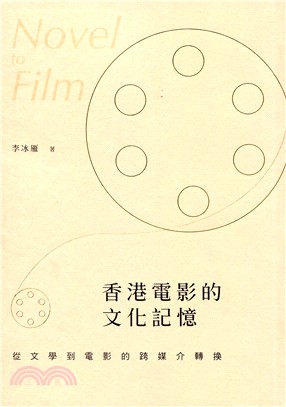 |
香港電影的文化記憶:從文學到電影的跨媒介轉換 出版社:三聯 出版日期:2017-05-2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56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48 |
戲劇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文化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香港電影的文化記憶:從文學到電影的跨媒介轉換
香港電影從對張愛玲小說的直譯式改編,對李碧華小說的改寫,引用劉以鬯、金庸等小說的意念對都市寓言的重述,以及對中國古典小說的顛覆和解構等等,在在講述一座浮城百年滄桑的故事。
在「借來的時空」中,他們試圖從中國傳統的「前現代」中追尋現代香港的文化之根,在全球化語境中念茲在茲地「懷鄉」,而其中的苦悶、頹廢乃至陷入身分的迷失,以及對瞬息萬變時空的無力把握,恰也是都市人的現代性體驗。香港電影將商業性與藝術性,傳統與現代,去國與懷鄉,犬儒與哲學融於一身,最終確立了文化身分的主體性。
作者簡介:
李冰雁,澳門大學哲學博士。現為澳門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惠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師,惠州文化創意產業孵化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文藝理論、電影美學、文化創意產業等。
TOP
章節試閱
《花樣年華》的「對倒」藝術(摘錄)
時空交錯的複調敍事
王家衛將劉以鬯的小說《對倒》的意念搬上銀幕,入圍法、德、英、意、澳電影界的「最佳外語片」獎,被美國CNN評為「十八部最佳亞洲電影」第一位,是歐美影評界綜合評價最高的華語電影之一。一部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經過影像的轉換成為世界電影史上頗受矚目的華語電影,不得不說是改編的成功。
從情節上看,《花樣年華》講述一個簡單的婚外情故事,除三處字幕引自《對倒》外,人物形象、情節均與原著沒有相似之處。但在電影語言方面,導演參照小說原著的敍事結構和文學技巧,通過敍事、...
時空交錯的複調敍事
王家衛將劉以鬯的小說《對倒》的意念搬上銀幕,入圍法、德、英、意、澳電影界的「最佳外語片」獎,被美國CNN評為「十八部最佳亞洲電影」第一位,是歐美影評界綜合評價最高的華語電影之一。一部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經過影像的轉換成為世界電影史上頗受矚目的華語電影,不得不說是改編的成功。
從情節上看,《花樣年華》講述一個簡單的婚外情故事,除三處字幕引自《對倒》外,人物形象、情節均與原著沒有相似之處。但在電影語言方面,導演參照小說原著的敍事結構和文學技巧,通過敍事、...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緒論(節錄)
香港電影除了原創劇作受到關注外,改編自文學、戲劇、漫畫的電影也風靡一時,不僅獲得高票房收益,還屢次在中外電影節上獲獎。香港電影改編自文學作品、題材的典範性和多樣化,為電影改編技術和理論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但也出現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在視覺藝術佔主流的當代,文學何為?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影如何「消費」文學經典?電影怎樣抵抗經典名著「影響的焦慮」而成就自身?電影經驗與文學技巧如何相互借鑑?文學改編電影折射了怎樣的文化政治變遷?全球化時代,面對荷里活的強勢入侵,電影改編如何堅守本土性、區域...
香港電影除了原創劇作受到關注外,改編自文學、戲劇、漫畫的電影也風靡一時,不僅獲得高票房收益,還屢次在中外電影節上獲獎。香港電影改編自文學作品、題材的典範性和多樣化,為電影改編技術和理論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但也出現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在視覺藝術佔主流的當代,文學何為?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影如何「消費」文學經典?電影怎樣抵抗經典名著「影響的焦慮」而成就自身?電影經驗與文學技巧如何相互借鑑?文學改編電影折射了怎樣的文化政治變遷?全球化時代,面對荷里活的強勢入侵,電影改編如何堅守本土性、區域...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張看」香港:張愛玲小說的直譯式改編
一、《傾城之戀》:懷舊的詩學
二、《紅玫瑰白玫瑰》:現代性體驗與主體的身份分裂
三、《半生緣》:亂世悲情
四、《色•戒》:重寫民國歷史
五、「懷舊」電影:想像的能指
第三章 香港身份:李碧華小說的改寫式改編
一、《霸王別姬》:性別意識與香港身份的消解
二、《胭脂扣》:香港銀幕「鬼文化」的歷史視野與現代意識
三、《青蛇》:從「情與理」到「情與慾」
四、通俗小說的類型模式與電影的文學風格
第四章 文藝香港:王家衛電影的意念式改編
一、...
第二章 「張看」香港:張愛玲小說的直譯式改編
一、《傾城之戀》:懷舊的詩學
二、《紅玫瑰白玫瑰》:現代性體驗與主體的身份分裂
三、《半生緣》:亂世悲情
四、《色•戒》:重寫民國歷史
五、「懷舊」電影:想像的能指
第三章 香港身份:李碧華小說的改寫式改編
一、《霸王別姬》:性別意識與香港身份的消解
二、《胭脂扣》:香港銀幕「鬼文化」的歷史視野與現代意識
三、《青蛇》:從「情與理」到「情與慾」
四、通俗小說的類型模式與電影的文學風格
第四章 文藝香港:王家衛電影的意念式改編
一、...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冰雁
- 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5-26 ISBN/ISSN:978962044114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