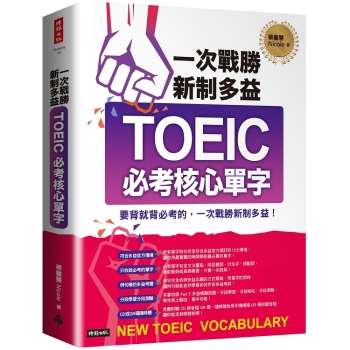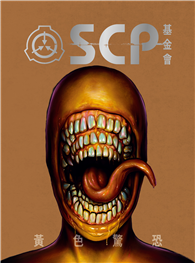序一:為我兒義行驕傲
蔡文力的祖父很喜歡說故事,小時因逃避迫害跟曾祖父從大陸遷到香港務農維生。祖父年青時,在上水火車站旁邊租了一塊農地種瓜種菜,大部份收成被運到石湖墟蔬菜市場出售。菜多的話,他就會搭單車沿着公路運到油麻地榕樹頭出售,來回要六小時,非常辛苦。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攻佔港島太平山,香港自此淪陷,當時祖父十五歲。日軍在港期間大隊駐軍粉嶺軍地,早上會派一名翻譯員到石湖墟買菜。翻譯員跟祖父年齡相若,每天走過街市都會點點頭。有一天,日軍受到本地的反日游擊隊襲擊,死傷多名。因此日軍四處搜捕游擊隊,拘捕可疑男子,祖父和數名榕樹頭的小販也因此而被捕,用繩捆綁後被送到軍部準備槍斃。行刑前,該名翻譯員剛巧經過,看見祖父被捆綁便問他發生了什麼事。祖父告訴他自己被誤會,說:「我只是一個農夫,不是游擊隊。」那翻譯員便對隊長說祖父是個菜農,他們吃的蔬菜都是向祖父買的。結果當日只有祖父一個人獲釋。
為了解決居住問題,祖父在農田上搭建了一間簡陋的木屋。屋身用木料和鐵皮構成,瀝青紙和木條做屋頂,每逢下雨便漏水。颱風溫黛襲港那年,天文台掛起十號風球,木屋整天受狂風暴雨襲擊,屋前面的河流也暴漲起來。不幸,風力越來越大,將屋頂吹到四五百米以外,全家只有等到天亮,幾兄弟才去尋找屋頂重新搭建木屋。洪水將河流的魚丶蝦衝到屋前的池塘,爸爸早上便跟鄰居一起到池塘捉魚,玩個不亦樂乎。突然,爸爸腳上傳來陣陣痛楚,不知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伸手一摸,從水中抓起一支似木棍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條兩丶三尺長的鱷魚!大驚之下爸爸拋下那條鱷魚,大叫:「鱷魚呀!鱷魚呀!」便狂奔回家,小腿也被咬去了一塊肉。兩歲的蔡文力也住過這木屋,坐在地上時母雞會走過來陪他,還送他一堆墨綠色的禮物,弄得他滿手芝麻糊(雞糞)!屋外有個水井,我們要用鐵絲網蓋住,免他失足丟進去。那時候,有條小黃狗整天跟住他,每日下午5時一聽見火車聲便一起跑出去接爸爸。
後來爸爸去外國深造,認識了一些非洲的大學同學,知道他們也很窮困,生活艱苦。所以當爸爸知道蔡文力要去非洲研究伊波拉病毒,為中國人爭光,他是贊成的。蔡文力第一次想參加無國界醫生組織時,媽媽極力反對,所以只好放棄。但當塞拉利昂爆發伊波拉疫症,他毅然加入赴非洲的團隊近距離接觸這病毒,不過要保密,一定不能告訴媽媽,只通知了妹妹。其實媽媽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他去闖天下,造福社會,但又想:「如果風箏飛得太高、太遠,跌下來時,恐怕會無比痛楚」。去到第三世界國家,在一個不毛之地與伊波拉病毒搏鬥,氣溫三十五度以上又要穿上全套保護衣工作,怎受得了?不暈倒才怪。有次在學校演講中,蔡文力説到西非生活不易,每天要工作十幾小時令他瘦了兩個碼。往西非的團隊成員回國後,身體出現這樣那樣的異常情況,賠上了健康。媽媽聽到後心痛萬分,當場淚如雨下。正如富蘭克林說:「經驗是一所代價昂貴的學校。」
蔡文力在非洲造福了不少人。感謝上天賜我倆一個博愛、無私的兒子,在非洲的大汪洋中為他們注入了一股新活力。
爸爸媽媽
序二:挑戰時刻,香港人也有種責任
執筆之時,想起原來我和蔡文力相識已經超過30年。
我們中一讀同一班,你坐在我隔離位。我們經歷過求學、青春期、升學、移民、戀愛、失戀、搵工、失業、創業、獲獎;我們曾一起在黎明時份看日出,一起衝上雲霄跳降落傘,討論人生意義,分享歡樂與憂愁。我們不經不覺成為對方摯友。雖然現在不會時常見面,但重要時刻都會分享、支持對方。
當你在WhatsApp告訴我:我現在在西非塞拉利昂。
我完全不理解。好端端的在英國過着文明的生活,在塞拉利昂的日子,肯定沒有冷氣,到處屍骸遍野。你有一日發了一張鱷魚張口的照片給我,輕描淡寫談你在塞拉利昂的工作,還說塞拉利昂也有獅子山,也有聖芳濟中學。我嚇了一跳,你會不會有危險?
我曾為多個國際品牌做公關顧問,做慈善都是為了企業形象或曝光見報。你不顧安危跑到老遠去對抗疫情,成本這麼高,可以有什麼回報?我不明白不理解,但我相信你。我只可以祝願你平安。
後來,你回港開了一個講座,我是座上客。我沒有深究你在塞拉利昂所做背後的意義,我只想利用自己的專業,讓更多人知道你的故事,我只覺得你應該有回報,所以我提名你選十大傑出青年。當時,沒有人相信你可以,因為我們不是名人,我們沒有靠山,我們只是寂寂無名、默默耕耘,但我相信你可以。最後,我們贏了。
在這本書中,一字一行間,穿梭着無情疫症下的生活日常,是這麼遠卻又那麼近。你從來沒有想過什麼回報,卻比任何煩塵俗世下所得出的成就更高,所獲得的滿足感更大。
「挑戰時刻,香港人也有種責任。」這是我競選2019年荃灣區議會時,擊敗對手田北辰時的口號。2019年我也做到了。
我感謝蔡文力,你是我心裡最崇拜的人,是你教會我,我不必變成什麼人,只須用個人的力量和方法去改變自己,改變世界。
劉卓裕
序三:塞拉利昂的真香港人 -
一場疫情,令世界天翻地覆,全球化趨勢可能從此部份逆轉,香港命運也可能出現微妙變化。但其實疫情一直影響世界各地社會發展,只是一般人在事不關己之時,往往選擇性漠視而已。香港抗疫成果得到舉世肯定,靠的自然不是政府,而是廣大醫護人員的專業、無私精神,和普羅大眾的高質自律。在這波疫情之前,其實一直有香港醫護人員走到天涯海角,協助不同地方的朋友抗疫,蔡文力博士是其中一人。
這是蔡博士在西非塞拉利昂對抗伊波拉病毒的故事,像日記,也像紀錄片,記下了一位香港人千里迢迢,走到非洲伊波拉醫療中心當醫護的點滴。從機場前往災區的心情,工作遊走伊波拉醫療中心的紅綠區之間,親眼目睹病情變化的無法預料,在市中心不遠處的亂葬崗,疫情高峰期如同世界末日的浮世繪,都好比《武漢日記》的真實和催淚,也教人認識到當地結構性問題的全貌。難得的是,本書每個章節均有故事性情節,令人讀得毫不費勁,說得輕描淡寫,事實卻是生死相搏,反映來自世界各地,願意在塞拉利昂資源不足、人民危機意識甚低的情況下團結策力,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醫護義工,都是何等舉重若輕。
提起塞拉利昂,在國際關係學界,第一時間自然是想起電影《血鑽》。現實比電影更殘酷,那場慘烈內戰,牽涉大量童兵、酷刑,令全國三分之一的人成為難民,還捲入鄰國利比里亞更複雜的戰爭,卻幾乎不獲主流媒體報導。這個國家怎樣成為英國當年制衡法國殖民地的窗口,屬於昔日英國人的故事;但一個香港人願意走到一般人眼中的「不毛之地」,不是獵奇打卡,而是長期工作,這就是屬於我們的共同故事,也是Globalization的故事。世界這麼近、那麼遠,誰想得到非洲的抗疫經歷,也可以應用在2020年的香港?
伊波拉可能距離我們太遠,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怎樣避免重蹈覆轍,始終對任何人都實用。在西非戰亂下,塞拉利昂的基礎建設根本無力應付伊波拉,加上民智普遍未開,大部份人連叫救護車的概念也沒有,疫情最終大爆發,並非偶然。但2020年COVID-19疫情全球失控,不少重災區都是最發達國家和地方,那又怎樣解釋?假如連發達國家的死亡率也如此驚人,疫情傳到發展中國家,又會有何後果?蔡博士的經歷,訴說了我們的生命是怎樣和大自然連成一體,政體和人在其中又發揮了哪些角色,再回望身旁的這場疫情,讀完本書,會彷彿忽然懂得了什麼,卻又盡在不言中。
沈旭暉
自序:兩個獅子山
這個世界原來有兩個獅子山,一個在香港,另一個在非洲西部叫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獅子山國。2014年伊波拉病毒首次在西非大規模爆發,死亡率佔確診病例的七成,釀成史無前例的人道災難。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發起緊急醫療救援,世界各國也出派醫護團隊前往協助,有數名千萬名義工加入拯救行列,當中包括醫生丶護士丶科學家丶流行病學家丶心理學家丶物流丶電工等等。這班義工來自不同國家,很多從未踏足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亦不熟悉塞拉利昂丶幾內亞(Guinea)或利比里亞(Liberia)三個西非國家的名字。但都不約而同選擇離開自己的舒適區,到當地跟前線人員並肩作戰。這本書便是從伊波拉説起的。我在2015年前飛去塞拉利昂,在伊波拉實驗室為病人測試病毒。估不到一個決定會徹底改變了自己。原來,生命還有很多可能性。
非洲的故事其實應該由非洲人自己講。我不是第一個去抗疫的志願者,也不是救得最多人。就當我的故事為五百多名無名英雄致敬吧。他們都是在這次伊波拉疫情中的犧牲了的醫護和前線的人員。
2019年年尾,武漢爆發2019冠狀病毒肺炎,並且在幾個月內迅速傳播到二百多個國家。香港三聯書店便邀請我出一本書去勉勵大家。全世界最貧窮的西非都可以戰勝伊波拉,最邊緣的人也可以自强不息。There is always hope!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非洲抗疫之路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的圖書 |
| |
非洲抗疫之路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出版日期:2020-07-17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非洲抗疫之路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本書是2016年的傑青得主蔡文力講述他到非洲的義工經歷,他到非洲塞拉利昂研究檢測伊波拉病毒,是勇敢地站在投疫最前線的科學家。
他本來是牛津大學免疫學博士,本可高薪厚職,是甚麼驅使他當年只取僅$400的日薪工作,疫情結束後更籌備「生還者監察計劃」,決定「幫人幫到底」。事件稍告一段落後,回家後竟覺得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毅然再到危險的剛果戰區做臨床實驗?在這些無私的故事背後,他的家人與摯友又是怎樣想呢?
這本書將會娓娓道來他這幾年來的困難與希望,亦給予正受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的所有人一支強力的安定針。
作者簡介:
蔡文力(Edward Choi)
蔡文力,香港出生,初中後赴笈澳、英留學,在牛津大學研究愛滋病疫苗,取得病毒及免疫學博士學位,再赴美作後博士研究。2004年他加入瘋牛症鼻祖Stanley Prusiner的研究團隊,在三藩市加州大學開設隔離設施,研究血液內的CJD脘毒體,確保血庫供應的安全。
2015年西非爆發伊波拉疫症,他毅然加入國際醫療團義工隊,在塞拉利昂的隔離實驗室為病人進行病毒測試。疫症後,他為生還者成立生還者監察計劃,並建設實驗室,致力為當地醫院引進分子診症科技。
塞國內戰多年,叛軍四出砍掉過千平民的手臂。有見及此,他自組社會企業,混合3D打印和傳統技術,為截肢者製作義肢。2016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近年為西非赤貧人口安裝太陽能照明系統。
蔡文力現職倫敦大學助理教授,為熱帶醫學院統籌伊波拉疫苗臨床測試,奔走於剛果和塞拉利昂之間。
作者序
序一:為我兒義行驕傲
蔡文力的祖父很喜歡說故事,小時因逃避迫害跟曾祖父從大陸遷到香港務農維生。祖父年青時,在上水火車站旁邊租了一塊農地種瓜種菜,大部份收成被運到石湖墟蔬菜市場出售。菜多的話,他就會搭單車沿着公路運到油麻地榕樹頭出售,來回要六小時,非常辛苦。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攻佔港島太平山,香港自此淪陷,當時祖父十五歲。日軍在港期間大隊駐軍粉嶺軍地,早上會派一名翻譯員到石湖墟買菜。翻譯員跟祖父年齡相若,每天走過街市都會點點頭。有一天,日軍受到本地的反日游擊隊襲擊,死傷多名。...
蔡文力的祖父很喜歡說故事,小時因逃避迫害跟曾祖父從大陸遷到香港務農維生。祖父年青時,在上水火車站旁邊租了一塊農地種瓜種菜,大部份收成被運到石湖墟蔬菜市場出售。菜多的話,他就會搭單車沿着公路運到油麻地榕樹頭出售,來回要六小時,非常辛苦。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攻佔港島太平山,香港自此淪陷,當時祖父十五歲。日軍在港期間大隊駐軍粉嶺軍地,早上會派一名翻譯員到石湖墟買菜。翻譯員跟祖父年齡相若,每天走過街市都會點點頭。有一天,日軍受到本地的反日游擊隊襲擊,死傷多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一 為我兒義行驕傲 爸爸媽媽
序二 挑戰時刻,香港人也有種責任 劉卓裕
序三 塞拉利昂的真香港人 沈旭暉
自序 兩個獅子山
章一 意義
1.1 象牙塔
1.2 我是誰
1.3 西非伊波拉大爆發
1.4 特訓
章二 考驗
2.1 國際合作
2.2 阿波圖
2.3 紅、綠、白
2.4 實驗室
2.5伊伯拉罕
2.6後遺症
2.7 Getting to Zero
圖集:那個獅子山的人、物和事
章三 延續
3.1 成功的定義
3.2 姑姐拗啲波啲
3.3 截肢營
3.4 e-Nable Sierra Leone
3.5 A Life Worth Living
3.6 天時、地利、太陽能
3.7 一封家書
章四 初衷
4.1 病毒是甚麼
4.2 最終目標
4.3 疫苗是怎...
序二 挑戰時刻,香港人也有種責任 劉卓裕
序三 塞拉利昂的真香港人 沈旭暉
自序 兩個獅子山
章一 意義
1.1 象牙塔
1.2 我是誰
1.3 西非伊波拉大爆發
1.4 特訓
章二 考驗
2.1 國際合作
2.2 阿波圖
2.3 紅、綠、白
2.4 實驗室
2.5伊伯拉罕
2.6後遺症
2.7 Getting to Zero
圖集:那個獅子山的人、物和事
章三 延續
3.1 成功的定義
3.2 姑姐拗啲波啲
3.3 截肢營
3.4 e-Nable Sierra Leone
3.5 A Life Worth Living
3.6 天時、地利、太陽能
3.7 一封家書
章四 初衷
4.1 病毒是甚麼
4.2 最終目標
4.3 疫苗是怎...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