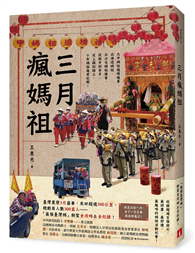胡適1891年12月17日在上海出生,祖籍安徽。在上海接受中學教育後,他負笈美國,先後入讀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前後七年。回國後,他年紀輕輕就擔任北京大學教授,1946年還出任該校校長;抗日戰爭期間關鍵的1938至1942年,他出任中國駐華盛頓大使,在推動美國介入二戰、軍事支援中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在生命中的最後四年裡,他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1911年滿清皇朝覆亡,西方嶄新和進步的思想湧入中國。胡適曾在不同的刊物當編輯,撰文介紹這些新思想,包括婚姻制度、提高婦權、文白之辯、孔儒思想、科學和民主等問題。他的一生、他的文章以及他的思想,影響、改變了無數中國人,是20世紀中國其中一位最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胡適的人生軌跡與中國近代最動盪的時期重疊,他交遊廣闊,著述豐富,又留下大量私人書信及日記,令研究胡適成為一個龐大的課題。本書深入淺出,從胡適的人生經歷、學術成就、感情生活等角度介紹他的事跡,是認識胡適全面而簡便的一冊。
作者簡介:
作者:馬克.奧尼爾(Mark O’Neill)
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1978年開始在海峽兩岸暨香港和日本等地為英國廣播公司(BBC)、路透社、《南華早報》及其他媒體工作。
馬克身兼作家、記者和大學講師多職,在北京和上海生活逾16年,現居香港。能說、寫中文(普通話和粵語)、法語和日語。著作包括:
《慈濟:慈悲濟世》
Tzu Chi: Serving with Compassion
《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
Frederick, the Life of My Missionary Grandfather in Manchuria
《參加一戰的中國勞工》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從沙皇鐵路到蘇聯紅軍》
From the Tsar’s Railway to the Red Army
《唐家王朝——改變中國的十二位香山子弟》
The Second Tang Dynasty — The 12 Sons of Fragrant Mountain Who Changed China
《兩岸故宮的世紀傳奇》
The Miraculous Story of China’s Two Palace Museums
《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
Ireland’s Imperial Mandarin: How Sir Robert Hart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er in Qing China
《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
Israel and China: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Silicon Wadi
《蔣經國的俄國妻子——蔣方良》
China''s Russian Princess: the Silent Wife of Chiang Ching-kuo
上述著作大部份兼有中文版(繁體和簡體)和英文版。
=========================
翻譯:程翰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曾從事經貿及教育文化交流工作,其後以語言教學及文字翻譯為業,長期為澳門新聞通訊社撰寫經貿新聞通訊稿。翻譯著作包括《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蔣經國的俄國妻子——蔣方良》等。
作者序
當你讀到胡適的故事,你會對中國的未來感到非常樂觀。胡適知識淵博,先後寫了共44本涉及多個主題的書,包括三本用英文寫成。胡適生於晚清末年,復得西方教育啟蒙,能駕馭中、英兩種語文,在國內外均如魚得水。若他因此驕傲自負,似屬理所當然,但他並不如此——他言談風趣、態度可親,且好廣交朋友。
1930年代,每逢星期天上午,胡適都會敞開其北京家宅的大門,歡迎各式人等進去坐坐聊聊,包括學生、路過的、來請願的,甚至要飯的。他一生的種種成就中,包括年紀輕輕就擔任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教授,1946年還出任該校的校長;抗日戰爭期間關鍵的1938至1942年出任中國駐華盛頓大使,在推動美國介入二戰、軍事支援中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在胡適生命中的最後四年裡,他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11年滿清皇朝覆亡,西方嶄新和進步的思想湧入中國。胡適曾在不同的刊物當編輯,撰文介紹這些新思想。他的一生、他的文章以及他的思想,影響、改變了無數中國人,是20世紀中國其中一位最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2021年12月17日,是胡適130歲冥壽。香港三聯與筆者決定共同出版一本他的傳記,作為對胡適的致敬。當然,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有個胡適,但對他豐富的一生能娓娓道來的,恐怕沒有幾個。在華文世界的學校課本里,胡適佔不到重要位置。除了漢學家的圈子外,沒有外國人聽過胡適。當筆者和老外朋友談到胡適時,他們的反應總是:「誰是胡適?」
多虧胡適的寫作題材寬廣、產量豐富;而華文世界的學者有關胡適之感情和學術人生的論著,題材更寬廣、產量更豐富,筆者在此對他們深表仰慕和敬意,學者們的勞動成果,是本書的主要材料來源。筆者有幸,得以拜讀這些材料,就如一個謙卑的學生般,從中得益匪淺。我們在書末鳴謝諸位「胡適學」的先行者,感謝他們細緻縝密的學術挖掘和深入洞察。
胡適1891年12月17日在上海出生,祖家是中國東部安徽省鄉郊的一個傳統家族。在上海接受中學教育後,他負笈美國,先後入讀全美國頂級大學的其中兩所——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前後共七年。這寶貴的七年,打開了胡適的眼界,讓他見識先進的工業國家如何先進,過程中慢慢塑造他的性格。他性好交友、為人樂觀、英語流利,與外國人相處和與中國人相處,一樣從容。
胡適生於那個年代,是他的福氣。他的事業生涯始於1917 年離美返國,終於1962 年離開人世,從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38年,是中國歷史上最自由開放的一個段落。知識分子有機會表達、出版他們有關政治、社會、文化、文學、宗教等的觀點,其自由開放的程度,是前後的年代都難以企及的。胡適充分利用這種自由。作為一個留美學生,他竟能就重要議題在當地發表文章,暢抒己見;而文章竟能在中國的雜誌上刊登,觸達廣大讀者。
滿清皇朝於1911 年覆亡,亞洲首個共和政體於翌年誕生。帝制的結束,引發了思想和辯論的巨變,既有激烈的爆發,也有靜默的發酵:中國應如何建設新社會、形成新政府?傳統社會中哪些元素應予保留、哪些應予揚棄?這便給意念豐富、思想躍動的胡適造就了一個理想平台。圍繞婚姻制度、提高婦權、文白之辯、孔儒思想、科學和民主等問題,人們都想一聽他的高見。
胡適也有幸,能在一個無論是工業實力還是創新泉源方面都超越了英、德兩強的國家——美國,紮實地度過了七年。在有關如何驅動經濟發展並重塑社會方面,這個國家是一部活的教科書,既有意念又有實踐。很少留美的外國學生像胡適般,懂得珍惜機會,充分善用身處彼邦的時間,滿載而歸。除學術追求外,胡適還投身認識美國社會,廣交朋友、編織人脈,無論是異國同胞抑或美利堅人。美國友人中有一個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胡適與她從初相識算起,相交相知,維持凡半個世紀,感情非比一般。
日子有功,胡適慢慢成為一位完全合格的英語演講者,事實上,他的演講邀約是如此的多,以致於1915年,他就讀碩士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撤銷了他的獎學金——他的教授們不滿他花太多時間在演講上,擠佔了他研讀哲學大師康德和黑格爾學說的時間。胡適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的了解,甚至比很多美國人還深。正是這些對當時中國人來說還遙不可及的西方教育,令胡適得以以26歲之齡,晉身北大教授的行列。
胡適再一個幸運,就是他在美國所結交的,都是教育程度高、思想開明,且善待外國學生的一類人。根據美國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輸入中國華工已被禁止。那是兩種情緒疊加的效果:種族主義,加上當地白人勞工不滿華人願為較低工資工作,飯碗被搶。但是,胡適在康大和哥大遇到的美國人教授、他們的妻子、學生等人,對胡適都很友善,甚且歡迎他加入自己的學術和社交圈子、過他們的社交生活。
不少美國華人住在紐約和三藩市唐人街的貧民窟,在面對暴力和歧視的惶恐下生活,而胡適則獲邀造訪精英階層的家宅,或與他們一道到郊外野餐,對他毫不見外;他們之中,有些成為胡適的終身摯友。這些體驗,在在令胡適對美式思維和行事大有好感。他尋思該等文化特質中,有哪些他日可帶回中國,加以弘揚。
留美七年,胡適還培養出日後讓他終生受用的個人技能和人際網絡,包括成為北美和英國的大學一位廣受歡迎的演說家,也包括為自己的國家籌措寶貴的外匯,以運營大學、修建鐵路,等等。他成為當時美國最著名的華人。此外,1941年秋,作為駐華盛頓大使的胡適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在他的影響下,美國在最後關頭拒絕與日本簽署一項協議——假使當日簽成,日本偷襲珍珠港之舉便不會發生;沒有珍珠港事件,美國就不會捲入二戰;美國不參戰,中國就不會打贏抗日戰爭。
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是引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中文的標準書寫形式。他在紐約他的寓所,一口氣把他那文學主張傾瀉紙上,然後把寫成的篇章,寄到太平洋彼岸的北京《新青年》雜誌。文章於1917年1月發表,一旦面世,其影響迅速遍及全國。不到五年,民國教育部便在為學校用的課本改用白話文作準備;報章雜誌以及向其投稿的作者們也已棄用文言文。今天一切都在變、明天一切都已變,其勢之迅猛,出乎所有人的想像。這是一場革命:它賦予數以百萬計的普通百姓前所未有的機會,去接觸書面語以及它所裝載的知識世界。
透過演說、報章和雜誌推廣白話文,只是胡適眾多追求的事業其中一項。他還推動廢除婦女纏足、主張年輕人自由選擇婚姻對象、鼓吹性別平等和節育等。他致力推動一種新的教育理念——鼓勵學生養成批判性思維的習慣,未有確證,不予盡信。
為追趕西方,中國必須學習科技;絕不能盲目相信其「精神文化」優於「物質主義」的西方。胡適在1961年一次演說中詰問:「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又說:「一位東方的詩人或哲人坐在一隻原始舢板船上,沒有理由嘲笑或藐視坐在近代噴射機在他頭上飛過的人們的物質文明。」他戲稱這種愚昧為「梅毒化」(syphilisation)——當現代文明從西方傳來,在接受它之好的同時,你無法甩掉它的壞。1500年代,葡萄牙商人為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打開利潤豐厚的歐洲新市場的同時,也把梅毒帶到中國來。
此外,胡適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他的著作涵蓋中國哲學史、白話文學史、中國佛教發展史等;他統籌一個把數十部西方經典著作翻譯成中文的浩大工程,包括《莎翁全集》。終其一生,他寫過有關中國古典小說評論的文字,超過45萬字;單是對《紅樓夢》的鑽研,也歷時逾30年。對很多人來說,他的主要缺點是興趣太廣、對太多課題都感興趣,以致就單一課題的成就而言,他難以企及專攻該課題的學者;他很享受與友儕相處,把不少光陰都花費其中,故有人稱胡適為「半部博士」——他發表了一部著作的上半部,讓人期待下半部,但那下半部卻始終不見影蹤。
胡適的私人生活也同樣精彩。這個語文現代化的大旗手、自由戀愛的鼓吹者,偏偏最終根據盲婚啞嫁的老俗,娶了來自安徽鄰村的一位女子為妻。定親之時,胡適才不過12歲,與自由戀愛、自主婚姻相距十萬八千里。一雙未來新人幾乎沒有任何共通之處,以致胡適曾有一次嘗試擺脫婚約,但妻子的激烈反應,讓他打消了念頭,並從此不再提「離婚」二字。胡適一生中,與三位女士維持著長久的關係,她們一位中國人、兩位美國人。假使他晚出生20年,與他結為夫妻的,或將是她仨其中之一,而不是那位安徽姑娘。
三位紅顏知己當中,胡適與韋蓮司的一段情誼最刻骨銘心。胡適於康大求學期間(1910~1915)與韋蓮司初遇,自此以後的50年,兩人信來信往達300封。我們今天之所以能讀到這批信,全賴韋蓮司於胡適死後,把胡適寫給她的信全數贈予位於台北的胡適紀念館,至於她寫給胡適的信,則由周質平教授於1997年在北大圖書館發現。在與陳毓賢的共同努力下,周教授分別以中英文,寫了一本關於胡韋二人浪漫故事的書,扣人心弦。
因著胡適的魅力、知識和迷人的個性,他的朋友圈子很寬,包括蔣介石、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夫婦和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等。台灣知名作家李敖形容胡適為一位對政治和社會均有巨大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若胡適的生平能像啟發筆者般啟發其他人,那就不枉筆者寫這本書了。
當你讀到胡適的故事,你會對中國的未來感到非常樂觀。胡適知識淵博,先後寫了共44本涉及多個主題的書,包括三本用英文寫成。胡適生於晚清末年,復得西方教育啟蒙,能駕馭中、英兩種語文,在國內外均如魚得水。若他因此驕傲自負,似屬理所當然,但他並不如此——他言談風趣、態度可親,且好廣交朋友。
1930年代,每逢星期天上午,胡適都會敞開其北京家宅的大門,歡迎各式人等進去坐坐聊聊,包括學生、路過的、來請願的,甚至要飯的。他一生的種種成就中,包括年紀輕輕就擔任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教授,1946年還出任該校的校長;抗日戰爭期間...
目錄
第一章 從安徽農村到常春藤大學
第二章 康乃爾大學:新世界的啟蒙
第三章 哥倫比亞大學:遇上人生導師和心靈伴侣
第四章 改造中國
第五章 1920年代:政治紛亂,但碩果纍纍
第六章 「一旦世界大戰爆發,中日兩國均將滅亡」
第七章 拯救中國
第八章 1946 ~ 1949:絕望與自我流放
第九章 自我流放及帶領中央研究院
第十章 文化遺產:白話走進書面語
第一章 從安徽農村到常春藤大學
第二章 康乃爾大學:新世界的啟蒙
第三章 哥倫比亞大學:遇上人生導師和心靈伴侣
第四章 改造中國
第五章 1920年代:政治紛亂,但碩果纍纍
第六章 「一旦世界大戰爆發,中日兩國均將滅亡」
第七章 拯救中國
第八章 1946 ~ 1949:絕望與自我流放
第九章 自我流放及帶領中央研究院
第十章 文化遺產:白話走進書面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