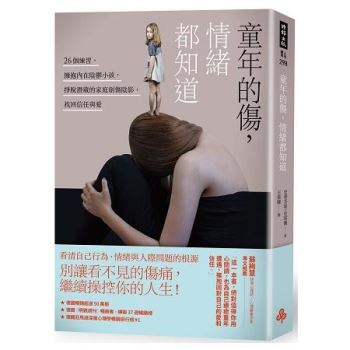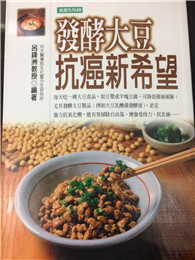對於從一九八○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學人來說,劉再復無疑是那個時代的標誌性人物,是一代學子的精神偶像。
《文學赤子——劉再復先生八秩壽慶文集》共收有七十篇文字,由再復老師的好友、同事、門生執筆,全書粗分八輯,即“海底自行”、 “放逐諸神”、“海內知己”、“文學先生”、“漂流歲月”、“心靈本體”、“文心空間”、“多維對話”,其中既有好友所作的序言,也有與友人的對談;既有國內老友的懷想,也有漂泊歲月的深情厚誼;既有滿懷深情的回憶性散文隨筆,也有對其學術思想的理解與闡釋,還有以學術論文形式呈現的祝壽之忱。
我們相信再復老師為文學而生的赤誠、自由的慈悲之心,會不斷感動和激勵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們,他們才是未來的希望。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文學赤子:劉再復先生八秩壽慶文集的圖書 |
| |
文學赤子:劉再復先生八秩壽慶文集 出版日期:2021-11-09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027 |
Books |
$ 1170 |
中文書 |
$ 1170 |
華文文學研究 |
$ 1170 |
華文文學研究 |
$ 1170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11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文學赤子:劉再復先生八秩壽慶文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主編簡介
王德威
哈佛大學東亞系EdwardC.Henderson講座教授。著有《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二十家》、《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後遺民寫作》、《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等中英文著作數十種。
季進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錢鍾書與現代西學》、《陳銓:異邦的借鏡》、《另一種聲音》、《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綜論》等。編注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五卷本)。主編有“西方現代批評經典譯叢”、“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叢書”等。
劉劍梅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出版過中英文專著《莊子與中國現代文學》、《革命加戀愛:文學史、女性身體和主題重複》、《莊子的現代命運》、《革命與情愛》、《徬徨的娜拉》、《狂歡的女神》、《共悟紅樓》(與劉再復合著)、《共悟人間》(與劉再復合著)。另有中英文文章數十篇,發表於各種報刊。
王德威
哈佛大學東亞系EdwardC.Henderson講座教授。著有《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二十家》、《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後遺民寫作》、《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等中英文著作數十種。
季進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錢鍾書與現代西學》、《陳銓:異邦的借鏡》、《另一種聲音》、《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綜論》等。編注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五卷本)。主編有“西方現代批評經典譯叢”、“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叢書”等。
劉劍梅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出版過中英文專著《莊子與中國現代文學》、《革命加戀愛:文學史、女性身體和主題重複》、《莊子的現代命運》、《革命與情愛》、《徬徨的娜拉》、《狂歡的女神》、《共悟紅樓》(與劉再復合著)、《共悟人間》(與劉再復合著)。另有中英文文章數十篇,發表於各種報刊。
目錄
序言:心靈的孤本 劉劍梅 001
輯一 海底自行
漂流與逍遙——《西尋故鄉》序 余英時 017
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思想者十八題》序 余英時 023
劉再復的心靈自傳——《漂流手記》序 李歐梵 030
自立於紅學之林——《紅樓夢悟》英文版的序 高行健 032
“山頂獨立,海底自行”——《五史自傳》序 王德威 034
輯二 放逐諸神
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沉浮——劉再復、李澤厚對談 劉再復 李澤厚 047
放下政治話語——巴黎十日談 劉再復 高行健 055
輕重位置與敘事藝術——劉再復、李歐梵對談 劉再復 李歐梵 075
說不盡的《紅樓夢》——劉再復、白先勇對談 劉再復 白先勇 089
輯三 海內知己
不竭的思想者——劉再復八十華誕之賀 謝冕 105
壽再復八十 董乃斌 108
輾轉寄給再復先生的兩首詩 劉登翰 117
再復,也是一個“半農” 程麻 121
科羅拉多的晚霞——洛基山下劉再復 張夢陽 129
終老難忘知遇恩——獻給再復摯友八十壽辰 林興宅 145
輯四 文學先生
先生文學,文學先生 丁帆 155
引領寫作向上向善的人 閻連科 160
您的名字叫文學 林丹婭 166
永遠的編輯和作者——劉再復先生與我 李昕 172
劉再復在一九八○年代 ——有關我的私人記憶 魯樞元 179
文學的守護人——劉再復印象 林崗 193
再復先生和一九八○年代的校園文化 黃心村 201
恭賀劉再復先生八十大壽 李輝 206
赤子之心——劉再復先生印象 梁鴻 213
關於《劉再復評傳》寫作及與再復先生交往二三事 古大勇 217
親炙劉再復先生的教誨 莊園 223
輯五 漂流歲月
劉再復的赤腳蘭花 董橋 231
漂泊的真誠 鄭培凱 233
我的朋友劉再復 羅多弼 237
童稚之心和悲憫之情──我印象中的劉老師 宋永毅 243
劉再復印象記 盧新華 247
永遠年輕的劉再復老師 孔海立 252
本真和自在——我所認識的劉再復先生 賈晉華 256
回憶華盛頓郊外的一個寧靜的秋日午後——也談劉再復先生與韓國的緣分 朴宰雨 260
與再復先生為鄰的日子 王瑋 269
洛基山下的白雪和綠草 陳偉強 275
輯六 心靈本體
人生的感悟 思想的結晶——劉再復先生的“人生悟語”或“碎片寫作” 萬之 283
“伴我遠遊的早晨” 黃子平 287
劉再復論魯迅的悲劇美學 王斑 291
精神的分野 張煒 299
一個人和一個文學時代——八十年代的劉再復小記 白燁 303
捧著一顆心——讀劉再復“漂流手記”系列 蘇煒 308
劉再復的“悟法”批評話語——文學批評和文化思想研究的一種範例 李以建 324
劉再復文學心靈本體論概要 何靜恆 張靜河 337
“新文體寫作”的意義 劉劍梅 345
時代罅隙之間,一個“講台上的教授”——莊園《劉再復年譜》序 朱壽桐 350
文學與懺悔 涂航 356
“超越”啟蒙——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三論” 喬敏 362
輯七 文心空間
清代女性詩詞中的行旅書寫 張宏生 373
歲寒濡呴慰勞生——庚子詩詞中的滄桑書寫與家國之喻 吳盛青 380
文學觀念與話語的解放——略論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學理論與批評 陳曉明 387
反思中國改革開放後文化威權與主體性建構的技術 陳綾琪 著 胡疆峰 譯 396
女性華文作家中的跨國性愛和主體性構建 魯曉鵬 404
“五四新文學”,到底“新”在哪裡?——重讀魯迅的三篇小說(節選) 許子東 411
邊界、越界和邊界書寫——冷戰與華語文學 王曉玨 419
回到未來——五四與科幻 宋明煒 428
跨文化語境下的“革命文學”概念 馬筱璐 434
輯八 多維對話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 陳平原 443
香港電影的中心離位動態 張英進 451
演繹“紅色經典”:三大革命音樂舞蹈史詩及其和平回歸 陳小眉 著 馮雪峰 譯 459
現代漢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模式初探 奚密 469
反行衝動——論黃翔詩歌中的聲音,口頭性與肉身性 米家路 486
先鋒與國歌 羅靚 504
疾病與話語 蔡元豐 著 陳文浩 譯 513
傳染與傳播——張貴興《群象》的免疫學讀本 羅鵬 著 張文顯 譯 519
文學.江湖.俠蹤 宋偉傑 533
“失”的寓言——遲子建《煙火漫捲》剖析 張恩華 541
荒誕、神實、救贖——讀閻連科的《日熄》 陳穎 549
歷史背面的斷憶――悼念賈植芳先生 陳建華 556
打撈歷史的碎片——誰是錢學熙? 季進 562
編後記 季進 577
附錄:劉再復著作出版年表 葉鴻基 整理 579
輯一 海底自行
漂流與逍遙——《西尋故鄉》序 余英時 017
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思想者十八題》序 余英時 023
劉再復的心靈自傳——《漂流手記》序 李歐梵 030
自立於紅學之林——《紅樓夢悟》英文版的序 高行健 032
“山頂獨立,海底自行”——《五史自傳》序 王德威 034
輯二 放逐諸神
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沉浮——劉再復、李澤厚對談 劉再復 李澤厚 047
放下政治話語——巴黎十日談 劉再復 高行健 055
輕重位置與敘事藝術——劉再復、李歐梵對談 劉再復 李歐梵 075
說不盡的《紅樓夢》——劉再復、白先勇對談 劉再復 白先勇 089
輯三 海內知己
不竭的思想者——劉再復八十華誕之賀 謝冕 105
壽再復八十 董乃斌 108
輾轉寄給再復先生的兩首詩 劉登翰 117
再復,也是一個“半農” 程麻 121
科羅拉多的晚霞——洛基山下劉再復 張夢陽 129
終老難忘知遇恩——獻給再復摯友八十壽辰 林興宅 145
輯四 文學先生
先生文學,文學先生 丁帆 155
引領寫作向上向善的人 閻連科 160
您的名字叫文學 林丹婭 166
永遠的編輯和作者——劉再復先生與我 李昕 172
劉再復在一九八○年代 ——有關我的私人記憶 魯樞元 179
文學的守護人——劉再復印象 林崗 193
再復先生和一九八○年代的校園文化 黃心村 201
恭賀劉再復先生八十大壽 李輝 206
赤子之心——劉再復先生印象 梁鴻 213
關於《劉再復評傳》寫作及與再復先生交往二三事 古大勇 217
親炙劉再復先生的教誨 莊園 223
輯五 漂流歲月
劉再復的赤腳蘭花 董橋 231
漂泊的真誠 鄭培凱 233
我的朋友劉再復 羅多弼 237
童稚之心和悲憫之情──我印象中的劉老師 宋永毅 243
劉再復印象記 盧新華 247
永遠年輕的劉再復老師 孔海立 252
本真和自在——我所認識的劉再復先生 賈晉華 256
回憶華盛頓郊外的一個寧靜的秋日午後——也談劉再復先生與韓國的緣分 朴宰雨 260
與再復先生為鄰的日子 王瑋 269
洛基山下的白雪和綠草 陳偉強 275
輯六 心靈本體
人生的感悟 思想的結晶——劉再復先生的“人生悟語”或“碎片寫作” 萬之 283
“伴我遠遊的早晨” 黃子平 287
劉再復論魯迅的悲劇美學 王斑 291
精神的分野 張煒 299
一個人和一個文學時代——八十年代的劉再復小記 白燁 303
捧著一顆心——讀劉再復“漂流手記”系列 蘇煒 308
劉再復的“悟法”批評話語——文學批評和文化思想研究的一種範例 李以建 324
劉再復文學心靈本體論概要 何靜恆 張靜河 337
“新文體寫作”的意義 劉劍梅 345
時代罅隙之間,一個“講台上的教授”——莊園《劉再復年譜》序 朱壽桐 350
文學與懺悔 涂航 356
“超越”啟蒙——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三論” 喬敏 362
輯七 文心空間
清代女性詩詞中的行旅書寫 張宏生 373
歲寒濡呴慰勞生——庚子詩詞中的滄桑書寫與家國之喻 吳盛青 380
文學觀念與話語的解放——略論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學理論與批評 陳曉明 387
反思中國改革開放後文化威權與主體性建構的技術 陳綾琪 著 胡疆峰 譯 396
女性華文作家中的跨國性愛和主體性構建 魯曉鵬 404
“五四新文學”,到底“新”在哪裡?——重讀魯迅的三篇小說(節選) 許子東 411
邊界、越界和邊界書寫——冷戰與華語文學 王曉玨 419
回到未來——五四與科幻 宋明煒 428
跨文化語境下的“革命文學”概念 馬筱璐 434
輯八 多維對話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 陳平原 443
香港電影的中心離位動態 張英進 451
演繹“紅色經典”:三大革命音樂舞蹈史詩及其和平回歸 陳小眉 著 馮雪峰 譯 459
現代漢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模式初探 奚密 469
反行衝動——論黃翔詩歌中的聲音,口頭性與肉身性 米家路 486
先鋒與國歌 羅靚 504
疾病與話語 蔡元豐 著 陳文浩 譯 513
傳染與傳播——張貴興《群象》的免疫學讀本 羅鵬 著 張文顯 譯 519
文學.江湖.俠蹤 宋偉傑 533
“失”的寓言——遲子建《煙火漫捲》剖析 張恩華 541
荒誕、神實、救贖——讀閻連科的《日熄》 陳穎 549
歷史背面的斷憶――悼念賈植芳先生 陳建華 556
打撈歷史的碎片——誰是錢學熙? 季進 562
編後記 季進 577
附錄:劉再復著作出版年表 葉鴻基 整理 579
序
序言
心靈的孤本
劉劍梅
這本《文學赤子——劉再復先生八秩壽慶文集》由王德威老師、季進和我聯合主編,承蒙海內外文壇諸位學者、文人、朋友的傾情支持,以及富有人文情懷的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周建華先生的鼎力幫助,得以在我父親八十歲生日之前出版,作為中外學人共同送給他的生日禮物。在此,我真誠地感謝每一位為文集撰稿的作者,您們的文字讓我深深感動,也讓我堅信,文壇不僅需要豐富、深邃的知識和學問,而且需要質樸、溫馨的“赤子之心”。在編輯文集的過程中,季進出力最多,但是因為我身兼學者和女兒的“雙重身份”,所以王德威老師和季進決定由我來為文集寫序。
我父親把一九八九年(四十八歲)之前的人生,視為第一人生,把這之後到海外的人生視為第二人生。在《漂流手記》的《瞬間》一文中,他寫道,在人的生命的某一瞬間的選擇,會使人的“生命意義和生命形式發生巨大的變動”:“也許,就在這一瞬間,你的靈魂已經跪下,成為魔鬼的俘虜和合作者;也許就在這一瞬間,你的靈魂往另一方向飛升,穿越了龐大的痛苦與黑暗,甚至穿越了殘酷的死亡,實現了靈與肉的再生。這一剎那,就是偶然,就是命運。”他的第二人生就是在那一剎那做的選擇,而為了這一服從自己良心的選擇,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背井離鄉,忍受寂寞和孤獨,在海外漂泊了三十二年。
記得錢鍾書先生曾經託朋友帶給我父親八個字:“令為暴臣,不為逋客。”雖然我父親一直非常敬重錢鍾書先生,但是他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回國,原因是“暴臣”難當。他曾經寫道:“一有自由心態,就不規矩不馴服,該說的話就說,不該說的話就不說,這就難免要觸‘暴’並為‘暴’所不容。如果沒有自由心態,當暴臣倒是不難而且很舒服,除了可以吃飽喝足之外,還可以有名有利有地位,甚至可以‘無災無禍到公卿’。”當時聽到這八個字,同樣選擇當“逋客”的李澤厚先生馬上回了八個字:“寧為雞口,不為牛後。”我父親聽了非常高興,他更願意做報曉的“雞口”,自由啼唱,自由表述,保持一個人的全部尊嚴,“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其實父親當時選擇出國之前,從廣東給我打過一個電話。他跟我母親擔心還在北京的奶奶、妹妹和我,我馬上回答:“你們不用擔心,走得越遠越好。”這麼多年過去了,我有時會想,如果父親當時選擇留在中國,會不會過得更舒適一些,更富裕一些,不用總是四處奔波,不用在異國他鄉那麼孤獨地生活。不過,讀了他後半生的文字,我就明白,他的選擇是對的,因為那些文字就是他獲得生命的大解脫大自在的見證。就像他說的,“我已還原為我自己,我的生命內核,將從此只放射個人真實而自由的聲音。”於是,他的聲音和文字清澈而純粹,真實而赤誠,強大而勇敢,伴隨著靈魂的鼓點,在空寂中再造自己的家園,屬於獨一無二的“心靈的孤本,生命的原版,和天涯的獨語”。
與生命相銜接的學問
作為學人,我父親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學術要跟生命相銜接”。他喜歡能夠激發靈魂活力的書籍,欣賞不只是靠頭腦生活、還靠心靈和生命整體生活的思想家。他說在中國,“知識者往往徘徊於皇統、道統與學統之間,或崇道統而輕學統,而崇學統與輕道統,而愛默生則看到有一個高於道統也高於學統的東西,這就是形成‘有活力的靈魂’的生命脈統。這種脈統可以照亮道統也可以照亮學統。一個沉醉於學統的學人是可敬的,但是,如果他入乎其中而不能超乎其外,即不能用生命血脈去穿透書籍,這種學統也是可疑的。”在跟我合著的《共悟人間》中,他反覆囑咐我不要陷入“語狂”和“語障”的陷阱,不要被各種概念、妄念所隔,不能讓概念和理論遮蔽真問題、真生命。他批評那種空有學術外殼而沒有太多思想和生命的赤誠的人,讓我千萬不要變成“滿身冷氣和酸氣”的學者。他寫道:
我們也看到學術史上一些星辰般的光束,這除了歷史上人們公認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孟德斯鳩、盧梭等之外,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中,我們看到的一些學者,如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中的馬爾庫塞、阿多諾、哈貝馬斯等,也很了不起的。他們的特點是把生命與學術相銜接,把思想與時代相銜接,始終面對生命困境並從中發現問題,始終不放棄一個知識分子最高貴的品性——敢於對權勢說真話和提出坦率的叩問。他們所有的“大哉問”都積滿膽汁、心汁或其他生命的液汁,其問號是殷紅的,絕不是灰白的。如果你能向他們學習,找到一個生命與學問的連結點,就能找到一條自己的精神價值創造之路。
我父親自己的學術路程,就是一個從知識走向生命的過程,是“學術與生命相銜接”的典型範例。用林崗的話來說,“與其說劉再復是一個專家型的學者,不如說他是一個思想型的學者。”在父親的第一人生中,他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具有鮮明的歷史和現實的針對性,極力反對把“主義”、概念、理論提高到“絕對精神”的高度,主張回到人的尊嚴。他的學術生涯是從研究魯迅開始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出版了《魯迅與自然科學》、《魯迅美學論稿》、《魯迅傳》。因為那個年代,國內思想剛剛解凍,所以他展現了一些思想的鋒芒,破除魯迅的偶像化,敢於把魯迅從“神壇”上拉下來,重新恢復他的 “人性”。自一九八五年之後,父親發表了《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出版了《性格組合論》,並提出了著名的“文學主體性”理論,還與林崗合著《傳統與中國人》。他這一期間的思想學術,被夏中義先生概述為“劉氏三論”:性格組合論、文學主體論、國魂反省論。父親的“三論”寫於八十年代的中後期,在思想上有了一個“飛躍”,不僅有主體意識,有超越和反思意識,還有尖銳的現實批判性,與當時的語境積極展開對話,針對當時僵化的文學理論做出大膽的批評,把文學引回人性,不再做政治的附庸和傳聲筒。他試圖走出當時流行的蘇聯的理論模式,用“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去解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用“主體論”去解構“典型論”和“反映論”,用“藝術主體”的個性去超越“現實主體”的黨派性,並且延續了五四的啟蒙精神和魯迅的批判國民性的精神。在《性格組合論》自序中,他寫道:“我們身外是這麼一個神秘的浩茫無際的宇宙,而我們身內不也有一個難以認識窮盡的、充滿著血的蒸氣的第二宇宙嗎?”他發現,在人的性格世界——“內宇宙”中,充滿複雜的悖論和相對性,是一個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相互轉換的豐富的存在,於是,他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說明人的性格應該是“善惡並舉”的動態鮮活的生命景觀。他的“文學主體論”,講述創作主體的超越性,把現實政治和文學創作分開,認為每一位作家都有雙重主體身份:一種是世俗角色即現實主體,另一種是本真角色即藝術主體。文學主體性充分肯定創作主體的本真屬性,擺脫黨派性和世俗性,對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念提出挑戰和質疑,並影響了之後的文藝批評理論和創作的探索。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強調作家必須“擁抱”現實,而父親的“文學主體論”強調作家必須“超越”現實。可以說,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父親扮演了“啟蒙者”和“弄潮兒”的角
色。他的“三論”之所以流傳很廣,就是因為他針對當時的語境,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少真問題,而且不懼政治壓力,顯示了一位知識分子的勇氣和風骨。
到了海外之後,他繼續深化自己的學術研究,出版了《告別革命》(與李澤厚合著)、《放逐諸神》、《罪與文學》(與林崗合著)、《現代文學諸子論》、《高行健論》、《李澤厚美學概論》等書,逐漸從性格探究走向靈魂探索,不再把文學看成啟蒙和救亡工具,而是恢復文學的初衷。首先,他向“第一人生”做了鄭重的告別。他和李澤厚先生在《告別革命》中,反省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思路——包括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有理論、歷史決定論、辯證唯物論、政治倫理宗教三位一體論、兩項對立的思路、意識形態崇拜的思路,以“二律背反”為他們的方法論、歷史觀和認識論,主張以經濟為本、改良漸進、階級協調、社會協調、對話論理、多元共存、和諧競爭、重新確定人的價值等等。雖然這本書不是學術專著,但是因為他們提出的問題與中國政治、文化、歷史、文學的大思路和大走向息息相關,所以在海外知識界的影響非常大,一版再版。然而,由於題目過於敏感,國內讀者難以看到。《放逐諸神》則是父親第二人生的一個里程碑,是他對以往的思想牢籠進行的一次告別儀式,不僅放逐“革命”、“國家”、“二極思維”、“概念”,而且放逐尼采式的膨脹的“自我”。他從宏觀的角度,對“重寫文學史”提出多角度的思考,反思國內以往以反映論為基點的文學理論系統,同時與國外流行的現代和後現代“主義”和概念也保持距離。他所要放逐的“諸神”中,同樣包括那些與中國文學作品的語境非常“隔”的西方理論。
告別“第一人生”的種種禁錮思維的模式之後,父親的寫作越來越往心靈和靈魂的方向轉變和靠攏。林崗曾經用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話來描述父親在海外時期的學術著作:“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他認為,第二人生讓我父親獲得了心靈的大自由,衝破“俗諦之桎梏”,去掉頭頂上的種種光環,如“所長”、“主編”、“盟主”等頭銜,而只剩下“客座教授”,領悟到自己在人生走一回,不過是“過客”而已——“夢裡已知身是客”,然而,“在‘俗諦’離他越來越遠的時候,真理卻離他越來越近。” 剛到海外的時候,父親出版過《人論二十五種》,對人性諸相進行了深刻的探討,如“肉人”、“畜人”、“酸人”、“忍人”、“癡人”、“傀儡人”、“套中人”、“分裂人”、“兩棲人”等。這些人性諸相,不僅代表中國的國民性,而且還具有普世的人性特徵。不過,他很快就把視角轉向靈魂。在與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中,他們叩問中國文學傳統所缺乏的宗教維度和懺悔意識,從靈魂視角進行中西方文學的宏觀性比較。他們認為,中國文學缺乏的正是“內心的靈魂呼告的聲音”,只重視外在的社會、政治、國家的維度,而不重視主體本身靈魂的對話和掙扎。“具有深度的罪感文學,不是對法律責任的體認,而是對良知責任的體認,即對無罪之罪與共同犯罪的體認,懺悔意識也正是對無罪之罪與共同犯罪的意識。” 歐洲自二戰後,出現了蔚為大觀的跟“懺悔意識”有關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和思想史論述,而在中國語境中觸及到這一問題的文論卻寥寥無幾,因此《罪與文學》有深遠的意義。
如果父親第一人生的理論和主張充滿了“救世”情結,那麼他的第二人生則著眼於“自救”。他所寫的文字是他在荒野隙縫中,為自己開闢的一片心靈的園地,來自於他內心真正的需求,不再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而是跨越古今中外,思考更為普遍和永恆的跟生命有關的命題。他曾說:“在宇宙的大明麗與大潔淨面前,方知生命語境大於歷史語境。” 《高行健論》是父親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對“文學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延續性思索。他注意到《靈山》中的“你”、“我”、“他”三人稱,正是內在主體的三坐標,構成了複雜的內在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另外,在第一人生中,他認同魯迅,傾向於做一位“精神界戰士”,一位能夠“攖人心”的摩羅詩人,一位積極擁抱社會、改變社會的知識分子,然而,在第二人生中,他更認同高行健,傾向於做一位超越潮流的冷觀者,用第三隻眼睛,審視世界和反觀自我的複雜性。
心靈的孤本
劉劍梅
這本《文學赤子——劉再復先生八秩壽慶文集》由王德威老師、季進和我聯合主編,承蒙海內外文壇諸位學者、文人、朋友的傾情支持,以及富有人文情懷的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周建華先生的鼎力幫助,得以在我父親八十歲生日之前出版,作為中外學人共同送給他的生日禮物。在此,我真誠地感謝每一位為文集撰稿的作者,您們的文字讓我深深感動,也讓我堅信,文壇不僅需要豐富、深邃的知識和學問,而且需要質樸、溫馨的“赤子之心”。在編輯文集的過程中,季進出力最多,但是因為我身兼學者和女兒的“雙重身份”,所以王德威老師和季進決定由我來為文集寫序。
我父親把一九八九年(四十八歲)之前的人生,視為第一人生,把這之後到海外的人生視為第二人生。在《漂流手記》的《瞬間》一文中,他寫道,在人的生命的某一瞬間的選擇,會使人的“生命意義和生命形式發生巨大的變動”:“也許,就在這一瞬間,你的靈魂已經跪下,成為魔鬼的俘虜和合作者;也許就在這一瞬間,你的靈魂往另一方向飛升,穿越了龐大的痛苦與黑暗,甚至穿越了殘酷的死亡,實現了靈與肉的再生。這一剎那,就是偶然,就是命運。”他的第二人生就是在那一剎那做的選擇,而為了這一服從自己良心的選擇,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背井離鄉,忍受寂寞和孤獨,在海外漂泊了三十二年。
記得錢鍾書先生曾經託朋友帶給我父親八個字:“令為暴臣,不為逋客。”雖然我父親一直非常敬重錢鍾書先生,但是他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回國,原因是“暴臣”難當。他曾經寫道:“一有自由心態,就不規矩不馴服,該說的話就說,不該說的話就不說,這就難免要觸‘暴’並為‘暴’所不容。如果沒有自由心態,當暴臣倒是不難而且很舒服,除了可以吃飽喝足之外,還可以有名有利有地位,甚至可以‘無災無禍到公卿’。”當時聽到這八個字,同樣選擇當“逋客”的李澤厚先生馬上回了八個字:“寧為雞口,不為牛後。”我父親聽了非常高興,他更願意做報曉的“雞口”,自由啼唱,自由表述,保持一個人的全部尊嚴,“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其實父親當時選擇出國之前,從廣東給我打過一個電話。他跟我母親擔心還在北京的奶奶、妹妹和我,我馬上回答:“你們不用擔心,走得越遠越好。”這麼多年過去了,我有時會想,如果父親當時選擇留在中國,會不會過得更舒適一些,更富裕一些,不用總是四處奔波,不用在異國他鄉那麼孤獨地生活。不過,讀了他後半生的文字,我就明白,他的選擇是對的,因為那些文字就是他獲得生命的大解脫大自在的見證。就像他說的,“我已還原為我自己,我的生命內核,將從此只放射個人真實而自由的聲音。”於是,他的聲音和文字清澈而純粹,真實而赤誠,強大而勇敢,伴隨著靈魂的鼓點,在空寂中再造自己的家園,屬於獨一無二的“心靈的孤本,生命的原版,和天涯的獨語”。
與生命相銜接的學問
作為學人,我父親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學術要跟生命相銜接”。他喜歡能夠激發靈魂活力的書籍,欣賞不只是靠頭腦生活、還靠心靈和生命整體生活的思想家。他說在中國,“知識者往往徘徊於皇統、道統與學統之間,或崇道統而輕學統,而崇學統與輕道統,而愛默生則看到有一個高於道統也高於學統的東西,這就是形成‘有活力的靈魂’的生命脈統。這種脈統可以照亮道統也可以照亮學統。一個沉醉於學統的學人是可敬的,但是,如果他入乎其中而不能超乎其外,即不能用生命血脈去穿透書籍,這種學統也是可疑的。”在跟我合著的《共悟人間》中,他反覆囑咐我不要陷入“語狂”和“語障”的陷阱,不要被各種概念、妄念所隔,不能讓概念和理論遮蔽真問題、真生命。他批評那種空有學術外殼而沒有太多思想和生命的赤誠的人,讓我千萬不要變成“滿身冷氣和酸氣”的學者。他寫道:
我們也看到學術史上一些星辰般的光束,這除了歷史上人們公認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孟德斯鳩、盧梭等之外,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中,我們看到的一些學者,如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中的馬爾庫塞、阿多諾、哈貝馬斯等,也很了不起的。他們的特點是把生命與學術相銜接,把思想與時代相銜接,始終面對生命困境並從中發現問題,始終不放棄一個知識分子最高貴的品性——敢於對權勢說真話和提出坦率的叩問。他們所有的“大哉問”都積滿膽汁、心汁或其他生命的液汁,其問號是殷紅的,絕不是灰白的。如果你能向他們學習,找到一個生命與學問的連結點,就能找到一條自己的精神價值創造之路。
我父親自己的學術路程,就是一個從知識走向生命的過程,是“學術與生命相銜接”的典型範例。用林崗的話來說,“與其說劉再復是一個專家型的學者,不如說他是一個思想型的學者。”在父親的第一人生中,他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具有鮮明的歷史和現實的針對性,極力反對把“主義”、概念、理論提高到“絕對精神”的高度,主張回到人的尊嚴。他的學術生涯是從研究魯迅開始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出版了《魯迅與自然科學》、《魯迅美學論稿》、《魯迅傳》。因為那個年代,國內思想剛剛解凍,所以他展現了一些思想的鋒芒,破除魯迅的偶像化,敢於把魯迅從“神壇”上拉下來,重新恢復他的 “人性”。自一九八五年之後,父親發表了《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出版了《性格組合論》,並提出了著名的“文學主體性”理論,還與林崗合著《傳統與中國人》。他這一期間的思想學術,被夏中義先生概述為“劉氏三論”:性格組合論、文學主體論、國魂反省論。父親的“三論”寫於八十年代的中後期,在思想上有了一個“飛躍”,不僅有主體意識,有超越和反思意識,還有尖銳的現實批判性,與當時的語境積極展開對話,針對當時僵化的文學理論做出大膽的批評,把文學引回人性,不再做政治的附庸和傳聲筒。他試圖走出當時流行的蘇聯的理論模式,用“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去解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用“主體論”去解構“典型論”和“反映論”,用“藝術主體”的個性去超越“現實主體”的黨派性,並且延續了五四的啟蒙精神和魯迅的批判國民性的精神。在《性格組合論》自序中,他寫道:“我們身外是這麼一個神秘的浩茫無際的宇宙,而我們身內不也有一個難以認識窮盡的、充滿著血的蒸氣的第二宇宙嗎?”他發現,在人的性格世界——“內宇宙”中,充滿複雜的悖論和相對性,是一個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相互轉換的豐富的存在,於是,他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說明人的性格應該是“善惡並舉”的動態鮮活的生命景觀。他的“文學主體論”,講述創作主體的超越性,把現實政治和文學創作分開,認為每一位作家都有雙重主體身份:一種是世俗角色即現實主體,另一種是本真角色即藝術主體。文學主體性充分肯定創作主體的本真屬性,擺脫黨派性和世俗性,對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念提出挑戰和質疑,並影響了之後的文藝批評理論和創作的探索。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強調作家必須“擁抱”現實,而父親的“文學主體論”強調作家必須“超越”現實。可以說,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父親扮演了“啟蒙者”和“弄潮兒”的角
色。他的“三論”之所以流傳很廣,就是因為他針對當時的語境,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少真問題,而且不懼政治壓力,顯示了一位知識分子的勇氣和風骨。
到了海外之後,他繼續深化自己的學術研究,出版了《告別革命》(與李澤厚合著)、《放逐諸神》、《罪與文學》(與林崗合著)、《現代文學諸子論》、《高行健論》、《李澤厚美學概論》等書,逐漸從性格探究走向靈魂探索,不再把文學看成啟蒙和救亡工具,而是恢復文學的初衷。首先,他向“第一人生”做了鄭重的告別。他和李澤厚先生在《告別革命》中,反省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思路——包括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有理論、歷史決定論、辯證唯物論、政治倫理宗教三位一體論、兩項對立的思路、意識形態崇拜的思路,以“二律背反”為他們的方法論、歷史觀和認識論,主張以經濟為本、改良漸進、階級協調、社會協調、對話論理、多元共存、和諧競爭、重新確定人的價值等等。雖然這本書不是學術專著,但是因為他們提出的問題與中國政治、文化、歷史、文學的大思路和大走向息息相關,所以在海外知識界的影響非常大,一版再版。然而,由於題目過於敏感,國內讀者難以看到。《放逐諸神》則是父親第二人生的一個里程碑,是他對以往的思想牢籠進行的一次告別儀式,不僅放逐“革命”、“國家”、“二極思維”、“概念”,而且放逐尼采式的膨脹的“自我”。他從宏觀的角度,對“重寫文學史”提出多角度的思考,反思國內以往以反映論為基點的文學理論系統,同時與國外流行的現代和後現代“主義”和概念也保持距離。他所要放逐的“諸神”中,同樣包括那些與中國文學作品的語境非常“隔”的西方理論。
告別“第一人生”的種種禁錮思維的模式之後,父親的寫作越來越往心靈和靈魂的方向轉變和靠攏。林崗曾經用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話來描述父親在海外時期的學術著作:“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他認為,第二人生讓我父親獲得了心靈的大自由,衝破“俗諦之桎梏”,去掉頭頂上的種種光環,如“所長”、“主編”、“盟主”等頭銜,而只剩下“客座教授”,領悟到自己在人生走一回,不過是“過客”而已——“夢裡已知身是客”,然而,“在‘俗諦’離他越來越遠的時候,真理卻離他越來越近。” 剛到海外的時候,父親出版過《人論二十五種》,對人性諸相進行了深刻的探討,如“肉人”、“畜人”、“酸人”、“忍人”、“癡人”、“傀儡人”、“套中人”、“分裂人”、“兩棲人”等。這些人性諸相,不僅代表中國的國民性,而且還具有普世的人性特徵。不過,他很快就把視角轉向靈魂。在與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中,他們叩問中國文學傳統所缺乏的宗教維度和懺悔意識,從靈魂視角進行中西方文學的宏觀性比較。他們認為,中國文學缺乏的正是“內心的靈魂呼告的聲音”,只重視外在的社會、政治、國家的維度,而不重視主體本身靈魂的對話和掙扎。“具有深度的罪感文學,不是對法律責任的體認,而是對良知責任的體認,即對無罪之罪與共同犯罪的體認,懺悔意識也正是對無罪之罪與共同犯罪的意識。” 歐洲自二戰後,出現了蔚為大觀的跟“懺悔意識”有關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和思想史論述,而在中國語境中觸及到這一問題的文論卻寥寥無幾,因此《罪與文學》有深遠的意義。
如果父親第一人生的理論和主張充滿了“救世”情結,那麼他的第二人生則著眼於“自救”。他所寫的文字是他在荒野隙縫中,為自己開闢的一片心靈的園地,來自於他內心真正的需求,不再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而是跨越古今中外,思考更為普遍和永恆的跟生命有關的命題。他曾說:“在宇宙的大明麗與大潔淨面前,方知生命語境大於歷史語境。” 《高行健論》是父親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對“文學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延續性思索。他注意到《靈山》中的“你”、“我”、“他”三人稱,正是內在主體的三坐標,構成了複雜的內在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另外,在第一人生中,他認同魯迅,傾向於做一位“精神界戰士”,一位能夠“攖人心”的摩羅詩人,一位積極擁抱社會、改變社會的知識分子,然而,在第二人生中,他更認同高行健,傾向於做一位超越潮流的冷觀者,用第三隻眼睛,審視世界和反觀自我的複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