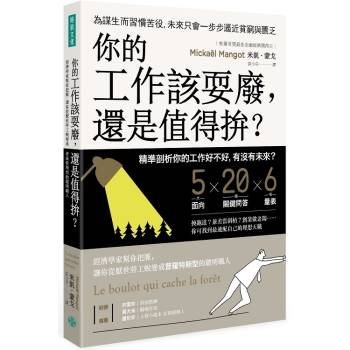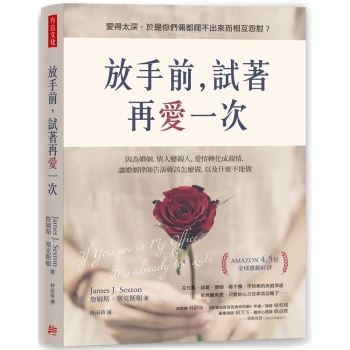代序:永遠的挑戰: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
歷史學是一門啟人心智的學問。它對於我們的吸引力,是與它所面臨的挑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誘導我們走上這條學術道路的,應該說,正是歷史學所仰賴、所辨析的豐富材料,也正是歷史學所關注、所回應的特有議題。
「材料(史料)」與「議題(問題)」,是歷史學者終日涵泳於其間、終生面對且需盡心竭力處理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水準的高下,正是取決於論著者對於「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於用語、詞彙的改變,必須從議題的瞭解與選擇、從材料的搜討與解讀開始。
一
就歷史學而言,材料(史料)是我們的源頭活水。梁啟超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他也回應了何謂「史料」的問題,指出:「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對於「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調度能力,無疑是對研究者基本素養的考驗。
新議題與新研究的出現,有賴於史料範圍的不斷開拓。當年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說法,正體現著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學人,頗由於議題難尋、材料匱乏而感覺困擾。走出困境的努力方向,一是尋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讀再解原有的歷史材料。
所謂不斷開拓,首先是對於新材料的開掘與運用。「新材料」中的一類,是諸如甲骨文、簡帛、出土文書、內閣檔案等陸續發現的材料,前輩學者對此給予高度的重視與期待。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這些新材料,不僅彌補了史料的缺失與不足,更促使著新問題的產生,決定著新的問題回應方式,影響著其後史學發展的路徑。
這類新材料的發現,未必能夠隨即還原出歷史的本來面目,或許帶給我們更多的是由此產生出來的新問題。而學者的任務正在於從這些新出現的問題出發,尋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決各類新問題的途徑與方法。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類,則是儘管長期存在卻一直被忽視的「邊緣材料」。這類材料從人們視而不見的背景下「湧現」出來,靠的是「問題意識」帶動下的新視角和新眼光。社會史領域的學者們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經典話語系統」,需要把研究的取材範圍從精英著述擴大到邊緣材料。這裡既包括文字資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傳統文獻之外的檔案、墓誌碑銘、方志輿圖、宗教典籍、醫書、筆記小說、詩詞乃至書信、契約、族譜等等),又包括對於各類實物、圖像、出土材料、考古遺蹟乃至情境場景(發生環境、社會氛圍等)的綜合認識及其與文字資料的互補互證。
材料出「新」,有賴於眼光的「新」。敦煌文書的學術價值,絕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能夠揭示;內閣大庫檔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著不同學術眼光之間的差距與更迭;如果沒有傅斯年、陳寅恪和李濟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觀,沒有他們心目中新的史學追求與問題關懷,殷墟發掘也不可能具備「近代」之意義。
新材料可以帶動新議題,但有些領域不夠幸運,沒有足以刺激新議題、衝擊原有研究體系的新史料發現,這就更加依靠於傳統史料的再研讀。嚴耕望先生曾經說:「新的稀有難得的史料當然極可貴,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從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黃永年先生在談及治學經驗時也說,他從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現,而是繼承了陳寅恪、顧頡剛等老一輩學人的做法,「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對於「舊」史料的再思考、新連結,能夠使其凸顯出以往不曾發現的新意。梁庚堯先生在其〈宋代太湖平原農業生產問題的再檢討〉一文中說:「本文所引據的資料,雖然多半出於前輩學者所已使用的範圍,但會有一些個人不同的組織與運用,以及進一步的比較與闡釋。」同樣的材料,切入角度不同、組織方式不同,呈現出的研究面貌便大不相同。
任何專題,都寓含在歷史的整體脈絡之中;任何研究,都需要有基本的材料面。網絡電子資源的豐富,使得今天的資料搜討手段遠遠勝於以往,同時也對研究者的解讀、分析、綜括能力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
對於材料,不能滿足於檢索搜討,更要注重平時的閱讀。老一輩學者經常提醒我們,要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只抱著題目找材料,很容易漏過真正重要的題目。我們在起步階段要想打下比較堅實的材料基礎,至少需要一兩部有影響力、有份量的史籍用來「墊底」,通過下功夫精讀,壓住自己的陣腳,儲備基本知識,增強解讀能力;進而「輻射」開來,逐步擴大材料面。
進入專題之後,要爭取「竭澤而漁」,要善於選擇最能切近主題的具體材料,這就如同入山採礦,第一反應是要瞭解資源何在,然後要能深入群山。特別是要充分調度角度不同、類型不同而彼此有所發明的材料,形成恰當的「材料組合」。能把哪些材料攬入視野、如何組織這些材料,直接決定著問題的闡發程度。
對於材料,不僅要能收集梳理,還要會比對辨析。「歷史」本身的歷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帶有特定的時代印痕與記述者的理解,不可能純粹客觀;對於歷史「真相」的追索與逼近,注定是一輾轉艱難而無止境的過程。材料的比對,或許正是這一過程的出發點。通過材料組合與比較,找出其異同,確定值得闡發的「問題點」進行辨析;辨析中可能牽涉到「事實」,也會關聯到「書寫」。例如,在現存史料中,有關宋代尚書內省的記載,簡略混沌,僅就該機構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年)改制一事的性質,《宋會要輯稿.后妃》《宋大詔令集.妃嬪》《九朝編年備要》《宋史》徽宗本紀及職官志等的說法即頗多差互。通過辨析,或印證,或質疑,都會給我們提供更為具體而廣闊的研究空間。
研究中使用的關鍵材料,要真正讀通,要善於「擠壓」「榨取」,充分提取其中的訊息。讀通,一要依靠相關的知識背景,二要勤於查詢。有位博士生,在討論隋代的禁衛武官時,引述《隋書》卷四三〈觀德王楊雄傳〉「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的說法,認為「楊雄為右衛大將軍,可參與朝政,可見禁衛武官不僅帶兵也有決策權」。其實這正如《新唐書.百官志》所說,是「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之濫觴。基本理解出了問題,導致結論失當,也使得本來可以用來討論制度變遷的寶貴史料從我們的指縫間輕易流失。
二
國內歷史學界有許多傳統的優勢,也承載著尋求學科生長點的迫切壓力。是否能夠準確地把握到學科的「生長點」,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敏銳地觀察到學術前行過程中核心的「問題點」。
「問題(議題)」對於我們的研究,具有一種先導意義。新史學是在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刺激下產生的,理論的指導意義不容低估,而理論往往產生於回應「問題」的過程之中。正如于沛在〈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科學—— 二十世紀我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回顧和思考〉一文中所說的,「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學理論的研究和建設,是中國史學發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學的發展,又不斷提出新的理論問題,有力地促進了對歷史進程或歷史學自身一系列理論問題的研究和探討。」二〇〇六年,廈門大學歷史系曾經召開題為「史料與方法——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歷史學」的學術研討會,收到了積極的效果。有參加者指出,「史料」與「方法」在實踐中並非對立,能將二者聯繫起來的關鍵是新的問題意識。有了新的問題,原有的史料會變成「新」史料,相應也會產生新的方法去處理這些新的史料,繼而形成新的體系。也就是說,引導出新方法的,往往是新的「問題」。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學者個人研究方向的選擇甚至畢生的學術事業,往往都是由廣闊的「問題群組」引導的。
有種現象或許值得一提:我們時常感覺到,當試圖說明「問題」這一概念時,難免遇到解釋中的紛擾:是指「疑難」、「困惑」、「麻煩」、「錯誤」,還是指「題目」、「議題」或「關鍵」?
這種語彙匱乏的狀況,和西方語境中對於「question」、「problem」、「trouble」、「mishap」與「topic」、「issue」、「point」等詞彙的細緻區分,迥然有別。毋庸諱言,這正體現出,在我們傳統的思維方式中,對於這樣一組相關範疇的認識並非周密充分。
近年來,不少研究著述、學位論文著意於「選題緣起」,會以「問題的提出」開篇,反映出注重問題導向的趨勢。學術「議題」的背後,牽繫著研究者的問題意識。這種意識貫穿於研究的全過程之中,即是要通過思考提出問題、展開問題、回應問題。「問題」決定於眼光和視野,體現出切入角度和研究宗旨,寓含著學術創新點。
「問題」不僅是研究的導引,也有益於促進融通。對於「問題」的關懷,使得各個研究領域的切分界限不再清楚,有利於調動諸多學術門類的研究力,實現多學科的交叉與結合。歷史現實中本沒有畛域的分隔,研究中專科專門的出現是為了針對性集中、為了便於深入,而這種領域的切分也可能造成理解中的斷裂、隔膜與偏頗。近些年的學術實踐使我們看到,以「問題」為中心組織研究,是跨越學科界限、促進交匯融通的有效方式。
歷史學的任務,本在於無限止的認識與再認識。如同史料需要「再發掘」一樣,有不少學術議題,看來有成說、似常識,其實具有「再認識」的空間與價值。社會性別史的研究者關注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的活動空間問題,而如何認識家庭「內/外」,並不像表面上那樣容易斷定區分。高彥頤對於明清女性「空間與家」的研究,即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再討論。
認識的「舊」與「新」,不在於提出的先後。要真正保持歷史學的創造性活力,重要的是要保持從研究心態到方法理路的常新。我們應該更加關注提問的方式,學習有層次地展開與回應。研究論著的內容是否具有新意,有時即取決於提問的角度與方式是否敏銳而個性化。提問要自「原點」出發,防範簡單化標籤化的主觀預設;問題不是凝固的平面板塊,要依其自身邏輯拆解分剝,以凸現其「立體」性;設問不能叢脞混雜地堆積鋪排,要把握其內在關聯,「由此及彼,由表及裡」,進階衍生式地合理組織。對於問題的回應,既要立論鮮明、自成一說,又要儘量保持開放性。
三
回顧上一世紀中國歷史學的發展路向,研究者常將以往代表性的學者分為「史料派」與「史觀派」,而仔細看去,史料派並非不具備史觀,史觀派也離不開對於史料的詮解。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說法,引起過許多詮釋與爭議。桑兵教授近期的研究,「用傅斯年的辦法來研究傅斯年的想法」,對此有十分深入的討論。在傅斯年這輩學者眼中,史料學顯然並不簡單等同於史料。如鄧廣銘先生指出的,「這一命題的本身,並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種理論、某種觀點立場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個從事研究歷史的人,首先必須能夠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鑒定其真偽,考明其作者及其寫成的時間,比對其與其他記載的異同和精粗,以及諸如此類的一些基礎工作。衹有把這些基礎工作做好,才不至被龐雜混亂的記載迷惑了視覺和認知能力而陷身於誤區,纔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於史實的真象。」事實上,在對待與處理史料方面具備特有主張與方式,形成為學說派別,方可稱之為「學」。
任何一種具有解釋力的研究模式,都需要由微見著的考訂論證作為其邏輯支撐。日本學者一些框架性很強的研究概念,例如「唐宋變革論」、「豪族共同體論」、「基體展開論」、「朝貢體系論」、「地域社會論」等等,也都是從問題的討論中,從實證的基礎上提煉生發出來。
歷史學的議題,有的重在甄別史實、敘述事件,有的重在闡釋、解構與建構,但無論哪種情形,都離不開材料,離不開實證。從根本上講,這是由歷史學的學科性質及特點所決定的。
楊訥先生在〈丘處機「一言止殺」再辨偽〉一文中說:「歷史學是一門重實證的學科。『一言止殺』故事,可以分解為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一是丘處機進言止殺,二是成吉思汗聽其言而止殺。若主張『一言止殺』實有其事,則理應對上述方面均予舉證。」在一些面向大眾的博物館中,會把對於「歷史」的追索比作尋蹤破案,這也體現出「舉證」的重要。學人研究中可能依靠不同的材料;有時從同樣的材料中,也會讀出不同的內容、看到不同的問題,而「舉證」則構成對話交流的平臺。
歷史學的探索,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出色的研究,往往從好的問題開始;而「好」問題是和學術前沿連帶在一起的。設問是在學術史的語境下提出,對學術史的回顧與觀察,正是為了尋求自己的學術起點,也就是論文議題的出發點。學術規範形式上是一系列技術標準與規則,實質上體現著學術意識與境界,是使學術受到尊重、取得進展的根本保證。學位論文選擇的「問題」,要具體真切、指向性強,而非懸游浮泛。議題展開是否順暢,關鍵在於「問題」的組合方式,這決定著材料的調度格局,也決定著脈絡的清晰程度。如何合理組織大小問題並引導自己的研究過程,考驗著我們的綜合能力。對於不同的議題,不同的學人,「合理」的方式自然各異,但總體上說,需要大邏輯套攏小邏輯,延展中儘量層次化、綿密化。要注意前與後、彼與此之間的銜接與區別、延續及斷裂;特別是,不僅要注意演進的端點,還要注意連接兩端的路徑與橋樑,探究過渡的層面、鏈條中的環節,這有助於形成新穎切實而富於洞察力與啟發性的認識。
論文寫作中,「材料」與「議題」,彼此不能「錯位」。曾經有位同學撰寫〈元代兩浙婦女生活初探〉,副標題是「以《鄭氏規範》為中心」。我們知道,「婦女生活」是指一種社會「實態」,而《鄭氏規範》體現的主要是「規範」及其滲透的「理念」,如果僅用《鄭氏規範》這一材料來討論婦女生活這一議題,二者容易發生錯位。
四
一波波「新史學」浪潮之中,歷史學的「史」與「論」、材料與問題(議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中心話題;而前行道路上的探索與周折,也通常是由此而起。
理論與方法,對於歷史學來說,是啟示而非模式。吳承明先生贊成「史無定法」之說,並且解釋道,「史無定法」有一個中心點是實證。「我同時把一切理論都看成是方法。」他認為,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向性,而是根據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這一提法,把所有理論都還原為從事歷史分析的具體工具,無疑具有促進思想解放的作用。在歷史學的脈絡中看,適用的「方法」,正是植根於特定的材料與問題(議題)之中。
史料的開拓與問題意識的形成,是學術事業的基點,是健康學風的要求;這離不開學術敏感,離不開自覺建設。從這一意義上說,材料與問題(議題),是對於學業切實的引導,也是對學人永遠的挑戰。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宋代文官制度六題的圖書 |
| |
宋代文官制度六題 出版日期:2021-09-0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87 |
Others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中國歷史 |
$ 396 |
中國歷史 |
$ 39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宋代文官制度六題
本書為「三聯人文書系」之一種,由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的六篇研究論文集結而成。內容圍繞宋代文官制度,尤其是官員的任用與考核制度展開,是作者對於宋代文官制度研究的精華之集。
具體論述涵蓋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北宋的循資原則及其普遍作用、宋代資序體制的形成及其運作、北宋文官磨勘制度、宋代文官差遣除授制度研究、宋代地方官員政績考察機制的形成。此外,本書也收錄了作者對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的認識。
作者簡介:
鄧小南,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國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
曾在「北大荒」雁窩島下鄉九年。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一九八五年研究生畢業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曾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德國維爾茲堡大學、圖賓根大學,韓國高麗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等學府講學及從事合作研究。
著有《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潤學史叢稿》、《宋代歷史探求》、《課績.資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側談》、《長路》等,在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研究論文百餘篇。
北京大學「十佳教師」。曾獲國家級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思勉學術原創獎、國華傑出學者獎等。
作者序
代序:永遠的挑戰: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
歷史學是一門啟人心智的學問。它對於我們的吸引力,是與它所面臨的挑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誘導我們走上這條學術道路的,應該說,正是歷史學所仰賴、所辨析的豐富材料,也正是歷史學所關注、所回應的特有議題。
「材料(史料)」與「議題(問題)」,是歷史學者終日涵泳於其間、終生面對且需盡心竭力處理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水準的高下,正是取決於論著者對於「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於...
歷史學是一門啟人心智的學問。它對於我們的吸引力,是與它所面臨的挑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誘導我們走上這條學術道路的,應該說,正是歷史學所仰賴、所辨析的豐富材料,也正是歷史學所關注、所回應的特有議題。
「材料(史料)」與「議題(問題)」,是歷史學者終日涵泳於其間、終生面對且需盡心竭力處理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水準的高下,正是取決於論著者對於「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於...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