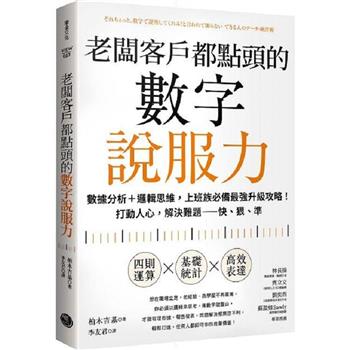“探討人生,總不能不聽聽禪家的發言。”
“說禪,如果決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那就只好站在禪堂之外。”
——張中行
本書是著名文史專家張中行先生談論佛教禪宗的著作。
“禪”來源於佛教,是歷史文化的重要一支。本書清晰梳理出佛教中土化的源流發展脈絡,分宗別派,從生活、學術、文學藝術等方面分述其影響。作者立身禪外,把恍兮惚兮的名相變為明晰易解的知識,旁參儒家道學等各家理論,解釋深入淺出,使不懂禪理的讀者也能略知其輪廓。字裏行間既指出教義與修持之道的積極意義,同時亦坦承其中離奇難解,及其難於實現之處。本書作為禪學入門書,歷久而不過時。
“禪”是一種人生之道,面對人生的種種欲望、無常、順逆、得失,總不能不聽聽禪家之言。加之時下瑜伽、頌缽、禪修冥想、靜觀正念的風氣盛行,說明現代人面對躁動營役的生活,希望透過禪的修持方法和生活態度為思緒尋找出口。從這一層面上看,本書亦不失為認識人生的經典之作。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禪外說禪(普通本) (電子書)的圖書 |
 |
禪外說禪 作者:張中行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11-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60 |
中文書 |
$ 560 |
禪修 |
$ 639 |
佛教 |
$ 639 |
宗教 |
$ 639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禪外說禪(普通本)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中行(1909-2006)
原名張璿,字仲衡。著名學者、哲學家、散文家。1909年1月生於河北省香河縣一農家。1931年畢業於通縣師範學校。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曾任教於中學、大學,亦曾編過期刊。1949年後就職於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
先生涉獵廣泛,遍及文史、哲學諸多領域,是二十世紀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與季羨林先生、金克木先生合稱“燕園三老”。著作先後出版有《文言津逮》《佛教與中國文學》《作文雜談》《負暄瑣話》《文言和白話》《負暄續話》《禪外說禪》《詩詞讀寫叢話》《順生論》《談文論語集》《負暄三話》《說夢樓談屑》《橫議集》《說書集》《流年碎影》《說夢草》《散簡集存》《張中行全集》等。其中或記舊人舊事,或談學論理,或探究人生,見識深邃,文筆獨特。
張中行(1909-2006)
原名張璿,字仲衡。著名學者、哲學家、散文家。1909年1月生於河北省香河縣一農家。1931年畢業於通縣師範學校。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曾任教於中學、大學,亦曾編過期刊。1949年後就職於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
先生涉獵廣泛,遍及文史、哲學諸多領域,是二十世紀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與季羨林先生、金克木先生合稱“燕園三老”。著作先後出版有《文言津逮》《佛教與中國文學》《作文雜談》《負暄瑣話》《文言和白話》《負暄續話》《禪外說禪》《詩詞讀寫叢話》《順生論》《談文論語集》《負暄三話》《說夢樓談屑》《橫議集》《說書集》《流年碎影》《說夢草》《散簡集存》《張中行全集》等。其中或記舊人舊事,或談學論理,或探究人生,見識深邃,文筆獨特。
目錄
第一章 弁言 ... 001
第二章 觀照人生 ... 017
第三章 佛法通義 ... 037
第四章 中土佛教 ... 071
第五章 禪宗史略 ... 121
第六章 禪悟的所求 ... 201
第七章 漸與頓 ... 233
第八章 師徒之間 ... 267
第九章 機鋒公案 ... 307
第十章 禪悅和禪風 ... 345
第十一章 理想與實際 ... 367
第十二章 可無的贅疣 ... 383
第十三章 禪的影響(上) ... 405
第十四章 禪的影響(下) ... 439
第十五章 餘論 ... 465
第二章 觀照人生 ... 017
第三章 佛法通義 ... 037
第四章 中土佛教 ... 071
第五章 禪宗史略 ... 121
第六章 禪悟的所求 ... 201
第七章 漸與頓 ... 233
第八章 師徒之間 ... 267
第九章 機鋒公案 ... 307
第十章 禪悅和禪風 ... 345
第十一章 理想與實際 ... 367
第十二章 可無的贅疣 ... 383
第十三章 禪的影響(上) ... 405
第十四章 禪的影響(下) ... 439
第十五章 餘論 ... 465
序
餘論
回顧既往
禪宗是中土佛教的一個宗派,禪是佛教中一種有特點的修持方法,講禪,尤其在理的方面,常常不能離開佛教,因此,本章打算混起來講。這裏稱餘論,意思是有關禪的一些情況講完了,用剩餘的筆墨總的說說。這所說偏於評價,自然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想由時間方面分作兩部分,過去和未來。先談過去,有以下幾點意思。
第一點,佛道是值得珍視的。前面一再說過,人生,作為一種客觀現實,是“一”,人生之道是“多”。這有如同是吃,有人喜歡酸的,有人喜歡辣的。同理,同是住在世間,有人喜歡朝市,有人喜歡山林。不同的選擇,都是求生活安適,或者用人生哲學的術語說,求快樂。可是說到快樂,問題又是一大堆。如叔本華就不承認有積極性質的快樂。佛家更進一步,認為錦衣玉食,聲色狗馬,以及娶妻生子,柴米油鹽,都沒有甚麼快樂可言,而是苦。擴大了說,世間就是苦海。這是“知”,知之後要繼以“行”,於是求滅苦之道。辦法是出世間。由常人看,這想法很怪。但仔細思考,生活中有苦,甚至多苦,也確是事實。還有,即使撇開苦。心安理得問題,有不少人是常常想到而沒有解決。這用佛家的話說,是生死大事未了。總之,人生確是有佛家所想的那樣的問題,即使在有些人的眼裏,問題並不那麼嚴重。有問題,應該解決,用甚麼辦法?佛道(尤其禪)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種辦法,而且有不少人真就這樣做了。做的結果呢?至少是信士弟子承認,有不少人真就斷了煩惱。也有不少人或者抱存疑態度,這也無妨。我們站在禪外,應該用公平的眼光,把它看作對付人生中某種病的一種方劑,如果真就得了這種病,那就無妨用它試一試。這是說,它是人生哲學方面的一種祖傳的遺產,保存以備用總是應該的。
第二點,慈悲的價值不可輕視。佛教修持的所求,小乘可以滿足於自了;大乘不然,菩薩行還要推己及人。儒家也主張推己及人,所以《論語》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佛家更進一步,是大慈大悲,就是擴大到人以外的“諸有情”或“眾生”。這由常人看,是過於理想,貫徹很難。不過理想有理想的價值,如中土自佛教盛行以後,也由於有果報說的輔助,推崇慈善、厭惡殘忍的思想感情總是很強烈,這對於維持社會的安定,緊密人與人的關係,應該說是有相當大的作用。打開窗戶說亮話,所謂“德”,不過是人己利害衝突的時候,多為人想想而已。慈悲的思想感情正是培養德的強大的力量,所以不只應該保存,而且應該發揚光大。
第三點,中土佛教的天台、華嚴、法相等宗,都著重繁瑣名相的辨析。禪宗走另一條路,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兩者相比,禪宗是走了簡明的路。所謂“簡”,是比較容易,如不通《成唯識論》等書同樣可以得解脫。所謂“明”,是比較容易說清楚,如自性清淨,當作信念堅持,日久天長就會雜念減削而感到心體湛然;如果鑽研唯識學說,到末那識、阿賴耶識那裏打轉轉,那就有陷入概念大海的危險。此外,禪還有接近世俗的優越性,就是說,容易致用。總之,中土佛教唐以後禪宗獨盛,既是演變的必然,又是選擇的當然。
第四點,是理想離現實太遠,難於實現。前面多次說過,佛道是以逆為順。逆甚麼?是逆《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這性,告子說得簡明具體,是“食色,性也”。對這些,佛家硬說是染污,甚至萬法皆空。要求清淨真實的,即所謂實相、真如、涅槃之類。這些事物實質是甚麼?在哪裏?難言也。且從頂端降下一層,不再問能不能證涅槃,只求能夠滅情欲以斷煩惱。可是情欲偏偏來於“天命之謂性”,順,容易,抗就太難了。自然,太難不等於不可能,有少數人,如馬祖、趙州之流,大概是斷了煩惱,夠得上真是悟了。可是,這正如《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家所說:“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因為太難,我的想法,自魏晉以來,出家、在家四眾,數目多到數不清,真正能夠解脫的恐怕為數不多。不能而住山林,持齋唸佛,參禪打坐,其中究竟還有多少煩惱,雖然難於確知,卻是可以想見的。這悲哀是隱蔽的。還有公開的,是把削髮為僧尼看作一條生路,甚至另一種養尊處優的生路,那就是名為出世間實際是入世間了。一部分所謂信士弟子,由以逆為順之難走到有名無實之假,也是佛教的悲劇的一面。這悲劇,應該由教理負責呢,還是應該由一些信徒負責呢?也許是兼而有之吧?
……
回顧既往
禪宗是中土佛教的一個宗派,禪是佛教中一種有特點的修持方法,講禪,尤其在理的方面,常常不能離開佛教,因此,本章打算混起來講。這裏稱餘論,意思是有關禪的一些情況講完了,用剩餘的筆墨總的說說。這所說偏於評價,自然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想由時間方面分作兩部分,過去和未來。先談過去,有以下幾點意思。
第一點,佛道是值得珍視的。前面一再說過,人生,作為一種客觀現實,是“一”,人生之道是“多”。這有如同是吃,有人喜歡酸的,有人喜歡辣的。同理,同是住在世間,有人喜歡朝市,有人喜歡山林。不同的選擇,都是求生活安適,或者用人生哲學的術語說,求快樂。可是說到快樂,問題又是一大堆。如叔本華就不承認有積極性質的快樂。佛家更進一步,認為錦衣玉食,聲色狗馬,以及娶妻生子,柴米油鹽,都沒有甚麼快樂可言,而是苦。擴大了說,世間就是苦海。這是“知”,知之後要繼以“行”,於是求滅苦之道。辦法是出世間。由常人看,這想法很怪。但仔細思考,生活中有苦,甚至多苦,也確是事實。還有,即使撇開苦。心安理得問題,有不少人是常常想到而沒有解決。這用佛家的話說,是生死大事未了。總之,人生確是有佛家所想的那樣的問題,即使在有些人的眼裏,問題並不那麼嚴重。有問題,應該解決,用甚麼辦法?佛道(尤其禪)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種辦法,而且有不少人真就這樣做了。做的結果呢?至少是信士弟子承認,有不少人真就斷了煩惱。也有不少人或者抱存疑態度,這也無妨。我們站在禪外,應該用公平的眼光,把它看作對付人生中某種病的一種方劑,如果真就得了這種病,那就無妨用它試一試。這是說,它是人生哲學方面的一種祖傳的遺產,保存以備用總是應該的。
第二點,慈悲的價值不可輕視。佛教修持的所求,小乘可以滿足於自了;大乘不然,菩薩行還要推己及人。儒家也主張推己及人,所以《論語》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佛家更進一步,是大慈大悲,就是擴大到人以外的“諸有情”或“眾生”。這由常人看,是過於理想,貫徹很難。不過理想有理想的價值,如中土自佛教盛行以後,也由於有果報說的輔助,推崇慈善、厭惡殘忍的思想感情總是很強烈,這對於維持社會的安定,緊密人與人的關係,應該說是有相當大的作用。打開窗戶說亮話,所謂“德”,不過是人己利害衝突的時候,多為人想想而已。慈悲的思想感情正是培養德的強大的力量,所以不只應該保存,而且應該發揚光大。
第三點,中土佛教的天台、華嚴、法相等宗,都著重繁瑣名相的辨析。禪宗走另一條路,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兩者相比,禪宗是走了簡明的路。所謂“簡”,是比較容易,如不通《成唯識論》等書同樣可以得解脫。所謂“明”,是比較容易說清楚,如自性清淨,當作信念堅持,日久天長就會雜念減削而感到心體湛然;如果鑽研唯識學說,到末那識、阿賴耶識那裏打轉轉,那就有陷入概念大海的危險。此外,禪還有接近世俗的優越性,就是說,容易致用。總之,中土佛教唐以後禪宗獨盛,既是演變的必然,又是選擇的當然。
第四點,是理想離現實太遠,難於實現。前面多次說過,佛道是以逆為順。逆甚麼?是逆《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這性,告子說得簡明具體,是“食色,性也”。對這些,佛家硬說是染污,甚至萬法皆空。要求清淨真實的,即所謂實相、真如、涅槃之類。這些事物實質是甚麼?在哪裏?難言也。且從頂端降下一層,不再問能不能證涅槃,只求能夠滅情欲以斷煩惱。可是情欲偏偏來於“天命之謂性”,順,容易,抗就太難了。自然,太難不等於不可能,有少數人,如馬祖、趙州之流,大概是斷了煩惱,夠得上真是悟了。可是,這正如《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家所說:“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因為太難,我的想法,自魏晉以來,出家、在家四眾,數目多到數不清,真正能夠解脫的恐怕為數不多。不能而住山林,持齋唸佛,參禪打坐,其中究竟還有多少煩惱,雖然難於確知,卻是可以想見的。這悲哀是隱蔽的。還有公開的,是把削髮為僧尼看作一條生路,甚至另一種養尊處優的生路,那就是名為出世間實際是入世間了。一部分所謂信士弟子,由以逆為順之難走到有名無實之假,也是佛教的悲劇的一面。這悲劇,應該由教理負責呢,還是應該由一些信徒負責呢?也許是兼而有之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