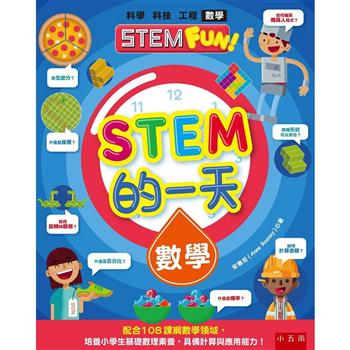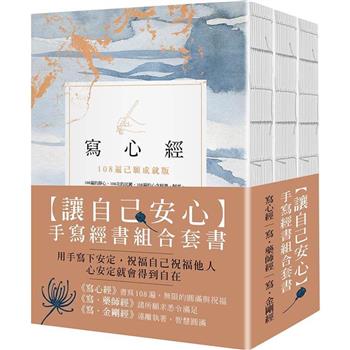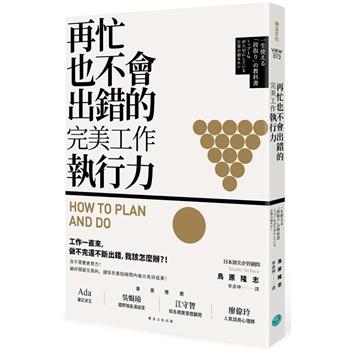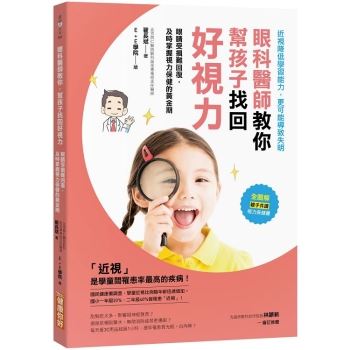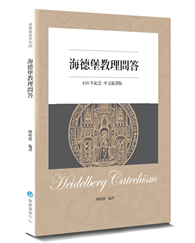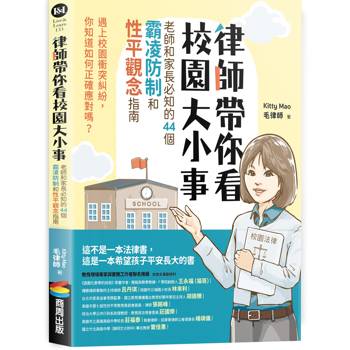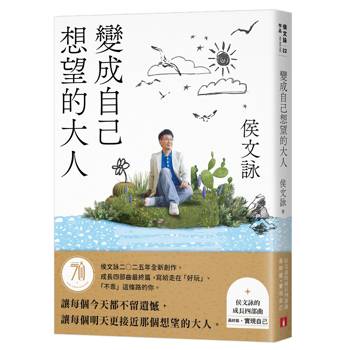自序
一、周恩來總理下達任務與我參加《中華民國史》編寫組的經過
中國有隔代修史的傳統。一個新的朝代建立了,要為前一個朝代修史。例如,明王朝建立了,要為元王朝修史;清王朝建立了,要為明王朝修史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老一輩革命家董必武、吳玉章即提出,要為中華民國修史。當時曾列入國家科學發展12年規劃。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規劃未能落實。直至1972年,周恩來總理重提此事,並由當時的國務院出版口將這一任務下達給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任吳玉章秘書、時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的李新教授勇敢地接受這一任務,並且說幹就幹,組織班子,制訂規劃,聚集人材,開始工作。起始的任務是編資料,即首先編寫《中華民國大事記》、《中華民國人物傳》和《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後者是一組專題資料,涉及的題目有好幾百個。李新教授的想法是,編資料有了頭緒之後,才啟動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的寫作。
我於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分配到一個和研究無關、可以說沒有起碼研究條件的單位。我在大學時研究過清末和民國時期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發表過有關論文。恰巧,《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有《南社》一題。1974年10月,我被邀請參加該題的寫作。1977年,《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華民國的創立》寫作啟動,我被邀請執筆其中的一章—《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鬥爭》。這樣我就成了《中華民國史》編寫組的正式成員。全書初稿寫出後,我奉命參加統稿,修改和重寫《武昌起義》一章。該書出版後,我奉命撰寫並主編第二編第五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現為第六卷)。
《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的主角是孫中山,早有定評,國共兩黨並無重大分歧,困難之處在於如何發掘新資料,將這一人物寫得更科學、更準確、更豐滿、更生動,因此我在寫作時並無任何思想負擔。但是寫到蔣介石,就大不一樣了。北伐時期,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成了這一時期的主角,但是,對這一個人物,後來國共兩黨的評價天地懸殊。譽之者視為“功勳蓋世,千古一人”,斥之者貶為“人民公敵,獨夫民賊”。怎麼寫?面對這一超級難題,我仍然毫無顧慮。這是因為,我想,只要堅持“實事求是”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力求從史實出發,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就不會犯大錯誤,而且,當時改革開放已進入高潮,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深入人心,學術界思想解放,允許探索,允許創新,我有何背負沉重思想負擔的必要呢!
當然,戰略上樂觀,戰術上卻必須慎之又慎。北伐戰爭的時間不過三年,我和幾位合作的學者寫這本書的時間卻用了整整十年。該書出版於1992年,出版之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金沖及教授發表評論,認為“這部近60萬字的巨著,許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前人又有新的突破。它是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內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李雲漢教授也發表評論,認為該書“內容充實,體系完整,能脫出舊窠臼而能運用多方面的史料”,“除對蔣中正尚是斧鉞交加外,其他敘述都甚平實可信” 。我們的這卷書寫北伐戰爭的全過程,其中既有國共兩黨共同作戰,並肩對敵,也有兩黨分裂,刀兵相見,不共戴天,因此之故,許多歷史事件的評論歷來不同,而我們的書卻能得到兩黨黨史研究領導人的共同好評,我自然非常非常高興。
我原來的理想是當作家,當詩人。北大五年,改為想當文學研究者。1977年,近代史研究所決定調我進所。經歷種種曲折,重重困難,1978年4月,調動成功。我當時的想法是幹幾年,然後找機會回頭搞文學。不想幾年下來,我認識到歷史學的重要,也感到了歷史學有著無比廣闊的天地,值得我投入一輩子,甚至幾輩子的精力,就決心與文學告別了。
2003年9月10日,溫家寶總理到中央文史研究館視察,親自主持座談會。我即席發言,表示編寫《中華民國史》是當年周恩來總理交給我們的任務,現在完成了一部分,還有許多部分尚未完成,主編已經病危,希望溫總理幫助我們,完成周總理交給我們的未竟之業。溫總理當時要我寫一份報告給他。此後,我聯絡原《中華民國史》編寫組的兩位骨幹耿雲志與曾業英,共同給溫總理寫報告,提出了一份約4000萬字的擴充修訂計劃。9月29日,溫總理批交文化部、教育部就此事進行調查研究。10月17日,我們第二次給溫總理寫信,報送已經出版的26部著作,提出增修黨派誌、政府誌、社團誌等39種誌書和30餘種圖表的計劃。11月5日,溫總理批交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領導“閱酌”。此後即無消息。2004年8月1日,原國民黨大佬居正之女居蜜博士自美國華盛頓上書溫總理,要求加速《中華民國史》的編寫。溫總理批交國務委員陳至立處理。陳至立國務委員批請文化部提出意見。後來了解到,文化部領導經過研究,認為以戴逸教授領銜的國家清史工程正在進行,《中華民國史》的擴大、修訂問題需要“擱一擱”。
鑒於上述情況,我便決定繼續重點研究蔣介石,這個曾經身任國民黨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中華民國總統,集黨政軍三大權力於一身的人,為中華民國史研究做點不能繞開的工作。
二、我研究《蔣介石日記》的經過
我奉命主持《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的編寫工作後,因為蔣介石是這一時期的主角,便留心收集蔣介石的有關資料,研究其中重大的帶有關鍵性的問題。我了解到,1926年3月20日發生於廣州的的中山艦事件撲朔迷離,親共的學者認為是蔣介石的陰謀,親國民黨的學者認為是共產黨的陰謀,蔣介石自己則稱,要了解事件的真相,只有在他死後看他的日記。自此,這一事件便成為不解之謎,兩派學者爭持不下。
蔣介石有愛保存歷史資料的習慣。大概是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自己早年的部分日記、電稿、文稿、函札交給毛思誠保管。毛是蔣介石青年時代的老師,後來成為他的秘書。毛思誠接到這批文件後,一直藏在寧波家中。“文革”期間,紅衛兵在毛家發現了這批文件,層層上報,一直報到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文革”後落實政策,毛思誠家人將這批文件捐獻給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83年,我到南京該館查檔,無意中發現了這批資料。其中有一份題為“黨政”,我很快意識到,這就是寧波毛家的原藏品。全名《蔣介石日記類抄》,分黨政、軍務、學行、文事、雜俎、旅遊、家庭、身體、氣象等9類,都是從蔣介石日記中摘錄出來的。其中就有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期間的日記。我手頭有當年寧波方面留下的檔案目錄,於是按目索驥,一卷卷、一件件調閱。看了審理中山艦事件有關人員的記錄、報告,也看了蔣介石、汪精衛之間的通信,經過一段時期的研究,終於發現,中山艦事件的起因並非蔣介石的陰謀,也不是中共的陰謀,而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和孫文主義學會製造的謠言,其目的在於離間廣州國民政府的內部團結。生性多疑、對中共的發展懷有戒懼心理的蔣介石誤信謠言,因而採取了錯誤行動。偶然中有其必然性。文章發表後,胡喬木同志幾次對中共黨史學界的領導人發表談話,肯定拙文“運用大量翔實的歷史材料,將中山艦事件的來龍去脈梳理得很清楚,作出了中肯的分析,真正解開了這個歷史之謎”,“是近年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準的學術文章”,“希望黨史研究也能作出這樣好的成果”。 他並在接見我時當面鼓勵:“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文章很快被日本學者和美國學者譯為日文和英文,在各自國家的學術刊物上發表。 該文在台灣學界也迅速獲得好評。蔣永敬教授原是國民黨部隊的政工人員,後來進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做研究,從黨史會退休後進入政治大學任教,也寫過關於中山艦事件的文章,獲得過盛譽。讀了拙文之後,他親自到北京見我,高度評價拙文,表示願意將“盛譽”轉讓給我。此後,他幾乎“到處逢人說項斯”,只要有機會,他就要誇獎拙作。
毛思誠所存蔣介石早年檔案中,除了《蔣介石日記類抄》外,還有蔣介石1931年全年日記的仿抄本1冊、1932年半冊。1995年,我根據上述資料寫成《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一文,提交當年台灣學界舉辦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學術討論會,獲得會議重視,被安排為首場的第一篇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訪問台灣。此後我訪台機會漸多,在“國史館”發現了蔣介石日記的另一種摘抄本—《困勉記》、《省克記》、《學記》、《愛記》、《遊記》等《五記》。毛思誠的《蔣介石日記類抄》時間自1919年至1926年,《五記》則延長到1945年。我用喜馬拉雅基金會資助我的5萬台幣,聘用台灣學生全文照錄,繼續寫了一批文章,集結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設有中華英才基金會,專門資助黨外專家出版學術著作。我經社會科學院推薦,並經嚴格審查、評議,獲得批准,由王兆國部長召開大會,宣佈給予資助。該書後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再次報批、審讀,與我的其他兩部書《海外訪史錄》和《從帝制走向共和》組成“近史探幽系列”出版。
讀了兩種蔣介石日記的摘抄本,我進一步關心蔣介石的全本日記何在。從台灣《聯合報》的一位記者口中,我得知蔣介石的全部日記保存在蔣經國的次子蔣孝勇的夫人方智怡女士手中,我便通過該記者傳話,《日記》史料價值很高,務必慎重保管。
大概是2005年,美國胡佛研究所的馬若孟(R. H. Myers)、郭岱君兩位教授從舊金山專程到北京來看我。他們給我帶來了絕好的消息:方智怡女士決定將《日記》寄存胡佛檔案館50年,將於明年3月下旬開放,邀請我屆時前往閱覽。這自然使我高興之至。光陰似箭,轉眼就到了開放日期,我和近代史研究所張海鵬所長提前到了斯坦福大學,在研究生宿舍租房住下。開放前一日,我和海鵬教授相約,第二天早點去,免得排長隊。第二天,我們到達位於地下的檔案館閱覽室時,發現並無人排隊。原來,我們二人是主人專門邀請的客人,《日記》開放的消息尚未廣為宣佈。我們花幾分鐘時間填了張表,在不得照相、不得複印、不使用電腦,只能手抄的保證書上簽了字,就開始調閱《日記》的影本了。《日記》影本就放在櫃檯工作人員身後的盒子裏。我報了需查閱的月份,工作人員隨手取給我,簡便之至。
胡佛檔案館方面宣稱,《蔣介石日記》從1915年開始,至1972年蔣介石去世前三年為止,但我檢查,發現缺少1915、1916、1917、1924年這4年,實存53年。公佈前規定,凡涉及個人及家庭隱私、身體狀況者不能開放,須作技術處理。秦孝儀先生的學生潘邦正代表蔣家,曹麗璿女士代表宋家參加審查,作技術處理的地方在影本上以墨塗黑,同時蓋章說明處理時間,30年後恢復原狀。全部日記分四批開放,每次開放約十年左右的日記。我從2006年起,共赴胡佛檔案館四次,以10個半月的時間讀完全部蔣介石日記,摘抄了大部分內容。
我的《中山艦事件之謎》以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都是根據《蔣介石日記》的摘抄本寫的。摘抄本的水準如何?有無斷章取義、歪曲竄改之處?如果有,我此前的研究豈不是根基不牢,須要推倒重做嗎?因此,我在到胡佛檔案館之前,心中不無惴惴,及至進了胡佛,仔細讀了蔣介石日記的影本,發現原來的摘抄非常之好,處理恰當,我原來的立論都可以成立,連引文都不需要更動。
日記有兩種,一種是準備出版,給別人看的,一種是只給自己看,在身前不準備出版的。從蔣介石不避諱寫自己的隱私和內心醜惡、齷齪、難以示人的念頭,也不避諱罵人,他的同事、親朋、下屬,如胡漢民、孔祥熙、宋子文、孫科,以至自己的老婆宋美齡,無人不罵。從這些方面看,我判定其日記屬於後一種,只給自己看,因此,沒有向公眾宣傳、粉飾自己,哄騙社會公眾的必要。此類日記,有較高的真實性,但是,也會有不願記、不能記,粉飾、美化自己,甚至作假的情形。我由此認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不看蔣介石日記,會是很大的損失,但是看了之後,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受騙,必須廣泛收集史料,對照其實際行動謹慎判別、考證、辨析。
自來的政治家,人們可以從他的公開言行去觀察他,研究他,但是政治家很少向公眾敞開自己的內心世界,因此,歷史家很難了解政治家公開言論背後的真實的隱蔽的意圖。蔣介石日記大量記載自己的思想活動,這就向歷史家敞開了心靈的窗戶,使歷史家不僅知道他做什麼,而且知道他為何這樣做。此外,政治家的許多活動是公開的,人們可知可見,但是,有許多活動是黑箱作業,人們難知、難見。蔣介石的這些黑箱作業,有些會在日記中有部分記載,或者透露出蛛絲馬跡,便於歷史家追蹤、探尋。因此,我決定利用這部《日記》,同時廣泛地收集各國和中國各黨、各派、各方的有關資料,參稽考辨,力求為讀者還原一個真實的蔣介石。
2008年,我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出版,立即在國內外、境內外引起較大反響。深圳《商報》邀請專家評選年度十大好書,據悉,全體評委一致推舉拙書為十大好書中的第一部,但不久即奉命撤除,臨時換了另一部書。瀋陽《商報》也評選十大好書,拙書也被選入列。報社及時通知我並讓我寫了《獲獎感言》,久久未見刊出。我打電話詢問,是否深圳故事重演?答云:評獎有效,但決定不宣傳。事後,報社給我寄來了獎盃。其後,全國31家媒體和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共同評選十大好書,拙書依然入列。我曾詢問,“上面”是否同意?答稱:上面認為資料豐富,同意。這樣,我就不僅高興,而且感激。顯然,這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在起作用。喬木同志要我“堅持這樣走下去”,自然,我沒有任何理由半途而廢。於是,接著寫,也繼續得到社會的鼓勵。第二集入選在廣州舉行的南國書香節的“金南方2011年最受關注歷史類圖書”榜單。第三集獲在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2014年十大好書獎”,在境內則獲得《作家文摘》舉辦的“十大好書獎”。第四集繼續獲《亞洲週刊》“2017年十大好書獎”,在境內則獲得《南方週末》舉辦的2018年“非虛構類讀物十大好書獎”。加上此前我得到過的“香港書獎”等,這樣,我的研究蔣介石的書幾乎每集都得獎,有時甚至是雙獎、多獎。我感到這一切都是社會和廣大讀者對自己的鼓勵,表明了社會和讀者對研究蔣介石著作的需要。
三、關於本書
到2018年底止,關於蔣介石其人,我已經出版了5本書,這就是最初出版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以及其後陸續出版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1至第4集。有朋友建議我出一部合集,這是個好主意,但是,簡單地湊合在一起又不行,這是因為,蔣介石有些方面,我還沒有寫到,更重要的,是上述各書並非成於一時,而是成於幾十年間。原始資料的發現和收集有一段漫長的過程,即以《蔣介石日記》而論,從我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現《蔣介石日記類抄》到《蔣介石日記》在美國全部開放,也經歷了二十多年。我的寫作原則是,一個題目,資料大體齊全了,條件成熟了,我才動筆寫作。這樣,我的寫作就無法按部就班,而只能成熟一個題目寫一個題目,出書時只能做到一本書之中,其時間先後有序,而各書之間,其時間則可能是交叉的,要合編,除補寫必要的篇目外,還必須將各書打亂,嚴格按歷史事件的先後重新排序。我還有若干文章,與《蔣介石日記》無關,但與蔣介石緊密相關,收在我的其他著作,如五卷本《楊天石近代史文存》裏。此次出書,就必須將它們收進來,一起排序,因此,本書不是個人關於蔣介石研究某部著作的再版或增補,而是個人關於蔣介石研究論文的增訂與選編,其他雖涉及蔣介石,而非以其為主角者則另編。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終了的結果。”“不是自然界和人類要適合於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只有在其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之時才是正確的。” 我一生治史,服膺恩格斯的這一段名言。從史實出發,還是從原則或其他什麼先驗的結論出發,是保證在歷史研究中能否堅持唯物主義的分水嶺。可以說,史實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也是檢驗歷史著作科學水準高低的重要標準。我願意以恩格斯的上述名言和同行互勉,也和讀史者、評史者共勉。最近寫了一首小詩,中云:
道是有情卻無情,功過條條縷縷明。
史筆千秋大義在,鏡中歷歷顯原形。
歷史好比一面鏡子,只要我們掌握史實,善用這面鏡子,拋棄各種主觀的、客觀的障蔽,任何複雜的歷史人物都可以功過清晰,是非分明。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個十分複雜的人物,運用科學理論與科學方法對之進行研究,給以科學的敘述和定位,是我們這一代歷史學家義不容辭的任務。這一工作做好了,將大有利於整個中國近代史科學水平的提高,也大有利於與台灣同胞以及世界各地愛國華人的大團結,應該繼續做下去,且力爭做好。
記得2002年2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次年7月,有自號“秀龍山人”者,化名“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軍、老新四軍、老解放軍戰士”,在網上發表致中共中央及胡錦濤同志的公開信,題為《蔣介石是中國的“民族英雄”,還是“頭號戰犯”、“千古罪人”、“民族敗類”?》,要求治我以“叛國罪”,並藉機攻擊改革開放政策。當時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奎元院長奉命“閱研”。事後向中共中央彙報,認為拙書是“扎實的學術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胡錦濤總書記批示:“此事到此為止。”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指示院裏派負責人和我談話,要我繼續安心研究。此事遂得以平息。至今想起此事,我仍然非常感謝胡錦濤、李長春、陳奎元等有關領導的關懷和愛護。沒有他們的關懷和愛護,我的蔣介石研究和出版可能很困難,很困難。
本書分5卷,寫了近百個專題,此次出版,在舊著5本之外又補寫了若干新篇章,共107題。個人感覺尚有若干專題可寫,或可補寫,但個人條件還不成熟,只能期之以異日。所論如有謬誤,史實或有不確,均請讀者批評指正。跂予望之。
2019年7月31日初稿於云南大理,洱海之濱,10月改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