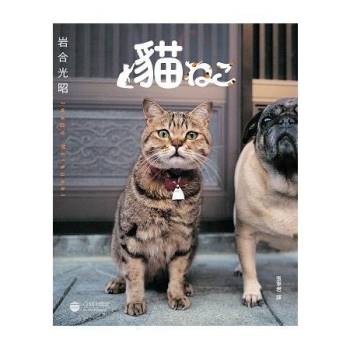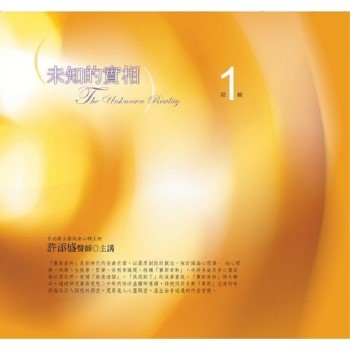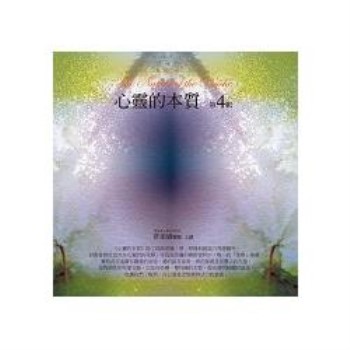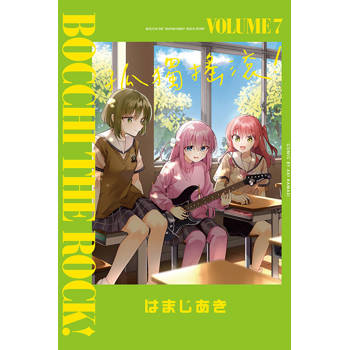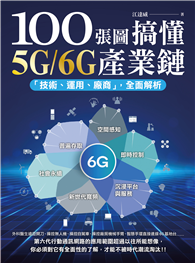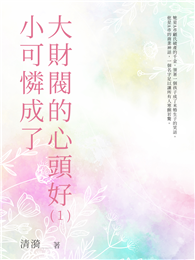旗袍,是展現中國女人特有的女性美的最佳代名詞,它是如此曼妙婉轉、婀娜多姿、自帶風情,既讓中國女性癡迷,亦讓世界女性驚歎。
畫家陸梅最愛旗袍之美,亦擅畫旗袍女子形象。她的第二本生活隨筆集《旗袍時尚情畫》收錄了30餘篇文字、近150幅畫作及若干圖片,既用大量各色各樣的旗袍女子圖像展現了上世紀中國女性的日常生活場景和豐富、寧靜、平和的生活狀態,亦切入當下生活的熱點話題,關注現代人的旗袍情結和生活思考。
陸梅筆下的民初女子,嬌、雅、柔、韻,顧盼生姿;她創造的時尚女性,俏、亮、脫、酷,宜古宜今。她將詩意與日常巧妙融合,畫作中縈繞著一股特別的東方韻味,帶來一種令人嚮往的審美體驗。
跟隨陸梅的畫筆,品味旗袍時光,相信你會愛上這種延續至今的美。
名人推薦
她筆下的女子形象生動、形神兼備,寥寥數筆卻畫出了骨子裏的女人味。什麼是地道的女人味,在我看來便是感性、靚麗、任性而又迷茫,加一點點慵懶和不自知的天真。——张欣, 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冷靜觀察、 熱情繪畫、幽默文字、平實生活、自在靈魂、新鮮活力、誠懇態度,這就是陸梅。我曾力薦她第一本書,這第二本書我同樣舉雙手奉上。陸梅,活出了最真實的自己。——曹雪,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导; 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原院长;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团队的负责人, 广州首个城市形象标志设计者
陸梅,自帶她的腔調。這本書讓我看到了另一個她,她的豐富性和多面性,比如她聊旗袍,她拉扯進的其實是當下時尚;而說時尚,她切入的是生活的態度。但她的畫,一如既往,是那麼性感、優雅、溫暖、動人。——黄佟佟, 作家、资深媒体人、“董小姐和黄小姐”公眾号联合创始人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旗袍時尚情畫的圖書 |
 |
旗袍時尚情畫 作者:陸梅 出版日期:2023-11-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旗袍時尚情畫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陸梅
畫家。
廣州美術學院服裝設計專業畢業,廣州美術學院藝術碩士,意大利米開朗基羅藝術學院藝術管理在讀博士。
創作以女性為主題,尤其擅長描繪中國旗袍時期的女子,別具一格,深情唯美而時尚,獲得當下時代女性的極度喜愛。
作品入選意大利電影節藝術展、意大利薩萊諾雙年展、意大利“永恆藝術”等國際藝術展覽,在意大利舉辦“東方女人”個展巡展;作品多次入選國家級展覽:第十三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綜合畫種·動漫作品展、全國首屆動漫展、全國首屆插畫師扶持計劃展,參與“變相”跨界藝術展、“漫步邊際”當代跨界藝術大展、首屆廣東省高校美術作品學院雙年展、首屆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美術作品展、第七屆藝術廣東國際收藏品及藝術品博覽會等,畫作被眾多藏家收藏。
出版暢銷書《旗袍時尚情畫》、 《衣櫥裏的小風月》。
陸梅
畫家。
廣州美術學院服裝設計專業畢業,廣州美術學院藝術碩士,意大利米開朗基羅藝術學院藝術管理在讀博士。
創作以女性為主題,尤其擅長描繪中國旗袍時期的女子,別具一格,深情唯美而時尚,獲得當下時代女性的極度喜愛。
作品入選意大利電影節藝術展、意大利薩萊諾雙年展、意大利“永恆藝術”等國際藝術展覽,在意大利舉辦“東方女人”個展巡展;作品多次入選國家級展覽:第十三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綜合畫種·動漫作品展、全國首屆動漫展、全國首屆插畫師扶持計劃展,參與“變相”跨界藝術展、“漫步邊際”當代跨界藝術大展、首屆廣東省高校美術作品學院雙年展、首屆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美術作品展、第七屆藝術廣東國際收藏品及藝術品博覽會等,畫作被眾多藏家收藏。
出版暢銷書《旗袍時尚情畫》、 《衣櫥裏的小風月》。
目錄
01|喝得高貴 聊得八卦 002
02|有一種顏色 她自帶情話 010
03|愛一個人最瘋狂的方式 022
04|怎樣的姿勢成就最高境界 030
05|中國式性感的背後 040
06|民國時代的那些生無可戀 052
07|優雅的壓力 062
08|高級臉必備短髮的潮與嘲 072
09|明亮的星 082
10|不負好時光 090
11|那一段「嫵媚」的平胸時光之下的內衣 098
12|蕉葉千香 小團圓 110
13|用最快的速度經營慢生活 120
14|烤麩、剁辣椒和五柳炸蛋 128
15|一團矛盾 134
16|何必歲月靜好,你本風韻猶存 142
17|擼清民國旗袍 152
18|穿旗袍那些事兒 162
19|生命是時時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170
20|活在一張白紙上 176
21|一別兩寬 各生歡喜 182
22|我們為什麼迷戀太太的客廳 190
23|且慢 198
24|去趟民國 204
25|江南無所有 聊贈一枝春 214
26|昔日新女性 224
◎ 附 記
01|浮生若夢 速記下江南 240
02|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260
03|旗袍迷媽媽們十大經典拍照POSE 270
04|我的信仰是孤獨 280
◎ 後 記
旗袍 女人的最愛One Piece 292
02|有一種顏色 她自帶情話 010
03|愛一個人最瘋狂的方式 022
04|怎樣的姿勢成就最高境界 030
05|中國式性感的背後 040
06|民國時代的那些生無可戀 052
07|優雅的壓力 062
08|高級臉必備短髮的潮與嘲 072
09|明亮的星 082
10|不負好時光 090
11|那一段「嫵媚」的平胸時光之下的內衣 098
12|蕉葉千香 小團圓 110
13|用最快的速度經營慢生活 120
14|烤麩、剁辣椒和五柳炸蛋 128
15|一團矛盾 134
16|何必歲月靜好,你本風韻猶存 142
17|擼清民國旗袍 152
18|穿旗袍那些事兒 162
19|生命是時時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170
20|活在一張白紙上 176
21|一別兩寬 各生歡喜 182
22|我們為什麼迷戀太太的客廳 190
23|且慢 198
24|去趟民國 204
25|江南無所有 聊贈一枝春 214
26|昔日新女性 224
◎ 附 記
01|浮生若夢 速記下江南 240
02|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260
03|旗袍迷媽媽們十大經典拍照POSE 270
04|我的信仰是孤獨 280
◎ 後 記
旗袍 女人的最愛One Piece 292
序
序一
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
陸梅又要出新書了,真為她高興。
說真的,我的確素來不答應給人寫序,就是自己的書也是自序,不過給陸梅的新書寫序卻是我的榮幸。一是我超級喜歡才女,二是我用過她無數幅畫作自己文章的插圖,也欠她的人情。
我喜歡欠朋友的人情,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為朋友做點什麼。
不認識陸梅的時候,就喜歡她的畫。
她筆下的女子形象生動、形神兼備,寥寥數筆卻畫出了骨子裏的女人味。什麼是地道的女人味,在我看來便是感性、靚麗、任性而又迷茫,加一點點慵懶和不自知的天真。
所以我想像中的陸梅是個高冷的女孩,恃才傲物,不好相處。
但又才華橫溢,不容忽視。
認識陸梅以後,我對她的認識完全是另一個極端。
首先就是她不極端,甚至是一個不自信的女孩,無論你怎麼誇她好,她都覺得自己不夠好;無論你怎麼給她加油打氣,她都是一臉茫然。別的女孩子,若有她一半的才華,肯定要上天了。
陸梅不是,她真的是超級謙和。
而且遇到她信任的人,她的內心完全不設屏障,沒有防火牆。
第一次我們深聊居然就可以淚眼相望,因為她太真誠了,會讓你的情感在不知不覺中淪陷。
她不僅謙和,而且謙讓。
據我所知,她並不是很有錢,可是她一點都不貪財,為人處世毫無貪念,反而特別替人着想,所以跟她相處完全是零壓力、零負擔。
許多人會覺得說人論事,你為何總在強調品格,我們又不是選道德模範。然而朋友,任何一個藝術家都離不開做人的基本尺度,品格恰恰是這個人能走多遠的底色,至少與才華一樣重要。
品格也決定了品位。
陸梅的審美品位毋庸置疑,我見過的穿得亂七八糟的人很多,而陸梅的個人風格特別有細節,她的服飾無論顏色、面料,還是樣式、做工,永遠是並不扎眼卻精緻優雅,並且保有淡淡的才女餘味。
終於,我可以說到陸梅的畫作了。
我知道陸梅希望我通篇多談她的畫作,其實不然。藝術作品這個東西是見仁見智的,若與伊無緣,說到天上去也是白搭;而品行確是一個人行走江湖的通行證,是我們認識一個畫家的窄門。
我喜歡她的畫,只能說明我們是有緣人。
自我的文章裏配了她的圖,我感覺自己的文字都活了起來。而且它們被許多讀者稱讚,成為絕配。我真是從心底感謝她。
這一次她的新書 《旗袍時尚情畫》即將面市,比較搶眼的主題是民國旗袍裏的女人,那種美麗、輕盈、淡雅和漫不經心的姿態,猶如唐詩中的「微暖」境界 ——竹窗聞風而動,疑是舊日的朋友到來。而恰恰是陸梅這樣一個有一點迷糊的女孩,竟然有着超常而敏銳的「穿越」能力,捕捉到她從未經歷過的時代的風情,留下那個時代最後的遺韻和神采。
在一個狂熱競爭、追求成功的時代,我們已經習慣了爭先恐後的節奏、粗枝大葉的交往、急功近利的選擇,對於慢和美的理解僅停留在概念上,然而這便是陸梅和她畫作的價值所在。
當你感受到一種別樣的微風和清流,相信我,那邊是陸梅老師的本意——風雨聲連連,似是故人來。
是為序。
張欣
作家、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序二
在香港的博物館工作多年,退休後放慢腳步,四處走走,接觸不一樣的人間情物。日子算是平淡,但也偶遇驚喜。
逗留在英倫十七世紀宅院期間,發現廚房一角被人遺忘了的「中國風」木櫃,上有一列仕女圖,一下子我思鄉了!流連在美國小鎮古董店某天,又給我看到民初月份牌,與旗袍美女四目交投,魂魄瞬即飛去上海的 1930 年代——我惦念的旗袍黃金歲月。
旗袍可說是我與陸梅女士結緣的橋樑,2018 年我為香港文化博物館撰寫《百物一天 — 香港 1935》 ,這是一部以歷史為背景而創作的「文博小說」 。當時我正為物色插畫師而煩惱,幸運地遇上陸梅,雖然我倆分隔港粵兩地,但一拍即合。陸梅用她的神來之筆完完全全地把我所構思的人、物、景發揮得淋漓盡致,書中女角們的旗袍式樣更成為了我與陸梅的熱話。
興奮期待陸梅的《旗袍時尚情畫》在港面世。陸梅筆下的民初女子,那種嬌、雅、柔、韻,一舉手,一投足,顧盼生姿。陸大姐的美人又是宜古宜今,她創造的時尚女性,那種俏、亮、脫、酷,帶領讀者穿梭時空之際,又開啟了嶄新的生活體驗。
現今網上資訊排山倒海,對我來說代替不了一書在手那種實在兼愉悅的滿足感。陸梅的畫冊淡淡輕筆,濃濃暖意,圖文並茂,正是你我好收藏之佳作。
司徒嫣然
前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
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
陸梅又要出新書了,真為她高興。
說真的,我的確素來不答應給人寫序,就是自己的書也是自序,不過給陸梅的新書寫序卻是我的榮幸。一是我超級喜歡才女,二是我用過她無數幅畫作自己文章的插圖,也欠她的人情。
我喜歡欠朋友的人情,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為朋友做點什麼。
不認識陸梅的時候,就喜歡她的畫。
她筆下的女子形象生動、形神兼備,寥寥數筆卻畫出了骨子裏的女人味。什麼是地道的女人味,在我看來便是感性、靚麗、任性而又迷茫,加一點點慵懶和不自知的天真。
所以我想像中的陸梅是個高冷的女孩,恃才傲物,不好相處。
但又才華橫溢,不容忽視。
認識陸梅以後,我對她的認識完全是另一個極端。
首先就是她不極端,甚至是一個不自信的女孩,無論你怎麼誇她好,她都覺得自己不夠好;無論你怎麼給她加油打氣,她都是一臉茫然。別的女孩子,若有她一半的才華,肯定要上天了。
陸梅不是,她真的是超級謙和。
而且遇到她信任的人,她的內心完全不設屏障,沒有防火牆。
第一次我們深聊居然就可以淚眼相望,因為她太真誠了,會讓你的情感在不知不覺中淪陷。
她不僅謙和,而且謙讓。
據我所知,她並不是很有錢,可是她一點都不貪財,為人處世毫無貪念,反而特別替人着想,所以跟她相處完全是零壓力、零負擔。
許多人會覺得說人論事,你為何總在強調品格,我們又不是選道德模範。然而朋友,任何一個藝術家都離不開做人的基本尺度,品格恰恰是這個人能走多遠的底色,至少與才華一樣重要。
品格也決定了品位。
陸梅的審美品位毋庸置疑,我見過的穿得亂七八糟的人很多,而陸梅的個人風格特別有細節,她的服飾無論顏色、面料,還是樣式、做工,永遠是並不扎眼卻精緻優雅,並且保有淡淡的才女餘味。
終於,我可以說到陸梅的畫作了。
我知道陸梅希望我通篇多談她的畫作,其實不然。藝術作品這個東西是見仁見智的,若與伊無緣,說到天上去也是白搭;而品行確是一個人行走江湖的通行證,是我們認識一個畫家的窄門。
我喜歡她的畫,只能說明我們是有緣人。
自我的文章裏配了她的圖,我感覺自己的文字都活了起來。而且它們被許多讀者稱讚,成為絕配。我真是從心底感謝她。
這一次她的新書 《旗袍時尚情畫》即將面市,比較搶眼的主題是民國旗袍裏的女人,那種美麗、輕盈、淡雅和漫不經心的姿態,猶如唐詩中的「微暖」境界 ——竹窗聞風而動,疑是舊日的朋友到來。而恰恰是陸梅這樣一個有一點迷糊的女孩,竟然有着超常而敏銳的「穿越」能力,捕捉到她從未經歷過的時代的風情,留下那個時代最後的遺韻和神采。
在一個狂熱競爭、追求成功的時代,我們已經習慣了爭先恐後的節奏、粗枝大葉的交往、急功近利的選擇,對於慢和美的理解僅停留在概念上,然而這便是陸梅和她畫作的價值所在。
當你感受到一種別樣的微風和清流,相信我,那邊是陸梅老師的本意——風雨聲連連,似是故人來。
是為序。
張欣
作家、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序二
在香港的博物館工作多年,退休後放慢腳步,四處走走,接觸不一樣的人間情物。日子算是平淡,但也偶遇驚喜。
逗留在英倫十七世紀宅院期間,發現廚房一角被人遺忘了的「中國風」木櫃,上有一列仕女圖,一下子我思鄉了!流連在美國小鎮古董店某天,又給我看到民初月份牌,與旗袍美女四目交投,魂魄瞬即飛去上海的 1930 年代——我惦念的旗袍黃金歲月。
旗袍可說是我與陸梅女士結緣的橋樑,2018 年我為香港文化博物館撰寫《百物一天 — 香港 1935》 ,這是一部以歷史為背景而創作的「文博小說」 。當時我正為物色插畫師而煩惱,幸運地遇上陸梅,雖然我倆分隔港粵兩地,但一拍即合。陸梅用她的神來之筆完完全全地把我所構思的人、物、景發揮得淋漓盡致,書中女角們的旗袍式樣更成為了我與陸梅的熱話。
興奮期待陸梅的《旗袍時尚情畫》在港面世。陸梅筆下的民初女子,那種嬌、雅、柔、韻,一舉手,一投足,顧盼生姿。陸大姐的美人又是宜古宜今,她創造的時尚女性,那種俏、亮、脫、酷,帶領讀者穿梭時空之際,又開啟了嶄新的生活體驗。
現今網上資訊排山倒海,對我來說代替不了一書在手那種實在兼愉悅的滿足感。陸梅的畫冊淡淡輕筆,濃濃暖意,圖文並茂,正是你我好收藏之佳作。
司徒嫣然
前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