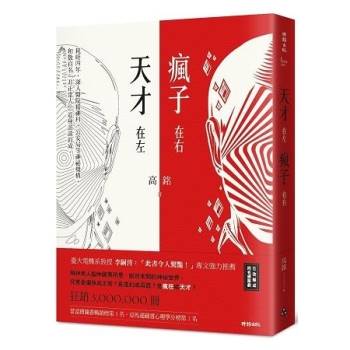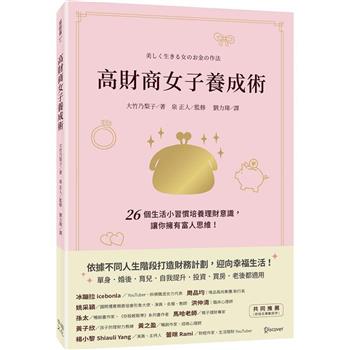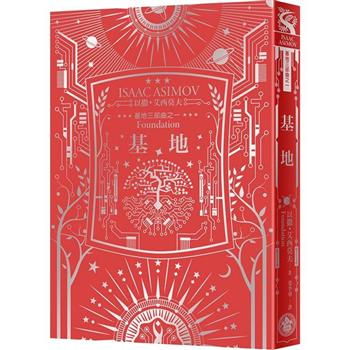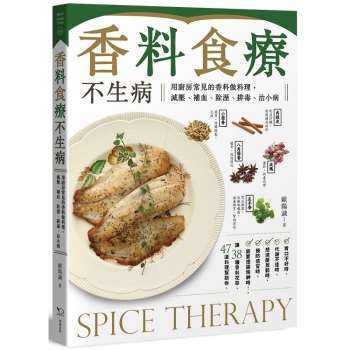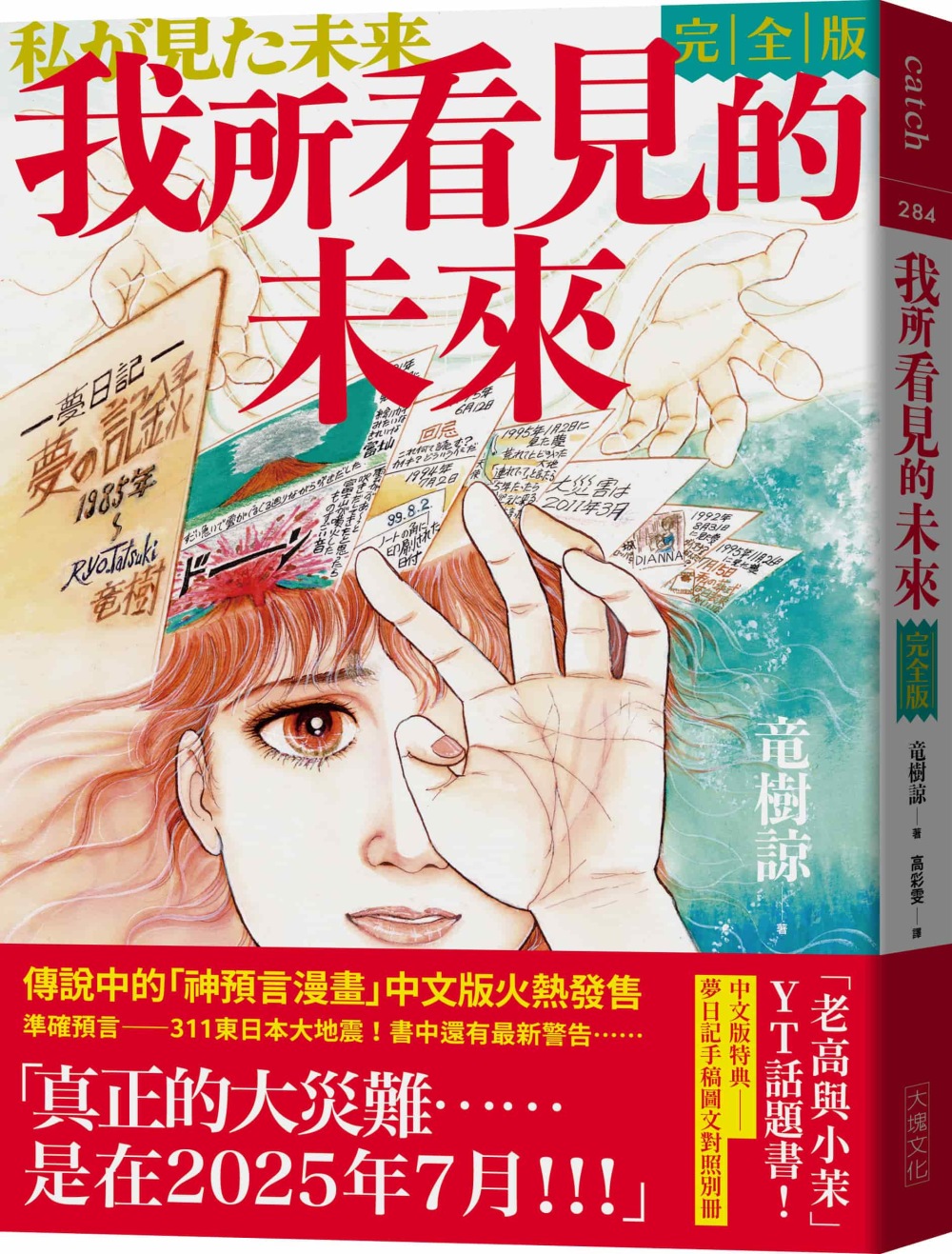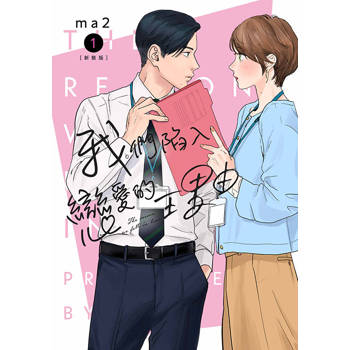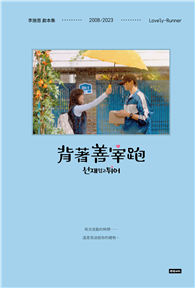前言
2023年5月,乘前作《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餘緒,假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舉行了一場講座,講者包括中國科學院的馮錦榮教授、香港大學建築系的王維仁教授和筆者本人,主題是「從古都選址看風水格局與王權文化」,馮教授和王教授分別從考古和建築角度解釋風水源流,筆者則談古都建設的風水。講座最後的問答環節,主持李安女士問筆者,古都的主人都是皇帝,可我們不過一介平民,古都的風水跟我們有關嗎?
筆者簡略回應後,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時代不同了,老祖宗的智慧放諸今日社會,是否還適用?應該怎樣理解和傳遞?於是開始構思寫這本書,作為前作的延伸,也為傳統風水嘗試賦予現代意義。
前作中提及,歷史上八大古都從來不止是一組組讓人遮風擋雨的硬件建築,它的選址和佈局上儼如一本無字地書,中間繼承著包括天文地理、儒家和天命史觀的多重文化積澱,是過去皇帝創造於地表的人文景觀。本書就嘗試從現代住宅的角度,解讀其中書單,有什麼古都的原則可以合理延伸到今天。
誠然,兩者在最基本的層面——宮城和民居的主人身份——上存在著巨大的落差。當住宅的主人是皇帝時,建設的是宮城,確立的是王權。疑古派史學家顧頡剛說出了政治現實:「學術性的東西是皇帝所不需要的,一定要插入對於皇帝有利的東西方能借得政治上的力量。」
我們熟悉的紫禁城,正正繼承了中國王朝語言的傳統。憑藉掌控天下的話語權,皇帝築城不受任何限制,包括在選址上、佈局上、裝潢上注入展示王權的文化符號,中軸線、九開間、前朝後寢、左祖右社等刻意直觀式的鋪排,組成一套帝王邏輯,流風所至,積澱為患,叫你不得不服膺和敬畏,「其設計的指導思想,就是要突出表現帝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達到鞏固王權統治的目的。」
至於一般民居,你多富有也好,王權的色彩(尤其在古代)必須完全抹去,好好安分守己,除非你得到像乾隆之於和珅的包庇,對大宅逾制睜一眼閉一眼,否則就會被視為 「逆臣」,賜以可殺頭的僭越罪。在統治和禮制層面而言,宮城和民居無法相提並論。然而,兩者的擇居條件是否就全無兼容之處?恐怕又未必。
宜居之地不分帝王與平民
在居住的層面,宮城和民居卻有另一種關係。儘管宮城的選址和佈局是一種複雜的宇宙圖式,但一點不離地,風水用於宮城,不代表一些基本原則不能應用於尋常民居。中國一直沿襲一套化家為國的觀念,權力由一家一姓把持,宮城既是皇帝治下邦國的表徵,也是皇帝躬居的家園。筆者多次強調,風水的初念到終極原則,只是如何適應大自然規律來尋找宜居之地,這點不管身份是帝王或平民並無二致。
東漢劉熙《釋名》稱:「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平時說的選擇,原來就是選宅。出於人類求生本能,居所必然選在宜居之地興建。風水是早期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反應,那中國的大自然環境有什麼特色?其一是山和水特多。巨大山脈如喜馬拉雅山、崑崙山、唐古拉山、天山、太行山、秦嶺等多達十條,主要分佈在中國西面和北面;而山脈之間也發源出眾多大型和中型河流,據統計多達45,000多條(小河流更不計其數),風水作為應對環境的生存之道,山勢、水法理論應運而生。到王朝制度確立,身為天下共主的統治者,便將這套強調自利和安穩的理論據為己有,用於都城選址和佈局,是為風水之大用,強調「夫地理之大,莫先於建國立都」(《地理人子須知》)。
但是,中國的山和水並非統治者專用,由之孕育而來的風水既為建都考量,也可施之於民間。風水講龍脈,講格局,大至國都固然要多加參詳,小至一屋一宅亦然。唐代《撼龍經》稱:「大為都邑帝王州,小為郡縣君公侯」;明朝《地理人子須知》續謂:「大聚為都會,中聚為大郡,小聚為鄉村、陽宅及富貴陰地(即墳墓)」,反映宮城和民居要求一致,從大格局中按次而下,尋找宜居之地。
例如為配合中國的氣候地貌,歷來宮城方位幾乎都是坐北向南(僅南宋臨安城例外),才得享冬暖夏涼。而北京的四合院也是同一取向,到香港我們也常說「千金難買向南樓」,甚至本港天文台網頁也有談天氣風水,用氣象學角度解釋向南的好處。風水的本義植根於人的本性之中,出於一種純個人感受,我們毋須上調到哲學或者帝王學層面,皇城與民居欲求一致,只是規模有別而已。
大自然和人的對話
人要生存,必須要和大自然共存,但兩者地位並不對等,喜怒無常的大自然一說不,人便要遭受無情的驅逐——洪水、旱災、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卑微的人類沒有討價還價能力。心裡越恐懼,越渴望穩定和秩序。為了生存,只好嘗試順應大自然運作的規律,想方設法,收集許多不同個案,觀察、比較、思考,然後作出結論。所有事物都有常規和秩序,風水理論就是古代的研究成果,是一種集體智慧和群眾經驗的累積,類似今天所講的大數據下的產物。跟大自然關係密切的風水,等如是中國大自然數據的調研報告,五行中指北方寒冷,南方溫暖,西方主肅殺,東方利生長,我們將之融合中國地理氣候,馬上心領神會。
而且中國的皇帝和平民,彼此分享著相同的族群精神和人文個性,基因一脈相承,詮釋術數符號的內涵一致,沒有文化差異問題;而且處於同一疆域,更不存在同一座崑崙山,一在中國西北,一在印度東北的山川方位落差,地理標識相同,兼融風水原則毫不違和,只要稍作調整,完全存在共融空間。
從宮廷到民間
萌芽期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二十世紀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他認為唐宋之際是中國中古史的結束,近世史的開端。中國建築學者傅熹年亦稱唐宋是「中古都城向近古都城演變的一個轉折點」。
風水的發展恰巧亦然——從在朝文化延伸成在野文化。唐代以前,熟悉天文曆法以至術數的能人異士只在朝廷司天台(後代稱欽天監)任職,相關文字記錄亦只僅供國家記錄和參照,民間無法得窺。原因不難理解,風水關乎自身利益,當中也有相當厭勝成分,更關乎中軸線等宣示正統地位的天命元素,是王權的象徵,不容分沾,必然一己獨攬,後來出現制度更替和政治變局,情況才逐步逆轉。隋唐開科取士,以儒家經典作為考試題目,《周易》與《尚書》、《詩經》、《禮記》和《春秋》並列五經之一,熱衷功名的讀書人,為應付科舉考試,開始對術數源頭——《易經》多作研究。有了易學基礎,學習風水容易得心應手,讀書人視之為與琴棋書畫相同檔次的風雅修養。影響所及,當時風水大師輩出,楊筠松、張遂、曾文辿、李淳風、袁天罡等互爭雄長,並各有名著傳世;堪輿作為風水的代名詞也是唐代以後的事,許慎《說文解字注》:「堪,天道;輿,地道。」簡單來說,堪輿就是天地間的道理,由純具象的自然描述(風和水),正式提升到理論層面。
政治上,唐朝中葉以後,發生黃巢之亂,建制逐步破局,據《南安府志》記載,原本掌「靈台地理事」的光祿大夫楊筠松逃離宮城長安,到江西安頓,向曾文辿及劉江東等人傳授地理之術。楊筠松等人由朝廷命官搖身一變,成為 「公共知識分子」,自此風水從宮廷流落民間,開始流傳,派別漸多,竟至其時已經有「百二十家渺無訣」之歎。經歷五代十國後,到宋代,民間風水逐漸大盛。
蓬勃期
經歷唐代醞釀,到宋代民間風水蔚然成風,與唐代最大的分別,前者視風水為副業,或只是文人間的一種談資,後者則是一種專業,討生活之資本。北宋熙寧朝宰相王安石估計,當時執業的風水師有近萬人,在《清明上河圖》一景中,有掛起寫上「神課」、「看命」、「決疑」的直幡,大街大巷給人算起命來。原因之一,是自唐代開科取士後,士人競相投身科場考取功名,不過僧多粥少,落第者反正有易學基礎,不少改靠算命謀生,碰巧社會需求正殷,讀書人不愁出路,紛紛以風水師自居。一直發展下去,儘管經歷改朝換代,到明清時候,民間看風水的風氣越演越烈,各種理論耳口相傳,尤其對龍脈等說深信不疑,據當時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觀察:「選擇修建公共建築或私宅的地點以及埋葬死人的地點時,他們是按照據說地下的特殊龍頭或龍尾或龍爪來研究地址的。他們相信不僅本身,而且全城、全省和全國的運道好壞全要看這些地域性的龍而定。」
看風水不單成為全民共識,更是官僚抗衡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的手段(詳見後說)。到清末帝制崩坍,對風水的最大影響,並非歸於沉寂,而是令其學理更難定於一尊,再無官方制約下,流播程度更甚,風水的派別也百花齊放,各師其說,演變成今日面貌。
簡單交代過自唐朝以後民間風水的發展,便知道今日有人熱衷看風水,不過是沿襲過去的人文基因,本書將以往屬於宮城的風水原則應用於民居,也只是延續傳統而已。
四神塑造置中觀念
從宮城到民間,風水上存在著怎樣合乎邏輯的演化,是筆者在本書中必須梳理和表達的題旨。舉一個例子,不管懂不懂風水,信不信風水的人,對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術語總不會陌生,四者為四神或四靈。前作提及中國八大古都建設強調大局觀,擇地必須四神俱全,除了出於拱衛需要,杜絕外界窺伺外,最重要一點,四神代表的東南西北四方,所圍繞而成的空間確立了「中」的存在。「中」具有中央和核心的意味,代表著權力的象徵,對中國古代集權制國家而言,這點尤其重要,天下共主,必然居中而立,得四神包圍才能製造這個「置中」條件。早在距今4,300年前,當時王者已經躬自進行「圭表測影」,通過「圭尺」來找尋「地中」,以對應天之中軸,馮錦榮教授稱之為:「集天文觀象、授時功能與惟王建制於一身之禮儀性活動的王者禮器」(見前作第三頁)。從國家的層面,這點不難理解,那普通人是否不必理會?答案當然是不。從個人的層面,「置中」同樣重要。「中」是一種觀察東西南北的視點,是本體,是自我。不管置身任何環境,每個人必然從自身角度審視四周,衡量自己與環境的關係,找出自己的需求,而英文news(消息)的字源,一說就是位處中心,收集來自東西南北的事情,由此判斷自身狀況,如何作出應對——例如對居住環境的訴求。
無論陰宅陽宅,風水立穴有一個術語名為「天心十道」,就是以前後左右四個方位的山為對稱座標,劃出一個十字,那個十字中間的交滙點,即立穴所在。所以,若然四神不全或者完全欠缺,格局不當,穴即不能定,本體和自我位置也無從確立,感覺若有所失,這也是為什麼北宋定都一馬平川的汴京後,宋太祖趙匡胤惴惴難安,需派重兵30萬連營設衛,駐守京師一帶。放之於民居,人同此心,始終期待四神俱在,好寄託安穩。
下一步,我們進而審視人與建築物的關係。按諸中國人的宇宙觀,建築物本身是人與自然之間一個中介物。人仰觀天地,經營宅居環境,建構建築物作為順應自然規律的載體,因此了解建築物的形制,等如了解大自然的形態。人因宅而立,宅亦因人而存,兩者存在微妙的共生關係。房屋灌注了人的主觀意識和期望,宮城和民居在本質上並無分別,唯順應自然得以宜居而已。建築師說風水是「認知建築最合適地點的時空規律,地理景觀的評價體系」。
於古有據
有別於一般只導以化解之道,筆者希望能從歷史和文化層面解讀風水源流和應用的根據,讓大眾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提供一份有助提高風水信用評級的信貸報告。
今天風水師稱開門見窗,直視屋外景物為「穿」,認為不能聚氣,容易漏財,甚至災病連連云云,化解之道有說在玄關位豎一屏風遮擋,又或落簾遮光等等。然而,只有建議,解釋欠奉,容易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它有舊例可循嗎?它有歷史沿革嗎?若有,又如何引伸而來?
筆者以為,考諸歷史,講求聚氣的原則在北魏洛陽城和明清紫禁城早有先例,各座城門之間不會直通,寧願增加工序和犧牲效率,總要左拐右轉才能抵達,背後的考量即在於不喜穿。穿則易洩,氣便不能聚,有違藏風聚水的原則,甚至城內河流也要九曲十三彎,目的相同。宏觀在宮城,微觀在民戶,分別在於規模而已。
而其實,這裡還涉及一種更深層的意義——出於中國人偏向內歛,注重隱私的個性,表現在生活環境之上,選擇了開門不見門,開門不見窗的建築形制。1934年,中國著名建築師、建築史學家梁思成來到浙江,考察武義樊嶺腳村民居時,有感而發說:「建築總是滲透著民族精神。」風水與中式建築關係密切,它的一些認知,是連串載負著中國文化意識的符號。風水到底是以人為本的學問,而人的共同訴求,就是尋找一片宜居之地,不管歷經多少年,這訴求一仍舊貫。風水理論累積了先民智慧、前賢心血,也蘊藏古代天文地理、儒釋道內容,經歷時間的洗禮,有沉厚的積澱和反覆的勘誤,才能流傳到今天。風水,就是在簡單的訴求中蘊藏複雜的原理,具有探討的價值。
正正在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令風水有別於天馬行空的藝術創作,它可以與時並進,但不容許顛覆和革命,一些純屬個人臆猜的建議,既於古無據,亦欠合理推論基礎,就應該受到質疑,不能因為術者有如簧巧舌或知名度高就得以倖免。為什麼只要信,不要問?
至於讀者將本書視作風水文化探索或選宅靈感,其實都不重要。重要在一直以來,不要問、只要信的風氣應該要改變,若然經得起論證,何須避忌?
好了,我們現就回顧過去,用今人思維連接遠古初心,談風水的現代詮釋。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2——現代詮釋的圖書 |
 |
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 2: 現代詮釋 作者:梁冠文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4-09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2——現代詮釋
時至今日,許多人視風水為個人趨吉避凶,追求榮華富貴的手段,令風水的價值相當世俗。然而,若我們願意花一點時間深耕細作,檢視風水的初念和原則,你會發現,中國風水呈現的視野,遠比一般人所想的遼闊;它埋藏的內涵,也出乎意料的深邃。
前作《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以中國八大古都為主角,分析其選址和佈局,中間繼承著包括天文地理、儒家和天命史觀的多重文化積澱,是過去皇帝創造於地表的人文景觀。時代轉變,老祖宗的智慧放諸今日社會,是否還適用?應該怎樣理解和傳遞?
儘管宮城的選址和佈局是一種複雜的宇宙圖式,但一點不離地,風水用於宮城,不代表一些基本原則不能應用於尋常民居。筆者多次強調,風水的初念到終極原則,只是如何適應大自然規律來尋找宜居之地,這點不管身份是帝王或平民並無二致。本書先由宏觀的大局環境出發,順次收窄視野,到屋外環境道路,以至室內佈局和擺設,看看有什麼古都建設的原則可以合理延伸到現代住宅。
名人推薦
麻省理工學院S. C. Fang中國語言與文化職業發展系教授特里斯坦.G.布朗(Tristan G. Brown)
英國皇家院士及國際中國哲學會青年學者論文獎得主李宗鴻
作者簡介:
梁冠文
作家及策展人。著作包括《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暗算滿清皇帝》、《御用捉刀人——韓非》、《認識中國系列4——飲食文化》等;策展項目有《周大福九十周年展覽—一件首飾 一個時代》、《盛世壁藏——唐代壁畫文化特展》、杭州文博會《香港館》、深圳文博會《香港創意館》及香港《文創無界》延展等。
作者序
前言
2023年5月,乘前作《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餘緒,假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舉行了一場講座,講者包括中國科學院的馮錦榮教授、香港大學建築系的王維仁教授和筆者本人,主題是「從古都選址看風水格局與王權文化」,馮教授和王教授分別從考古和建築角度解釋風水源流,筆者則談古都建設的風水。講座最後的問答環節,主持李安女士問筆者,古都的主人都是皇帝,可我們不過一介平民,古都的風水跟我們有關嗎?
筆者簡略回應後,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時代不同了,老祖宗的智慧放諸今日社會,是否還適用?應該怎樣理解和傳遞?於是開始構思寫...
2023年5月,乘前作《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餘緒,假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舉行了一場講座,講者包括中國科學院的馮錦榮教授、香港大學建築系的王維仁教授和筆者本人,主題是「從古都選址看風水格局與王權文化」,馮教授和王教授分別從考古和建築角度解釋風水源流,筆者則談古都建設的風水。講座最後的問答環節,主持李安女士問筆者,古都的主人都是皇帝,可我們不過一介平民,古都的風水跟我們有關嗎?
筆者簡略回應後,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時代不同了,老祖宗的智慧放諸今日社會,是否還適用?應該怎樣理解和傳遞?於是開始構思寫...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選址——周朝洛邑的啟示
第二章 大局觀——外閉內寬的桃花源記
第三章 直觀——融貫自然 直指本心
第四章 方位——坐北向南基因
第五章 屋型——從紫禁城到四合院
第六章 間隔——城門房門概念一致
第七章 陳設——厭勝古今傳承
第八章 內外六事——時代意義不同
後記
第一章 選址——周朝洛邑的啟示
第二章 大局觀——外閉內寬的桃花源記
第三章 直觀——融貫自然 直指本心
第四章 方位——坐北向南基因
第五章 屋型——從紫禁城到四合院
第六章 間隔——城門房門概念一致
第七章 陳設——厭勝古今傳承
第八章 內外六事——時代意義不同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