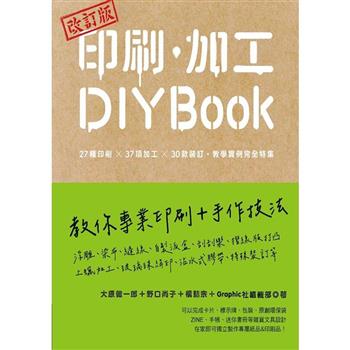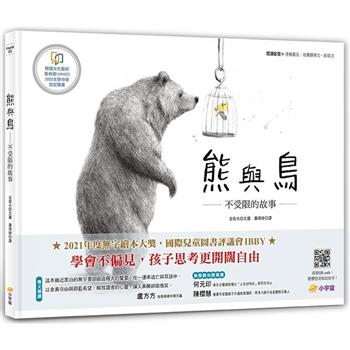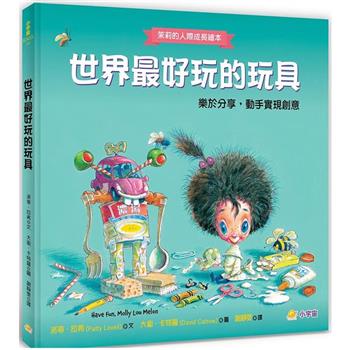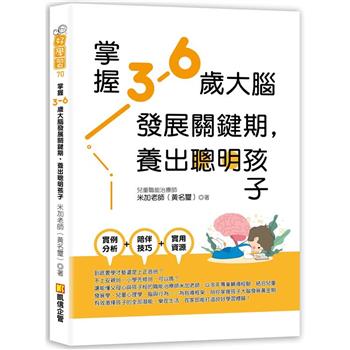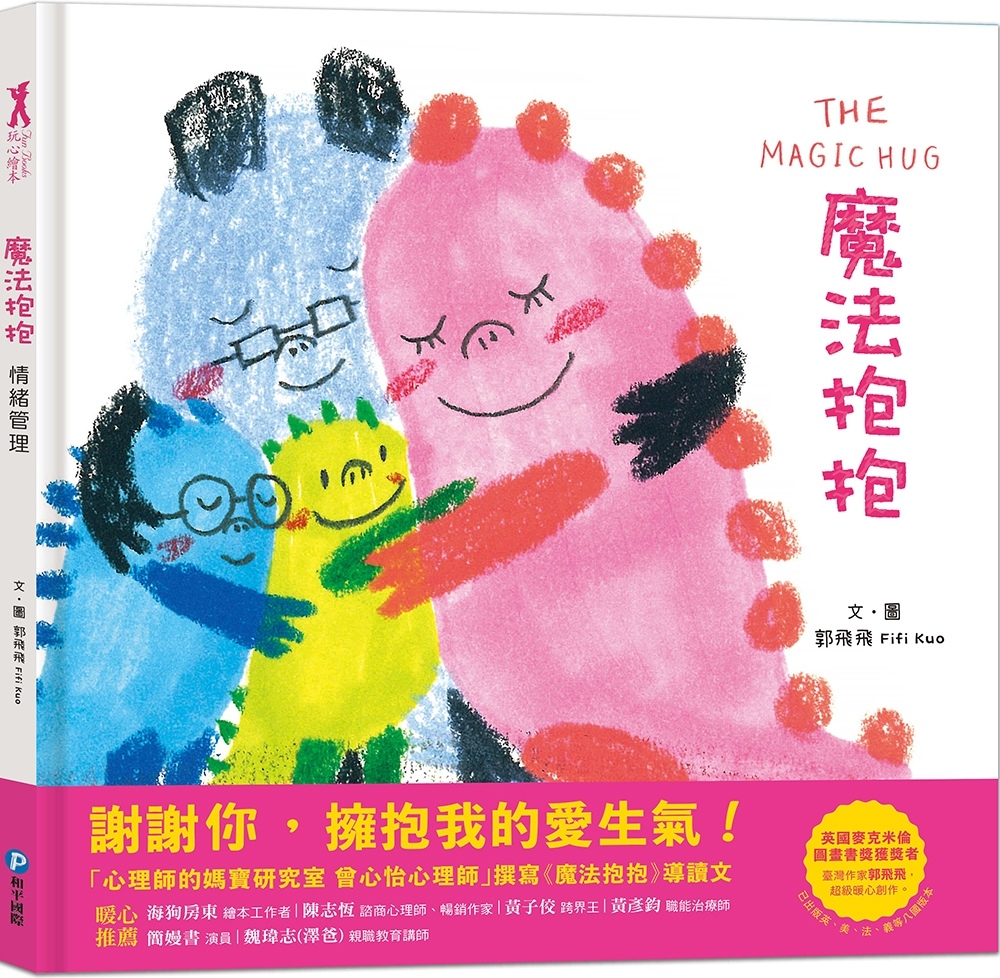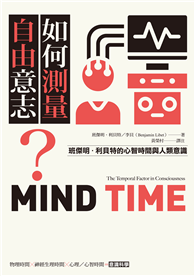本書精選七十二首唐詩名作,既注重對詩歌篇法、章法、句法的傳統分析,復以現代語言學角度,闡述時空結構、意象互動、語言特色等古代詩話難以言明的奧妙之處。以「縱」、「橫」兩大軸線組織架構,細心尋繹詩與詩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的關係,探究十三個不同主題的藝術特點,從而圓覽唐詩的發展。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蔡宗齊講唐詩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蔡宗齊講唐詩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蔡宗齊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榮休教授,著、編中英文學術書籍各十七種,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典詩歌、散文、文論及比較詩學。與袁行霈教授共同創辦杜克大學英文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已進入AHCI)。為嶺南大學創辦杜克大學英文期刊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並復辦和主編《嶺南學報》。與袁行霈教授共同主編哥倫比亞大學叢書How to Read Chinese Literature和博睿(Brill)叢書Chinese Texts in the World。2020年被美國學術期刊主編協會評選為傑出主編。古典詩歌方面的專著、編著,包括:《聲音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文新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如何讀中國詩歌:作品導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如何讀中國詩歌:詩歌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語法與詩境:漢詩藝術之破析》(中華書局〔北京〕,2021);《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詩歌模式與自我呈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蔡宗齊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榮休教授,著、編中英文學術書籍各十七種,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典詩歌、散文、文論及比較詩學。與袁行霈教授共同創辦杜克大學英文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已進入AHCI)。為嶺南大學創辦杜克大學英文期刊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並復辦和主編《嶺南學報》。與袁行霈教授共同主編哥倫比亞大學叢書How to Read Chinese Literature和博睿(Brill)叢書Chinese Texts in the World。2020年被美國學術期刊主編協會評選為傑出主編。古典詩歌方面的專著、編著,包括:《聲音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文新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如何讀中國詩歌:作品導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如何讀中國詩歌:詩歌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語法與詩境:漢詩藝術之破析》(中華書局〔北京〕,2021);《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詩歌模式與自我呈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目錄
序言 vii
開篇語 xii
律詩篇
五律氣象何以成 005
1杜甫〈春望〉 如何化無情為有情 007
2杜甫〈江漢〉 詩聖法寶之題評句 013
3杜甫〈登岳陽樓〉 一轉再轉,轉即是合 020
4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擬人只為找玩伴 025
5王維〈終南山〉 四個詩眼不尋常 028
6王維〈漢江臨眺〉 隱形的移步換景之法 032
七律何以自由縱橫 036
7杜甫〈詠懷古跡〉其三 詩聖絕技之草蛇灰線 038
8李商隱〈隋宮〉 別人怕用的虛字,我用 043
七律之爭誰第一 047
9王維〈積雨輞川莊作〉 七言不得減兩字才是真工夫 049
10沈佺期〈古意〉 樂府入律,何以稱雄 054
11崔顥〈黃鶴樓〉 歌行入律,何以爭勝 058
12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PK〈黃鶴樓〉為何失敗 062
13杜甫〈登高〉 當七律達到極致時 066
快詩、慢詩、意識流詩 072
14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沉鬱頓挫之外 073
15李商隱〈無題〉 結構不奇,枉稱無題 079
16李商隱〈錦瑟〉 現代意識流的鼻祖 083
絶句篇
以小見大之極致 091
17王之渙〈登鸛雀樓〉 固定機位,全方位動態視角 092
18祖詠〈終南望餘雪〉 僅憑通感妙句而登第 095
19柳宗元〈江雪〉 虛擬賓語接引盡善境界 097
20孟浩然〈春曉〉 化平常為神奇的章法 100
21王維輞川絕句三首 小景如何寫出超越時空的禪境 103
定點與動態的山水描寫 107
22杜甫〈絕句〉 固定機位,周覽天地 108
23張繼〈楓橋夜泊〉 意象濃密寫愁緒 111
24杜牧〈江南春〉 大景與小景,自然與人文 115
25徐凝〈廬山瀑布〉 東坡辣評之惡詩 118
26李白〈望廬山瀑布〉 不只遠看與近觀 120
27李白〈早發白帝城〉 寫快第一詩 122
山川異域、古今對比的書寫 124
28王之渙〈涼州詞〉其一 笛聲穿越的兩個時空 126
29王昌齡〈出塞〉其一 古今景物、戰事、悲情之疊加 128
30王昌齡〈從軍行〉其一 倒裝手法,代實為虛 130
31王翰〈涼州詞〉其一 頓與挫、起承轉合 133
32陳陶〈隴西行〉其二 蒙太奇結構與天人永隔之傷慟 136
33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如何做到言淺情深 138
34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跨越時空的雙向奔赴 142
35賈島〈渡桑乾〉 宦遊離心力PK思鄉向心力 144
36李商隱〈夜雨寄北〉 交錯時空的奇妙構思 146
懷古絕句:為何五言無法PK七言 148
37杜甫〈八陣圖〉 五絕懷古,詩聖難為 150
38杜甫〈武侯廟〉 陳述史事,難有精彩 152
39杜甫〈蜀相〉 七律懷古,遊刃有餘 154
40劉禹錫〈金陵五題〉 為何此詩讓白居易嘆為觀止 156
41杜牧〈泊秦淮〉 層層相扣寫茫然 161
古詩篇
詩仙層出不窮的結構創新 167
42李白〈月下獨酌〉 倒裝的組詩要怎樣讀 168
43李白〈將進酒〉 自說自演的戲劇結構 174
44李白〈古風〉其一 攝入文學史的詠懷 178
45李白〈行路難〉其一 結構起起落落來取勝 182
46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三重奏彰顯陰陽結構 184
47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 動靜、真幻相生的結構 188
杜甫古詩、律詩之比較 192
48杜甫〈夢李白〉其一 步步轉化、步步深入 193
49杜甫〈夢李白〉其二 角度多樣、聯聯不同 196
50杜甫〈天末懷李白〉 五律懷友的不同寫法 199
戰爭敘事的結構藝術 202
51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邊塞詩少見的陰柔美景 204
52高適〈燕歌行〉 盡顯陽剛本色的邊塞詩 206
53杜甫〈兵車行〉 樂府結構融入自我抒情 209
54杜甫〈新婚別〉 樂府結構抒情化又一式 213
55杜甫〈石壕吏〉 全知型的觀察敘述 216
文藝表演之描寫:剛與柔的完美呈現 219
56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熔多重為一爐 221
57白居易〈琵琶行〉(選段) 聲音的視覺想像 224
58韓愈〈聽穎師彈琴〉 琴聲掀起情感冰火兩重天 228
59韓愈〈調張籍〉 五言句組配成跳躍片段 231
陰柔之美的名篇是如何生成的 235
60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 線性結構為何引人入勝 236
61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鬼仙出沒的懷古之作 240
62白居易〈長恨歌〉 顛覆性的創新傑作 243
結語:與唐人三境說的對話 256
跋 263
開篇語 xii
律詩篇
五律氣象何以成 005
1杜甫〈春望〉 如何化無情為有情 007
2杜甫〈江漢〉 詩聖法寶之題評句 013
3杜甫〈登岳陽樓〉 一轉再轉,轉即是合 020
4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擬人只為找玩伴 025
5王維〈終南山〉 四個詩眼不尋常 028
6王維〈漢江臨眺〉 隱形的移步換景之法 032
七律何以自由縱橫 036
7杜甫〈詠懷古跡〉其三 詩聖絕技之草蛇灰線 038
8李商隱〈隋宮〉 別人怕用的虛字,我用 043
七律之爭誰第一 047
9王維〈積雨輞川莊作〉 七言不得減兩字才是真工夫 049
10沈佺期〈古意〉 樂府入律,何以稱雄 054
11崔顥〈黃鶴樓〉 歌行入律,何以爭勝 058
12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PK〈黃鶴樓〉為何失敗 062
13杜甫〈登高〉 當七律達到極致時 066
快詩、慢詩、意識流詩 072
14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沉鬱頓挫之外 073
15李商隱〈無題〉 結構不奇,枉稱無題 079
16李商隱〈錦瑟〉 現代意識流的鼻祖 083
絶句篇
以小見大之極致 091
17王之渙〈登鸛雀樓〉 固定機位,全方位動態視角 092
18祖詠〈終南望餘雪〉 僅憑通感妙句而登第 095
19柳宗元〈江雪〉 虛擬賓語接引盡善境界 097
20孟浩然〈春曉〉 化平常為神奇的章法 100
21王維輞川絕句三首 小景如何寫出超越時空的禪境 103
定點與動態的山水描寫 107
22杜甫〈絕句〉 固定機位,周覽天地 108
23張繼〈楓橋夜泊〉 意象濃密寫愁緒 111
24杜牧〈江南春〉 大景與小景,自然與人文 115
25徐凝〈廬山瀑布〉 東坡辣評之惡詩 118
26李白〈望廬山瀑布〉 不只遠看與近觀 120
27李白〈早發白帝城〉 寫快第一詩 122
山川異域、古今對比的書寫 124
28王之渙〈涼州詞〉其一 笛聲穿越的兩個時空 126
29王昌齡〈出塞〉其一 古今景物、戰事、悲情之疊加 128
30王昌齡〈從軍行〉其一 倒裝手法,代實為虛 130
31王翰〈涼州詞〉其一 頓與挫、起承轉合 133
32陳陶〈隴西行〉其二 蒙太奇結構與天人永隔之傷慟 136
33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如何做到言淺情深 138
34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跨越時空的雙向奔赴 142
35賈島〈渡桑乾〉 宦遊離心力PK思鄉向心力 144
36李商隱〈夜雨寄北〉 交錯時空的奇妙構思 146
懷古絕句:為何五言無法PK七言 148
37杜甫〈八陣圖〉 五絕懷古,詩聖難為 150
38杜甫〈武侯廟〉 陳述史事,難有精彩 152
39杜甫〈蜀相〉 七律懷古,遊刃有餘 154
40劉禹錫〈金陵五題〉 為何此詩讓白居易嘆為觀止 156
41杜牧〈泊秦淮〉 層層相扣寫茫然 161
古詩篇
詩仙層出不窮的結構創新 167
42李白〈月下獨酌〉 倒裝的組詩要怎樣讀 168
43李白〈將進酒〉 自說自演的戲劇結構 174
44李白〈古風〉其一 攝入文學史的詠懷 178
45李白〈行路難〉其一 結構起起落落來取勝 182
46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三重奏彰顯陰陽結構 184
47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 動靜、真幻相生的結構 188
杜甫古詩、律詩之比較 192
48杜甫〈夢李白〉其一 步步轉化、步步深入 193
49杜甫〈夢李白〉其二 角度多樣、聯聯不同 196
50杜甫〈天末懷李白〉 五律懷友的不同寫法 199
戰爭敘事的結構藝術 202
51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邊塞詩少見的陰柔美景 204
52高適〈燕歌行〉 盡顯陽剛本色的邊塞詩 206
53杜甫〈兵車行〉 樂府結構融入自我抒情 209
54杜甫〈新婚別〉 樂府結構抒情化又一式 213
55杜甫〈石壕吏〉 全知型的觀察敘述 216
文藝表演之描寫:剛與柔的完美呈現 219
56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熔多重為一爐 221
57白居易〈琵琶行〉(選段) 聲音的視覺想像 224
58韓愈〈聽穎師彈琴〉 琴聲掀起情感冰火兩重天 228
59韓愈〈調張籍〉 五言句組配成跳躍片段 231
陰柔之美的名篇是如何生成的 235
60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 線性結構為何引人入勝 236
61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鬼仙出沒的懷古之作 240
62白居易〈長恨歌〉 顛覆性的創新傑作 243
結語:與唐人三境說的對話 256
跋 263
序
序
我一直有這樣的構想:寫一部向廣大讀者介紹唐詩藝術,同時又有學術含金量的專著,這也是我對學術原創的執着追求的延伸。自從2008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如何閱讀中國詩歌:導讀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以來,在鑽研學術的同時,我一直孜孜不倦地開展推廣中國古典詩歌的工作,各種集體和個人項目也越做越大。首先是完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中國詩歌選集》系列(共三部),接着又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合作,於2023年出版此系列的兩部中文擴充版。從2022年開始,這項穿越英語、漢語世界的工程開始從書籍出版擴展到新媒體的傳播。2022年,我與美國十多位知名漢學家合作,推出五十六集的英文播客「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2023年推出三十四集中文視頻《唐詩之意境》;2024年3月,繼續推出九集中文視頻《唐詩之音韻》。無論是構思設計,還是具體的講解,無不源於我對原創的追求。我認為,做學術,不應該拘束於條條框框,應當有獨立的思想,敢於大膽發揮;研究古典詩歌的學者,要敢為人之先,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假若沒有一些真知灼見,只是照本宣科地介紹他人的觀點、見解,我覺得對不起讀者的寶貴時間。此書就是抱着這種對讀者強烈的責任感寫出來的。
本書不僅精解了七十二首唐詩名作,在選詩和內容的組織上也獨闢蹊徑:以「縱」和「橫」兩個軸線來組織架構。所謂「縱橫」,各自又有兩個層次:其一是作為材料組織方面的「縱橫」,其二是方法論上的「縱橫」。
在材料組織方面,「縱」是指在詩歌解讀中注重詩歌形式方方面面的演變,力圖揭櫫它們的歷史發展脈絡。本書每個主題中,絕大部分的選詩是按照時序來組織的。通過「縱」的原則,我試圖找出唐詩不同時期、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間,以及不同的詩人之間相互影響和互動的痕跡。「橫」的方面的組織則更為複雜。傳統的詩歌分類方法以詩體為板塊,高棅的《唐詩品彙》、孫洙的《唐詩三百首》、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都把唐詩按照古詩、律詩、絕句三種來分類,實屬一種「橫向」的分類。然而,三書只是以此法將詩歸類,並沒有深入討論這三種詩體的表達各有怎樣的特點、在不同主題書寫上呈現出何種優勢和劣勢。在處理相同或相似的主題上,古詩、律詩、絕句其實各有其獨特的寫作方法。
本書亦按照傳統的分類方法,把唐詩分成律詩、絕句和古詩三種,其各部分又包括五言與七言兩類。但與傳統的編排不同,我不只舉例,更強調這三種詩體相互間的「橫向」比較。在詩體的大框架之下,全書七十二首詩按照十三個主題來組織。對每一個主題之中的作品都予以串講,做相互比較,從而彰顯每位作者處理該主題的獨特之處。通過這種橫向的組織,我們還可以發現,在某一詩體中,哪些主題用得比較多,最有特色;哪些主題難以恰當處理,故很少問津。例如寫「禪」的詩,五言為貴,七言便難以表達「禪」的精神;關於「詠史」的主題,五絕太短,七絕才更適於表達「史」的氣質。特定詩體用於表達特定主題,是否具有優勢或劣勢?為何如此?這些都是學界較少關注的,但卻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課題。
在方法論上,「縱」、「橫」也各司其職。在「縱」的方面,我注重和古人在「縱向」時間上的對話。古人談詩,大多數時候是一種欣賞性的「詩話」。我們闡釋唐詩、賞析唐詩,實際上都是對歐陽修《六一詩話》以來「詩話傳統」的繼承。我們討論的唐詩中的大部分問題,有很多其實是古人早已討論過的,我的解詩也深深得益於古人的真知灼見。當然,受惠於前人的同時,也應當以創新的思路延續之。詩話的核心之一就是談詩歌的形式,涉及詩歌語言使用的特點,比如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等。這些形式是如何來助力詩歌創作的,又是如何深入加強詩人和讀者的審美經驗的?探究這些理論問題時,我都會回歸詩話傳統,與古人進行溝通和交流。
方法論上的「橫」,主要是指將視野橫向展開,把唐詩放諸世界的文學批評(「世界詩學」)之中,以及穿梭於跨學科的不同維度之中。在分析詩歌句法、章法方面,我吸收了現代語言學研究古代漢語的成果,從主謂句、題評句兩個角度,揭示了近體詩營造絢麗紛呈的藝術境界的奧秘。站在現代語言學的角度,「主謂句」指主—動—賓的詞序。王力先生指出,「主—動—賓的語序是從上古漢語到現代漢語的詞序」(《漢語史稿》)。這種詞序呈現線性的邏輯及時空關係,配上從句,就能表達複雜的時空關係。李商隱〈隋宮〉名聯「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名詞「玉璽」、「錦帆」是主語,即句子中的施事者;動詞「歸」、「到」是謂語,即是句子所描述的動作或狀態;名詞「日角」、「天涯」是賓語,即動作的承受者。從主語→謂語→賓語,不僅指動作發生始末和空間關係,也點明施事、事、承事三者之間的邏輯關係。這聯兩行組合為一個跨行的複雜主謂句,主要是由形容動作的短語「不緣」、「應是」所致。「不緣」表示一種否定的假設,而「應是」表示這種假設的可能結果。這樣,兩行就構成了一個前後連貫、假設因果關係的複雜主謂句了。
「題評句」則由題語和評語組合而成,兩者之間有邏輯和時空的斷裂,故可呈現超時空的關係。例如,在杜甫〈江漢〉首聯「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中,名詞「江漢」、「乾坤」是題語,而名詞詞組「思歸客」、「一腐儒」是評語。兩行中,題語與評語邏輯上是斷裂的,因為江漢與思歸客、乾坤與腐儒屬於完全不同的事類。就時空關係而言,一句中的前兩字和後三字之間也沒有必然的時空關係。在題評句中,題語是詩人觀察的對象,而評語是詩人觀物的情感反應。杜甫凝視江漢天地,情感反應是想到自己當今的窘境,便用評語來抒情。
在律詩和律絕中,唐代詩人在句法上可謂是絞盡腦汁,各顯神通,各式各樣的主謂和題評句式應運而生,目不暇接,美不勝收。本書律詩篇和絕句篇中,每一個主題、每一篇詩作的分析,無不從句法和章法的角度展開,無不試圖從這兩方面說明它們予以我們無限審美享受的所以然。然而,在寫古詩時,唐人對煉字、煉句往往是不屑一顧的,儘管在名篇中我們偶爾可以見到精雕細琢的對句。因此,古詩篇的討論重點自然也移到了篇法結構上。
詩人書寫某一主題,為甚麼要選擇古體詩,而不是律詩或絕句?在同一篇詩內,不同的材料、段落如何組織起來,能使表達、抒情、寫意的效果是最佳的?這與詩人的詩風、篇法結構的安排息息相關。西方新批評中關於「詩人」、「詩中人」、「作品內容」之間的關係論說,對分析古詩結構有借鑒的價值。作品是用詩人第一人稱直接抒情,還是採用「詩中人」代言的視角,抑或是兩者混雜而用,這是很關鍵的,獨特的敘述視角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一篇古體詩的亮點。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就是以全知型的視角來寫,他知道所有人的心情,瞭解所有人的話語,但他本人從頭到尾也沒有站出來發表過議論。再如李白的〈月下獨酌〉,用第一人稱「我」來抒情,詩的內容便只限於「我」的瑰麗想像了。古體詩允許不同的敘述角度,或對話,或坦白,或寫意。這些分析都是我得益於「世界詩學」的結果。在方法論「橫」的方面,「世界詩學」的確為我開闢了分析古代詩歌的新路徑。
在本書中,「縱」與「橫」相互交錯,編織出了一個龐大的、多層次的網絡。將七十二首名作放入此網絡中進行精解,有助於加強微觀與宏觀的視野的互動。通過這種互動,我希冀引導讀者跳出「就詩論詩」的窠臼,將詩篇細讀與文學史知識相結合,做到「既見樹木,又見樹林」,既會作微觀的欣賞,又能有宏觀的把握。宏觀,通過微觀而變得有血有肉;微觀,通過宏觀而變得博大精深。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在這張「縱橫之網」中咀嚼欣賞七十二首名作吧!在閱讀過程中,讓我們細心尋繹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的關係,探究十三個主題的藝術特點,從而圓覽唐詩的發展。這樣閱讀,我們就有望把握唐詩的精髓。
此書能在較短時間完成,有賴於嶺南大學中文系徐曉童和樊哲揚同學幫助整理文稿,謹此鳴謝。
是為序。
我一直有這樣的構想:寫一部向廣大讀者介紹唐詩藝術,同時又有學術含金量的專著,這也是我對學術原創的執着追求的延伸。自從2008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如何閱讀中國詩歌:導讀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以來,在鑽研學術的同時,我一直孜孜不倦地開展推廣中國古典詩歌的工作,各種集體和個人項目也越做越大。首先是完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中國詩歌選集》系列(共三部),接着又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合作,於2023年出版此系列的兩部中文擴充版。從2022年開始,這項穿越英語、漢語世界的工程開始從書籍出版擴展到新媒體的傳播。2022年,我與美國十多位知名漢學家合作,推出五十六集的英文播客「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2023年推出三十四集中文視頻《唐詩之意境》;2024年3月,繼續推出九集中文視頻《唐詩之音韻》。無論是構思設計,還是具體的講解,無不源於我對原創的追求。我認為,做學術,不應該拘束於條條框框,應當有獨立的思想,敢於大膽發揮;研究古典詩歌的學者,要敢為人之先,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假若沒有一些真知灼見,只是照本宣科地介紹他人的觀點、見解,我覺得對不起讀者的寶貴時間。此書就是抱着這種對讀者強烈的責任感寫出來的。
本書不僅精解了七十二首唐詩名作,在選詩和內容的組織上也獨闢蹊徑:以「縱」和「橫」兩個軸線來組織架構。所謂「縱橫」,各自又有兩個層次:其一是作為材料組織方面的「縱橫」,其二是方法論上的「縱橫」。
在材料組織方面,「縱」是指在詩歌解讀中注重詩歌形式方方面面的演變,力圖揭櫫它們的歷史發展脈絡。本書每個主題中,絕大部分的選詩是按照時序來組織的。通過「縱」的原則,我試圖找出唐詩不同時期、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間,以及不同的詩人之間相互影響和互動的痕跡。「橫」的方面的組織則更為複雜。傳統的詩歌分類方法以詩體為板塊,高棅的《唐詩品彙》、孫洙的《唐詩三百首》、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都把唐詩按照古詩、律詩、絕句三種來分類,實屬一種「橫向」的分類。然而,三書只是以此法將詩歸類,並沒有深入討論這三種詩體的表達各有怎樣的特點、在不同主題書寫上呈現出何種優勢和劣勢。在處理相同或相似的主題上,古詩、律詩、絕句其實各有其獨特的寫作方法。
本書亦按照傳統的分類方法,把唐詩分成律詩、絕句和古詩三種,其各部分又包括五言與七言兩類。但與傳統的編排不同,我不只舉例,更強調這三種詩體相互間的「橫向」比較。在詩體的大框架之下,全書七十二首詩按照十三個主題來組織。對每一個主題之中的作品都予以串講,做相互比較,從而彰顯每位作者處理該主題的獨特之處。通過這種橫向的組織,我們還可以發現,在某一詩體中,哪些主題用得比較多,最有特色;哪些主題難以恰當處理,故很少問津。例如寫「禪」的詩,五言為貴,七言便難以表達「禪」的精神;關於「詠史」的主題,五絕太短,七絕才更適於表達「史」的氣質。特定詩體用於表達特定主題,是否具有優勢或劣勢?為何如此?這些都是學界較少關注的,但卻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課題。
在方法論上,「縱」、「橫」也各司其職。在「縱」的方面,我注重和古人在「縱向」時間上的對話。古人談詩,大多數時候是一種欣賞性的「詩話」。我們闡釋唐詩、賞析唐詩,實際上都是對歐陽修《六一詩話》以來「詩話傳統」的繼承。我們討論的唐詩中的大部分問題,有很多其實是古人早已討論過的,我的解詩也深深得益於古人的真知灼見。當然,受惠於前人的同時,也應當以創新的思路延續之。詩話的核心之一就是談詩歌的形式,涉及詩歌語言使用的特點,比如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等。這些形式是如何來助力詩歌創作的,又是如何深入加強詩人和讀者的審美經驗的?探究這些理論問題時,我都會回歸詩話傳統,與古人進行溝通和交流。
方法論上的「橫」,主要是指將視野橫向展開,把唐詩放諸世界的文學批評(「世界詩學」)之中,以及穿梭於跨學科的不同維度之中。在分析詩歌句法、章法方面,我吸收了現代語言學研究古代漢語的成果,從主謂句、題評句兩個角度,揭示了近體詩營造絢麗紛呈的藝術境界的奧秘。站在現代語言學的角度,「主謂句」指主—動—賓的詞序。王力先生指出,「主—動—賓的語序是從上古漢語到現代漢語的詞序」(《漢語史稿》)。這種詞序呈現線性的邏輯及時空關係,配上從句,就能表達複雜的時空關係。李商隱〈隋宮〉名聯「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名詞「玉璽」、「錦帆」是主語,即句子中的施事者;動詞「歸」、「到」是謂語,即是句子所描述的動作或狀態;名詞「日角」、「天涯」是賓語,即動作的承受者。從主語→謂語→賓語,不僅指動作發生始末和空間關係,也點明施事、事、承事三者之間的邏輯關係。這聯兩行組合為一個跨行的複雜主謂句,主要是由形容動作的短語「不緣」、「應是」所致。「不緣」表示一種否定的假設,而「應是」表示這種假設的可能結果。這樣,兩行就構成了一個前後連貫、假設因果關係的複雜主謂句了。
「題評句」則由題語和評語組合而成,兩者之間有邏輯和時空的斷裂,故可呈現超時空的關係。例如,在杜甫〈江漢〉首聯「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中,名詞「江漢」、「乾坤」是題語,而名詞詞組「思歸客」、「一腐儒」是評語。兩行中,題語與評語邏輯上是斷裂的,因為江漢與思歸客、乾坤與腐儒屬於完全不同的事類。就時空關係而言,一句中的前兩字和後三字之間也沒有必然的時空關係。在題評句中,題語是詩人觀察的對象,而評語是詩人觀物的情感反應。杜甫凝視江漢天地,情感反應是想到自己當今的窘境,便用評語來抒情。
在律詩和律絕中,唐代詩人在句法上可謂是絞盡腦汁,各顯神通,各式各樣的主謂和題評句式應運而生,目不暇接,美不勝收。本書律詩篇和絕句篇中,每一個主題、每一篇詩作的分析,無不從句法和章法的角度展開,無不試圖從這兩方面說明它們予以我們無限審美享受的所以然。然而,在寫古詩時,唐人對煉字、煉句往往是不屑一顧的,儘管在名篇中我們偶爾可以見到精雕細琢的對句。因此,古詩篇的討論重點自然也移到了篇法結構上。
詩人書寫某一主題,為甚麼要選擇古體詩,而不是律詩或絕句?在同一篇詩內,不同的材料、段落如何組織起來,能使表達、抒情、寫意的效果是最佳的?這與詩人的詩風、篇法結構的安排息息相關。西方新批評中關於「詩人」、「詩中人」、「作品內容」之間的關係論說,對分析古詩結構有借鑒的價值。作品是用詩人第一人稱直接抒情,還是採用「詩中人」代言的視角,抑或是兩者混雜而用,這是很關鍵的,獨特的敘述視角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一篇古體詩的亮點。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就是以全知型的視角來寫,他知道所有人的心情,瞭解所有人的話語,但他本人從頭到尾也沒有站出來發表過議論。再如李白的〈月下獨酌〉,用第一人稱「我」來抒情,詩的內容便只限於「我」的瑰麗想像了。古體詩允許不同的敘述角度,或對話,或坦白,或寫意。這些分析都是我得益於「世界詩學」的結果。在方法論「橫」的方面,「世界詩學」的確為我開闢了分析古代詩歌的新路徑。
在本書中,「縱」與「橫」相互交錯,編織出了一個龐大的、多層次的網絡。將七十二首名作放入此網絡中進行精解,有助於加強微觀與宏觀的視野的互動。通過這種互動,我希冀引導讀者跳出「就詩論詩」的窠臼,將詩篇細讀與文學史知識相結合,做到「既見樹木,又見樹林」,既會作微觀的欣賞,又能有宏觀的把握。宏觀,通過微觀而變得有血有肉;微觀,通過宏觀而變得博大精深。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在這張「縱橫之網」中咀嚼欣賞七十二首名作吧!在閱讀過程中,讓我們細心尋繹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的關係,探究十三個主題的藝術特點,從而圓覽唐詩的發展。這樣閱讀,我們就有望把握唐詩的精髓。
此書能在較短時間完成,有賴於嶺南大學中文系徐曉童和樊哲揚同學幫助整理文稿,謹此鳴謝。
是為序。
蔡宗齊
2025年1月25日
於香港屯門滿名山夢文廬
2025年1月25日
於香港屯門滿名山夢文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