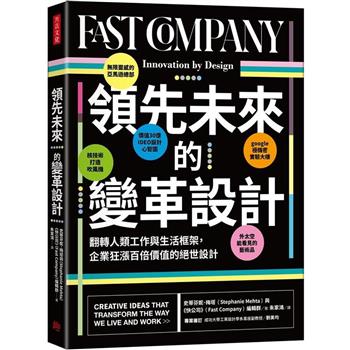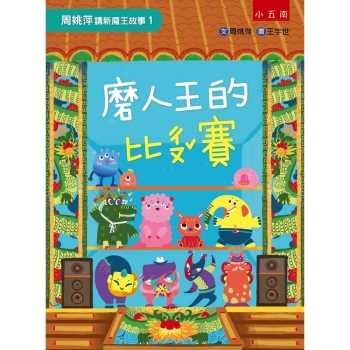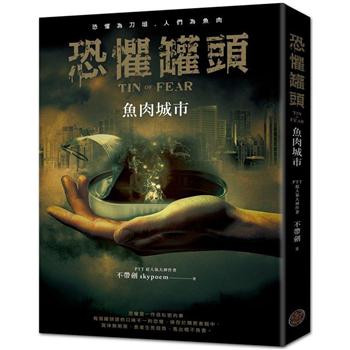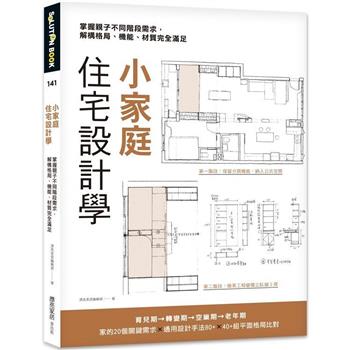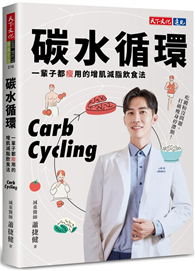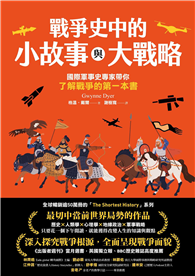中文譯本序
“既像玩雜耍,又像變戲法;剛剛讓它滑過去,隨即又把它抓回來;忽而用想像的虹彩把它點綴得五色繽紛,忽而又給它插上悖論的翅膀任其翱翔。”
王爾德《道林•格雷的畫像》第三章
“創作藝術作品依然是我的目的所在。你覺得我的處理精巧且具有藝術價值,我實在欣喜萬分。我覺得報上的那些文章好像出自那些荒淫無恥的市儈之手。我實在無法理解,他們怎麼可以將《道林•格雷的畫像》(下稱《畫像》) 當作不道德的作品呢。”1
以上摘自王爾德1891年4月寫給柯南•道爾的一封信中的幾句話,包含着讀者會感興趣的內容主要有二。收信人確實就是那位創造了大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及其助手約翰•華生醫生的小說家。阿瑟•柯南•道爾 (1859-1930) 比王爾德小五歲,二人應美國出版商斯托達特的邀請與之共進晚餐。席間,兩位作家接受斯托達特的約稿,為《利平科特月刊》(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 各寫一部小說。柯南•道爾在1924年出版的《回憶錄及冒險史》一書中述及:“王爾德送去的是《畫像》,那是一本有很高道德水平的書;而我則寫了《四個神秘的簽名》”2,此為其一。其二是,最早評論《畫像》的一些文章,卻與柯南•道爾的看法大相徑庭,認為此書公開侮辱了上流社會的價值觀,因而直接斥之為“不道德”。事情的緣由還得從頭說起。
十九世紀末葉,歐洲處於社會大變動的前夜,人心浮動,知識界分化的趨勢加劇。在這個被稱為“世紀末”的時期,歐洲文藝界一些富有才華的代表人物經歷着深刻的思想危機。他們對於自己所屬的階層有相當透徹的了解和頗為強烈的憎恨。為了給自己的創作尋找出路,開闢施展才能的新天地,他們中有些人率先走向唯美主義的殿堂,在文學方面倡導“為藝術的藝術”(Art for Art’s Sake),認為“不是藝術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藝術”。王爾德曾經寫下這樣一段話:“在這動盪和紛亂的時代,在這紛爭和絕望的可怕時刻,只有美的無憂殿堂可以使人忘卻,使人歡樂。我們不去往美的殿堂,還能去往何方呢?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異教經典稱作citta divana (聖城) 的地方去,在那裏一個人至少可以暫時擺脫塵世的紛擾與恐怖,也可以暫時逃避世俗的選擇。”3
奧斯卡•芬格爾•奧弗萊赫蒂•威利斯•王爾德1854年10月16日生於愛爾蘭首府都柏林。他的家世雖不算顯赫,但他父親是眼科名醫,曾給瑞典國王奧斯卡做過治療白內障的手術,並在1864年被維多利亞女王冊封為爵士 (倒並非因為手術,而是在人口統計方面有突出貢獻,此對於次子的命名也許有影響)。母親是一位富有民族主義精神的詩人 (筆名Speranza——拉丁文“希望”),參加過號召愛爾蘭人奮起衝擊都柏林城堡的“青年愛爾蘭”運動。奧斯卡自幼受到文學氛圍很濃的家庭薰陶,深愛古典文化,曾因古希臘文成績優異在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獲授予金質獎章,1874年得到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1805年,以收藏文物著稱的英國議員羅傑•紐迪吉特爵士設立了一項以他本人姓氏命名的詩歌獎。儘管王爾德在大學時代就為自己起了詩名,1878年還以《拉文納》一詩獲紐迪吉特獎,卻未能成為接受獎學金的研究生,遂於同年從牛津畢業。孰料上天給這位躊躇滿志的才子留下的時間已不到一半了。
王爾德的文學活動領域十分寬廣。他既是詩人 (1881年就有他的詩集問世),又寫小說和童話 (包括《快樂王子》、《石榴之家》、《阿瑟•薩維爾勳爵的罪行》三個書集,以及他唯一的長篇小說《畫像》,以上四本作品除《快樂王子及其他童話》於1888年成書外,其餘三本均於1891年出版)。他還寫過不少評論和隨筆 (較重要的有他自己選編的《意圖集》和《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均刊行於1891年)。但為他贏得最輝煌成功的要數1892至1895年間前後在倫敦西區舞台上首演的社會諷刺喜劇《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一個無足輕重的女人》、《一個理想的丈夫》和《認真的重要》。1891年王爾德根據聖經故事用法文寫下了獨幕劇《莎樂美》。這個見於《新約•馬太福音》第十四章和《新約•馬可福音》第六章的故事,已在十九世紀經過多位法國作家和畫家的詮釋,特別是以神話和宗教題材作色情畫聞名的象徵派畫家居斯塔夫•莫羅 (1826-1898) 所作的油畫《莎樂美之舞》,為後來者作了鋪墊。儘管如此,到了王爾德筆下還是給人無比強烈的衝擊,難怪英國內務大臣以藉口“任何以聖經人物為角色的劇目都不准在英國上演”,拒絕給此劇頒發演出許可證。4德國作曲家理查•斯特勞斯在1905年把王爾德的原劇譜寫成歌劇,只是由拉赫曼譯成德文的唱詞代替了法文台詞。這位晚期浪漫主義作曲家在《莎樂美》和他的另一部歌劇《厄勒克特拉》(1909) 中完成了向表現主義的過渡。理查•斯特勞斯的歌劇《莎樂美》被選為1998年2月香港藝術節的揭幕之作,其中的《七重紗之舞》更是二十世紀以來許多指揮家和交響樂隊展示瑰奇多變的管弦樂色彩效果的熱門曲目。
王爾德總共寫過九部戲劇,但另外四部劇作已被遺忘。真正令他名利雙收的那幾部社會諷刺喜劇全都集中在九十年代前期,可想見他在十九世紀末英國戲劇界是何等舉足輕重。本文起首處引用的一段文字,寫的是對道林•格雷的道德淪喪負有很大責任的亨利•沃登勳爵在上流社會餐桌旁口若懸河、妙語迭出的精彩表演。從作者津津樂道的口吻可以看出,王爾德無疑是在顧影自憐,因為他自己正是這樣的表演高手,而他在社交圈中越練越“酷”的口才,在他的社會喜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令觀眾如癡如醉,以致當時的劇場頂替了教堂在社會中的地位 (蕭伯納語)。然而正當王爾德身為劇作家的好運如日中天之際,一場醜聞官司卻把他從九霄雲端一下子直摔進了萬丈深淵。
1895年2月14日,王爾德最後一部,也是他才華機智達到巔峰狀態的劇作《認真的重要》在聖詹姆斯劇院首演,觀眾如潮,盛況空前。兩週後,王爾德在阿爾比馬爾俱樂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約翰•道格拉斯 (John Sholto Douglas, Marquis of Queensberry, 1844-1900) 留下的名片,上面寫着:“致裝模作樣的好男色者奧斯卡•王爾德”。王爾德從1891年開始便與比他小十六歲的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 (侯爵之子,當時還在上牛津大學) 有不正當關係,而且經常“儷影雙雙”地出現在倫敦的公共場所,並一起旅遊,令侯爵十分反感。侯爵對自己的兒子毫無辦法,而阿爾弗雷德也不斷挑戰父親的權威。1894年4月,兒子還曾打電報侮辱其父;6月,侯爵亦曾到切爾西泰特街王爾德的寓所羞辱後者遭逐,故在大半年後有這次留名片之舉。王爾德與年輕男性的同性戀行為遭人物議不自此時始。前面提到過譴責《畫像》的評論家中就有一位是查爾斯•惠布里,他在《蘇格蘭觀察家報》上撰文稱:“奧斯卡•王爾德先生又開始寫那等還是不寫為妙的貨色了。”其中的“又”字暗示王爾德於1889年發表的《W. H.先生的畫像》一文。要說這篇東西是小說、散文或學術考據都不像,又都像,內容是通過分析研究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提出一種觀點:莎翁這些詩篇奉獻和讚美的對象W. H.先生乃是一個名叫威利•休斯的小男旦 (莎士比亞時代戲劇中的少女角色往往由少男扮演)。惠布里顯然認為王爾德有拉莎翁為自己“好男色”壯膽之嫌疑。評論接着指出:“……除了那些不法貴族和變態的電報投送員,沒人要看他寫的東西。”這裏更是毫不含糊地重提發生在1889年的一樁同性戀醜聞,那件事曾使經常光顧克利夫蘭街上一家孌童妓院的亞瑟‧薩默賽特勳爵和一批郵局僱員名譽掃地。5但是到了1895年,王爾德居然向一貫百般嘲弄他的作品和生活方式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法律和社會求助,以誹謗罪把昆斯伯里侯爵告上法庭。兩年後,王爾德沉痛地承認自己做了“一生中最可恥、最無法原諒、最可鄙的事”。1895年4月3日,法院開庭審理王爾德訴昆斯伯里侯爵誹謗案 (王爾德自幼渴望的倒是能在“女王訴王爾德”的官司中出庭),被告輕而易舉地反證原告確是“好男色者”,從而推翻誹謗的指控。4月5日,侯爵無罪獲釋,王爾德反因涉嫌“與其他男子發生有傷風化的肉體關係”被捕後保釋候審。又經過兩次審訊,5月25日,倫敦中央刑事法院根據1885年通過針對男子同性戀的刑法修正案判處王爾德兩年勞役刑罰,先後囚於紐蓋特、彭頓韋爾和萬茲沃斯監獄,11月20日又移至雷丁監獄服滿刑期。這位折翼的悖論大師從此一蹶不振。6
1897年5月,王爾德刑滿釋放後立即流亡法國,化名塞巴斯蒂安•梅爾莫斯。三個月後,他完成了長詩《雷丁監獄之歌》,1898年在倫敦出書,十六個月內就印至第七版。這是他的天鵝之歌,也是身為詩人的王爾德的最高成就。1897年9月,他在法國魯昂與道格拉斯重逢,兩人還於10月同赴意大利的卡布里島旅遊,但終於在次年斷交。1898年4月,康斯坦絲去世。1900年11月30日,王爾德因患腦膜炎病逝於巴黎阿爾薩斯旅館,臨終時由羅斯請來了神父為他施洗,實現了逝者皈依天主教的遺願。
在王爾德去世之日與這個譯本出版之時中間隔着整整一個二十個世紀,還得掛上二十一世紀的肇始。一百多年來,這個“臭名昭著的牛津聖奧斯卡、詩人、殉道者”(他逝世前不久為自己想好的永久稱號),一直是文壇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不過,讚美也罷,唾駡也罷,若此公泉下有靈,應該不會感到寂寞和悲哀,因為他有一句名言:“世上唯一比被人議論更糟糕的,就是無人議論。”上世紀末了的那幾年,英美兩國掀起了一場王爾德熱潮。1995年2月,為紀念《認真的重要》上演一百週年,英國政府在西敏寺詩人角設彩色櫥窗,展覽王爾德的生平和創作,倫敦和都柏林分別舉行王爾德紀念牌揭幕式;4月,BBC播放紀念王爾德的專題片;同年,新月書局印行了最新版的《王爾德全集》。1997年是王爾德刑滿出獄一百週年,倫敦和紐約各地紛紛重排上演《認真的重要》、《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等名劇,巴黎出版了法文多卷本《王爾德文集》。英國小說家、電影名演員史蒂芬•佛萊 (Stephen Fry) 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撰文指出,王爾德再度崛起,成為繼莎士比亞之後,在歐洲被閱讀最多、被譯成語種最多的英國作家。在為數可觀的傳記中,被認為最客觀和公允的名作是理查德•埃曼所著的《奧斯卡•王爾德》。此書由佛萊改編和主演,並由布萊恩•吉爾伯特執導搬上銀幕。佛萊甚至認為:“對於那些近來方有合法同性戀地位且需要英雄和殉道者的人們,他是一個聖人;……稱王爾德為救世主,聽上去有些過份誇張……但與基督的一生比較,相似之處明顯存在。”在1998年3月5日《紐約書評》上發表《預言家》一文的傑森•愛普斯坦寫道:“……王爾德用他的花花公子面貌和極端的唯美主義來挑戰的不單單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虛偽。他所挑戰的是英國歷史上最為頑固的禮法。”
當然,對於如此興師動眾、頂禮膜拜的紀念活動也有人持強烈反對態度。1998年5月18日的《紐約客》週刊發表了阿當•戈普尼克的文章《發明奧斯卡•王爾德》。作者認為“批評家、電影家和劇作家在把維多利亞的傳統敵人王爾德當成同性戀殉道者來紀念。他們全都弄錯了”。戈普尼克引用王爾德生前所言“凡是企圖證明甚麼的書都不值得閱讀”,斷言目前所有與之有關的書,王爾德肯定都不會去讀。7
其實,不同觀點的交鋒應該是正常和有益的。一百多年前《畫像》剛問世便遭到強烈譴責,同樣也不意味着當時只有一片討伐聲。除了本文開頭提到的柯南•道爾外,愛爾蘭詩人、劇作家威廉•葉芝 (William Yeats, 1865-1939) 稱《畫像》是“一本奇妙的書”,沃爾特•佩特用“真正有活力的”來概括它的特點。也許可以公平地說,只要不是把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奉為金科玉律的人,都能從中發現不少可供欣賞和值得讚歎的東西。意味深長的是,當初北美洲對此書的評論就比它的原產地好得多。王爾德本人剛從在英國遭到迎頭痛擊的震盪中緩過神來,便開始努力捍衛這部小說的生存權。他在大量書簡和文章 (尤其是《從深處》) 中提到《畫像》所流露的深情,是他對自己其他作品所不能比擬的。出獄後不久,他在給出版商倫納德•史密瑟斯的信中寫道:“我只知道《畫像》是部經典作品,而且堪稱經典作品。”8
和任何經典作品一樣,《畫像》也是在其他經典的基礎上寫出來的。探究其淵源,不難想到巴爾札克的《驢皮記》、哥提耶的《莫班小姐》等等。當然,浮士德博士為窮究生命意義用自己的靈魂換取魔鬼梅菲斯特的幫助這筆交易,無疑為道林•格雷表達那個致命的願望——讓畫像變老變醜作為自己永葆青春的代價——提供了一份“合約樣本”。作為《人間喜劇•哲學研究》系列中影響最大的一部作品,《驢皮記》顯然比其他作品與《畫像》有更近的親緣關係。巴爾札克筆下的瓦朗坦因慾望得不到滿足而日夜受着煎熬,只想求得一天的快樂,哪怕用生命去換取也在所不惜。處在這種心態的瓦朗坦,遇到一個老古董商送給他一張有東方文字符籙的驢皮,但須用他的生命作代價。驢皮象徵着持有者的壽限,它將與所滿足的慾望強度和次數成正比同步收縮。瓦朗坦毫不猶豫地接受下來。然而他每次實現自己的願望後感受到的卻不是快樂,而是恐怖,因為眼看着驢皮越縮越小,他清楚地意識到死亡離自己越來越近,最後在一次縱慾中結束了生命。
這裏不能不提到《畫像》第十章末段亨利勳爵帶給道林的一本黃封面的書。這本沒有直接點明的書乃是法國作家若利斯·卡爾·於斯曼 (Joris Karl Huysmans, 1848-1907) 所寫的《逆流》(A Rebours)。它的主人公德艾薩特反抗社會的態度近乎德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性施虐狂”或泛指任何虐待狂的sadism一詞,即由其姓氏得名,此人也因而“不朽”)。王爾德並不掩飾自己對此書有一定程度的欣賞,但也毫不含糊地指出“這是一本有毒的書”。上述那些作品的回聲在《畫像》中時有所聞,但王爾德不是一個一邊公開抄襲他人,一邊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人,只要有正當理由,他也不怕抄襲。他曾告訴一名記者,那本毒害了道林•格雷的奇書應該是《逆流》的一個奇幻變種。但是,用過於肯定的方式斷言王爾德與其他作家的相似性或與其他書籍的師承關係,難免會流於輕率。1895年王爾德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過:“撇開希臘文和拉丁文作者的散文和詩歌不說,影響過我的只有約翰•濟慈、古斯塔夫•福樓拜和華特•佩特,而在我與之相會前,我已迎着他們走了一大半路程。”上述三位作家中有兩個是英國人,所以阿瑟•蘭瑟姆認定《畫像》是“用英文寫成的第一部法國小說”這一說法,稍稍有些熱心過頭。9
王爾德是個非常迷信的人,《畫像》從一開始便讓人感到宿命和厄運的壓力。請看第一章畫家霍爾渥德對亨利勳爵說的話:“才貌出眾的人多半在劫難逃……你有身份和財產,亨利;我有頭腦和才能,且不管它們價值如何;道林•格雷有美麗的容貌。我們都將為上帝賜給我們的這些東西付出代價,付出可怕的代價。”當王爾德自己被關在雷丁監獄的囚室內付出他所說的可怕的代價時,曾在《從深處》中提到“厄運像一條紫線貫穿《畫像》那件金衣”。小說第十二章一開始交代了道林殺死霍爾渥德那天是前者三十八歲生日的前夕,但在《利平科特月刊》上發表的最早版本卻是三十二歲生日的前夕,這不是甚麼無關宏旨的細節。王爾德最初因靈感文思如泉湧而寫得太快,沒有意識到這年齡會洩露天機 (王爾德初涉同性戀泥淖時年三十有二),但他把此事與道林謀殺畫家的罪惡聯繫起來,恰恰說明王爾德並不是一個真正隨心所欲、完全蔑視禮法的人。他的負罪感一直令他對自己身上墮落的一面覺得如芒刺在背,但在作者和他筆下的人物之間劃上等號未免過於簡單。王爾德自己1894年2月12日在致拉爾夫•佩恩的信中寫道:“這本書會造成毒害,或者促成完美,道林•格雷並不存在……貝澤爾•霍爾渥德是我認為的個人寫照;亨利勳爵在外界看來就是我;道林是我願意成為的那類人——可能在別的時代。”10在文情斐然的字裏行間未必不能發現道德家尖刻審視的目光,甚至在他唯美派或花花公子的面具後面潛伏着一個天生的清教徒也難說。他喜歡他所創造的那個光輝燦爛的世界,但也可以讓這個世界隨着道林•格雷臨死前極度恐怖的一聲慘叫訇然倒塌。說到底,通過《畫像》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王爾德,首先是一個小說家,而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文化史家,對小說本身也只能從這一角度來評判。即使不用現今比一百年前“開明”得多的尺度加以衡量,《道林•格雷的畫像》也不該被詆為一本不道德的書。
榮如德
王爾德自序
藝術家是美的作品的創造者。
藝術的宗旨是展示藝術本身,同時把藝術家隱藏起來。
批評家應能把他對美的作品的印象用另一種樣式或新的材料表達出來。
自傳體是批評的最高形式,也是最低形式。
在美的作品中發現醜惡含義的人是墮落的,而且墮落得一無可愛之處。這是一種罪過。
在美的作品中發現美的含義的人是有教養的。這種人有希望。
認為美的作品僅僅意味着美的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
書無所謂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書有寫得好的或寫得糟的。僅此而已。
十九世紀對現實主義的憎惡,猶如從鏡子裏照不見自己面孔的卡利班的狂怒。
十九世紀對浪漫主義的憎惡,猶如從鏡子裏照不見自己面孔的卡利班的狂怒。
人的精神生活只是藝術家創作題材的一部份,藝術的道德則在於完美地運用並不完美的手段。
藝術家並不祈求證明任何事情。即使那些天經地義的事情也是可以證明的。
藝術家沒有倫理上的好惡。藝術家如在倫理上有所臧否,那是不可原諒的矯揉造作。
藝術家從來沒有病態。藝術家可以表現一切。
思想和語言是藝術家藝術創作的手段。
邪惡與美德是藝術家藝術創作的素材。
從形式着眼,音樂家的藝術是各種藝術的典型。從感覺着眼,演員的技藝是典型。
一切藝術同時既有外觀,又有象徵。
有人要鑽到外觀底下去,那由他自己負責。
有人要解讀象徵意義,那由他自己負責。
其實,藝術這面鏡子反映的是照鏡者,而不是生活。
對一件藝術品的看法不一,說明這作品新穎、複雜、重要。
批評家盡可意見分歧,藝術家不會自相矛盾。
一個人做了有用的東西可以原諒,只要他不自鳴得意。一個人做了無用的東西,只要他視若至寶,也可寬宥。
一切藝術都是毫無用處的。
奧斯卡‧王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