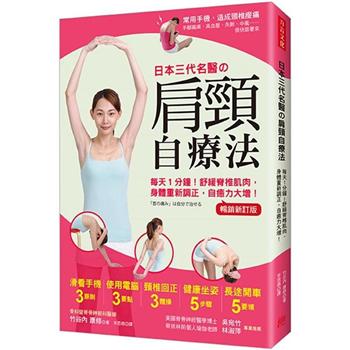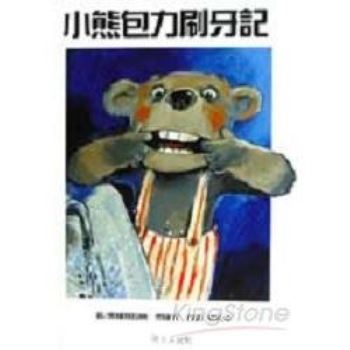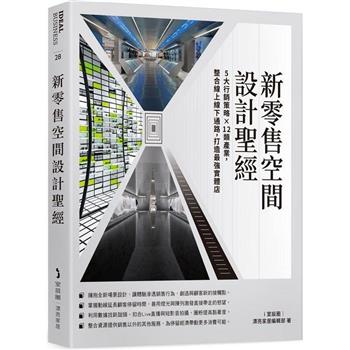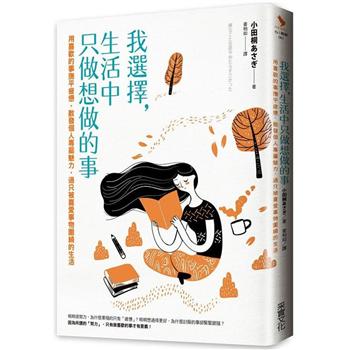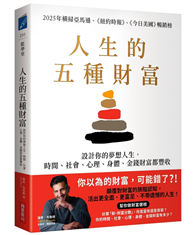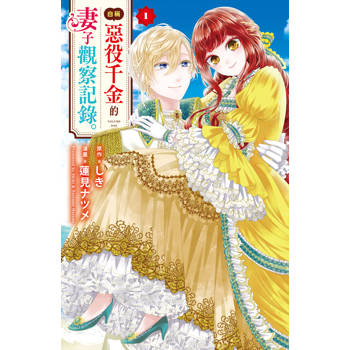《香港文學大系》共三輯,包括新詩、散文、小說、評論、舊體文學、通俗文學、兒童文學等共十二卷,由十一位本地專家學者擔任主編,追本溯源,發掘被時間洪流淹沒的早期香港文學作品。
本卷選錄1942至1949年間,在日據與戰後兩個歷史時期裡,香港報刊所刊載的散文以及個人文集裡的篇章。本地作家的佳構與南來名家的作品兼收,說理、敘事、記人、抒情、表意、狀物、寫景各種體例均備。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散文卷二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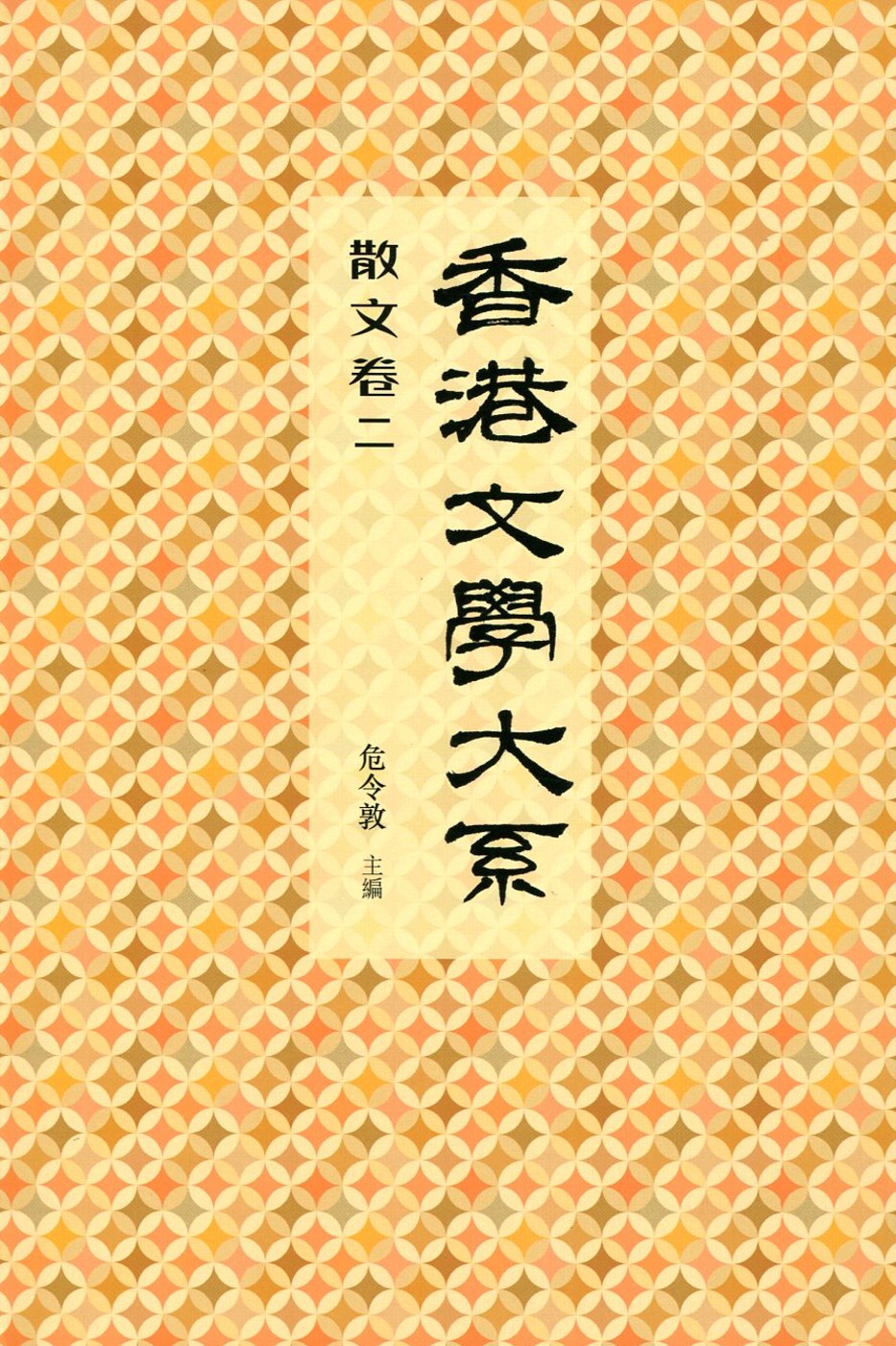 |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散文卷二 作者:危令敦 出版社:商務 出版日期:2014-07-3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37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6 |
散文 |
$ 316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16 |
中文現代文學 |
$ 340 |
社會人文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現代散文 |
$ 36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散文卷二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危令敦先生
是暨南大學文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危教授的研究興趣包括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港澳文學及比較文學。
論著有《香港小說五家》、《一生二,二生三:高行健小說研究》、合編論文集有《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情思滿江山,天地入沉吟:第一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
危令敦先生
是暨南大學文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危教授的研究興趣包括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港澳文學及比較文學。
論著有《香港小說五家》、《一生二,二生三:高行健小說研究》、合編論文集有《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情思滿江山,天地入沉吟:第一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
目錄
總序/陳國球……1
凡例……41
導言/危令敦……43
玄囿
新歲感……85
夜談與散文……87
葉靈鳳
吞旃隨筆……90
秋鐙夜讀抄……96
鄉愁……102
憶江南……105
陶惠
去年今日——香港攻略戰身歷記……112
易玲
香港新年雜景……132
戴望舒
鹽倉土地……139
記瑪德里的書市……141
山居雜綴……145
寄友人……148
學子
關於北京人的種種……151
陳君葆
談女人……155
上下……159
詹言……160
閒空……162
黃魯
門……165
斷想伍則……168
死的默想……171
一個人的紀念……174
三蘇
直版論……178
實迫處此論……179
恭喜平安論……181
雞變鴨論……182
施蟄存
栗和柿……184
夏果
喜悅的尋覓……188
香港‧船的城……190
香港的風景畫……192
自強
龍陵雨……197
李綉
職業太太……202
緊急疏散——香港學校風光……205
黃秋耘
門外愛談——青年生活諸問題之一……207
皮球、坦克和小螺絲釘——青年
生活諸問題之二……210
「香港頭」的改造——青年
生活諸問題之三……213
穆何之
談吃蛇貓之類——北方人聽了
毛骨悚然……219
衝鋒章……221
北平的胡同……224
故都的酒肆……226
佚名
南京屠殺漏網記……228
紅鷹
「強制歸鄉」歷險記……232
黃藥眠
海的懷念……234
沒有眼淚的城市……237
沉思……243
野店……247
聶紺穹
毛澤東先生與魚肝油丸……254
論時局……258
怎樣做母親……261
蘇海
電車社會……274
易水
木屋旅行記……277
鷗外鷗
愛我的夏娃(們)……280
當我寫作的時候……284
一個人的成長……288
與北園克衛的友誼……294
夏衍
超負荷論……299
坐電車跑野馬……304
侶輪
燈火……310
書與我……312
人參……315
舊地……319
黃蒙田
蜀道小記……324
鬼魂……327
縴伕……330
吳盂
婁山關買鳥記……334
茅店的風情……339
林默涵
獅和龍……342
秦牧
野獸……347
司馬文森
「山上人」和「山下人」……353
香豬……358
田裏的魚……360
艾迪
沒有了燈的房間……363
海兵
風災……369
樓適夷
遇盜的故事……378
高岱
香港的二樓社會……384
巴波
書……387
戈雲
周求落魄記……391
文值
秋風裡的蕭頓球塲……398
宋光
藏書家……401
澹生
華北的黃塵……405
望雲
給我一隻好浴盆……408
黃金的好日子……409
無心之失……411
殘生……412
馮式
蚯蚓的文學情調……416
南明河之憂鬱——憶烽火中的貴陽……417
舒巷城
冬天的故事——一九四九年一月
寓居香港西灣河剩稿……420
作者簡介……425
凡例……41
導言/危令敦……43
玄囿
新歲感……85
夜談與散文……87
葉靈鳳
吞旃隨筆……90
秋鐙夜讀抄……96
鄉愁……102
憶江南……105
陶惠
去年今日——香港攻略戰身歷記……112
易玲
香港新年雜景……132
戴望舒
鹽倉土地……139
記瑪德里的書市……141
山居雜綴……145
寄友人……148
學子
關於北京人的種種……151
陳君葆
談女人……155
上下……159
詹言……160
閒空……162
黃魯
門……165
斷想伍則……168
死的默想……171
一個人的紀念……174
三蘇
直版論……178
實迫處此論……179
恭喜平安論……181
雞變鴨論……182
施蟄存
栗和柿……184
夏果
喜悅的尋覓……188
香港‧船的城……190
香港的風景畫……192
自強
龍陵雨……197
李綉
職業太太……202
緊急疏散——香港學校風光……205
黃秋耘
門外愛談——青年生活諸問題之一……207
皮球、坦克和小螺絲釘——青年
生活諸問題之二……210
「香港頭」的改造——青年
生活諸問題之三……213
穆何之
談吃蛇貓之類——北方人聽了
毛骨悚然……219
衝鋒章……221
北平的胡同……224
故都的酒肆……226
佚名
南京屠殺漏網記……228
紅鷹
「強制歸鄉」歷險記……232
黃藥眠
海的懷念……234
沒有眼淚的城市……237
沉思……243
野店……247
聶紺穹
毛澤東先生與魚肝油丸……254
論時局……258
怎樣做母親……261
蘇海
電車社會……274
易水
木屋旅行記……277
鷗外鷗
愛我的夏娃(們)……280
當我寫作的時候……284
一個人的成長……288
與北園克衛的友誼……294
夏衍
超負荷論……299
坐電車跑野馬……304
侶輪
燈火……310
書與我……312
人參……315
舊地……319
黃蒙田
蜀道小記……324
鬼魂……327
縴伕……330
吳盂
婁山關買鳥記……334
茅店的風情……339
林默涵
獅和龍……342
秦牧
野獸……347
司馬文森
「山上人」和「山下人」……353
香豬……358
田裏的魚……360
艾迪
沒有了燈的房間……363
海兵
風災……369
樓適夷
遇盜的故事……378
高岱
香港的二樓社會……384
巴波
書……387
戈雲
周求落魄記……391
文值
秋風裡的蕭頓球塲……398
宋光
藏書家……401
澹生
華北的黃塵……405
望雲
給我一隻好浴盆……408
黃金的好日子……409
無心之失……411
殘生……412
馮式
蚯蚓的文學情調……416
南明河之憂鬱——憶烽火中的貴陽……417
舒巷城
冬天的故事——一九四九年一月
寓居香港西灣河剩稿……420
作者簡介……425
序
總序
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是説膩了的老話,也是一個事實。早期出現多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疏誤實在太多,香港學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由於上世紀三〇年代面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認為是後來「新文學史」書寫的重要依據,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不絕於耳。1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際此,有關「文學大系」如何牽動「文學史」的意義,值得我們回顧省思。
一、「文學大系」作為文體類型
在中國,以「大系」之名作書題,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由趙家璧主編,蔡元培總序,胡適、魯迅、茅盾、朱自清、周作人、郁逹夫等任各集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大系」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指有系統地把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匯聚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大」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系」指其間的組織聯繫。2趙家璧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就提到他以「大系」為題是師法日本;他以為這兩個字:
既表示選稿範圍、出版規糢、動員人力之「大」,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又是一個有「系統」的整體,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3
《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以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並依循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區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資料顯示,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
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一九三八》(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六八)。
在臺灣則有: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九);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一九八九—二〇〇三》(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
>《馬華新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新加坡:世界書局/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〇—一九七二);
>《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新加坡:世界書局,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一);
>《馬華文學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
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
>《戰後新馬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七六)(北京:華藝出版社,一九九九);
>《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二〇〇一);
>《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五);
>《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等。
其他以「大系」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形形色色還有許多,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於此不必細論。
導言
一
本卷涵蓋的歷史時期為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年,而這個時期又以一九四五年九月為界,再分為「日據」與「戰後」兩個階段。
劃分的依據是對香港民生與文化產生直接衝擊和影響的三個重要軍事與政治事件:(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正式向美、英兩國宣戰,同時入侵菲律賓、馬來亞以及香港等地,引發太平洋戰爭。駐港英軍不敵日軍,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向日軍投降,香港遂淪為日軍「占領地」。(二)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與九日,美軍分別在廣島與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促使日本於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十六日,英軍夏愨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H. J. Harcourt)代表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在港督府接受據港日軍投降。1至此,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階段結束,香港步入戰後復原時期。(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此之前,香港政府為管理境內迅速增加的人口,於同年八月十七日通過《人口登記條例》,登記居民資料並為居民簽發身分證。一九五〇年,香港政府為限制中國難民入境,舒緩人口壓力,封鎖中港邊境關卡。一九五一年初,中國政府限制人口流向廣東,以減少南下香港的人數,並封鎖邊境。此後兩地民眾不能自由往來。2
二
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報業與文學,香港這塊「飛地」;曾發揮微妙而重要的作用,不僅被稱為「文化中心」,4更被譽為「輿論中心」,5甚至被比喻為言論的「天堂」。6由於微妙的地緣政治與複雜的歷史因素使然,香港成為中國現代報業發源地之一,也是中國政黨組織各種活動,並通過報刊宣揚政見,向北方喊話的重要場域。自一八七四年王韜與黃勝在港創辦《循環日報》開始,康有為、梁啓超的改革派以及孫中山的革命黨均在港辦報宣傳,此為香港的「黨派報業」時期。及至三〇與四〇年代,中日兩國交戰,加上國共兩黨內鬥,意識形態的戰火蔓延至香港報業,以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六至四九年間最為激烈。7早期香港華文報刊在報道新聞、評説時事之餘,不忘文學。8爾後大批文人因時局動盪或政治工作需要,9分別於三〇年代及四〇年代下半葉南來,在報刊上抒發政見,亦發表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他們的寫作興旺了此地的報刊文化,也促進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10一部分文人的文學評論更深刻的影響了日後中國文藝的方向。11
論者研究二十世紀前半葉香港報業或文學,都留意到中國因素的支配性影響。此時的香港報業與內地報業幾乎「融為一體」,所關注的焦點是中國,而不是香港。此地的報道與輿論轉向本土是一個漸進過程,隨著「社經報業」在戰後逐步取代「黨派報業」才日趨顯著。12至於香港本土的新文學,從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雖有人才與陣地,但與內地文人兩度以「排山倒海」之姿南來香港的盛況相比,聲勢未免微弱。13換句話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文學的主體性尚未明朗,此地報刊上湧現的新文學大體是中國文學的延伸,被研究者稱為「香港的文學」,意即「在香港出現的文學」或「『在香港』的文學」。14後來報業轉而關注本土社會民生,與香港人口持續增長,生活改善,人心轉向,凝聚力趨強有關。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香港華人社會基本上由移民組成,他們抱著「過客」心態居留,身分認同的主要對象是中國,不是香港。進入五〇年代,不斷湧至的華人移民與難民因不願北返而安身香港,成為永久居民,此後出生的華人亦視香港為家,以此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為榮,本土意識方才得以滋長。15香港文學須待二十世紀下半葉方才逐漸浮現。16
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是説膩了的老話,也是一個事實。早期出現多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疏誤實在太多,香港學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由於上世紀三〇年代面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認為是後來「新文學史」書寫的重要依據,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不絕於耳。1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際此,有關「文學大系」如何牽動「文學史」的意義,值得我們回顧省思。
一、「文學大系」作為文體類型
在中國,以「大系」之名作書題,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由趙家璧主編,蔡元培總序,胡適、魯迅、茅盾、朱自清、周作人、郁逹夫等任各集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大系」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指有系統地把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匯聚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大」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系」指其間的組織聯繫。2趙家璧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就提到他以「大系」為題是師法日本;他以為這兩個字:
既表示選稿範圍、出版規糢、動員人力之「大」,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又是一個有「系統」的整體,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3
《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以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並依循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區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資料顯示,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
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一九三八》(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六八)。
在臺灣則有: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九);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一九八九—二〇〇三》(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
>《馬華新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新加坡:世界書局/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〇—一九七二);
>《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新加坡:世界書局,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一);
>《馬華文學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
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
>《戰後新馬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七六)(北京:華藝出版社,一九九九);
>《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二〇〇一);
>《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五);
>《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等。
其他以「大系」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形形色色還有許多,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於此不必細論。
陳國球(節錄)
導言
一
本卷涵蓋的歷史時期為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年,而這個時期又以一九四五年九月為界,再分為「日據」與「戰後」兩個階段。
劃分的依據是對香港民生與文化產生直接衝擊和影響的三個重要軍事與政治事件:(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正式向美、英兩國宣戰,同時入侵菲律賓、馬來亞以及香港等地,引發太平洋戰爭。駐港英軍不敵日軍,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向日軍投降,香港遂淪為日軍「占領地」。(二)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與九日,美軍分別在廣島與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促使日本於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十六日,英軍夏愨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H. J. Harcourt)代表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在港督府接受據港日軍投降。1至此,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階段結束,香港步入戰後復原時期。(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此之前,香港政府為管理境內迅速增加的人口,於同年八月十七日通過《人口登記條例》,登記居民資料並為居民簽發身分證。一九五〇年,香港政府為限制中國難民入境,舒緩人口壓力,封鎖中港邊境關卡。一九五一年初,中國政府限制人口流向廣東,以減少南下香港的人數,並封鎖邊境。此後兩地民眾不能自由往來。2
二
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報業與文學,香港這塊「飛地」;曾發揮微妙而重要的作用,不僅被稱為「文化中心」,4更被譽為「輿論中心」,5甚至被比喻為言論的「天堂」。6由於微妙的地緣政治與複雜的歷史因素使然,香港成為中國現代報業發源地之一,也是中國政黨組織各種活動,並通過報刊宣揚政見,向北方喊話的重要場域。自一八七四年王韜與黃勝在港創辦《循環日報》開始,康有為、梁啓超的改革派以及孫中山的革命黨均在港辦報宣傳,此為香港的「黨派報業」時期。及至三〇與四〇年代,中日兩國交戰,加上國共兩黨內鬥,意識形態的戰火蔓延至香港報業,以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六至四九年間最為激烈。7早期香港華文報刊在報道新聞、評説時事之餘,不忘文學。8爾後大批文人因時局動盪或政治工作需要,9分別於三〇年代及四〇年代下半葉南來,在報刊上抒發政見,亦發表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他們的寫作興旺了此地的報刊文化,也促進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10一部分文人的文學評論更深刻的影響了日後中國文藝的方向。11
論者研究二十世紀前半葉香港報業或文學,都留意到中國因素的支配性影響。此時的香港報業與內地報業幾乎「融為一體」,所關注的焦點是中國,而不是香港。此地的報道與輿論轉向本土是一個漸進過程,隨著「社經報業」在戰後逐步取代「黨派報業」才日趨顯著。12至於香港本土的新文學,從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雖有人才與陣地,但與內地文人兩度以「排山倒海」之姿南來香港的盛況相比,聲勢未免微弱。13換句話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文學的主體性尚未明朗,此地報刊上湧現的新文學大體是中國文學的延伸,被研究者稱為「香港的文學」,意即「在香港出現的文學」或「『在香港』的文學」。14後來報業轉而關注本土社會民生,與香港人口持續增長,生活改善,人心轉向,凝聚力趨強有關。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香港華人社會基本上由移民組成,他們抱著「過客」心態居留,身分認同的主要對象是中國,不是香港。進入五〇年代,不斷湧至的華人移民與難民因不願北返而安身香港,成為永久居民,此後出生的華人亦視香港為家,以此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為榮,本土意識方才得以滋長。15香港文學須待二十世紀下半葉方才逐漸浮現。16
危令敦(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