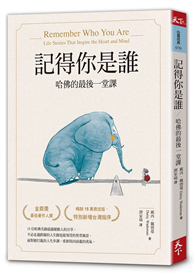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小說卷一的圖書 |
 |
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小說卷一 出版社:商務 出版日期:2015-08-1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23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2 |
社會人文 |
$ 316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小說 |
$ 36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小說卷一
本卷發掘香港1919至1941年間,印行於雜誌、報章副刊及單行本之小說。
二十年代香港文學新舊交替,白話小說的內容與技巧雖仍處於摸索階段,卻沿此開發出奇異多元的創作實績。其中可見私小說式的文人感懷、城市感官的印象速寫、社會低下階層生活之刻劃;不少作者更通過現代小說此一有待定義之媒介,或深入人際關係、情感愛慾的幽微處,或重塑社會道德價值、性別身份,大膽新穎之想像,未必不及後來者。三十年代末至香港淪陷前,不少內地知名作家短暫來港,固然予本地文壇以啟發與示範,但亦同時成為主導聲音,文學創作與急迫的政治局勢漸見無可分割,早期香港新文學的活力反倒有所減退。
為存香港文學草創時期之豐富面貌,本卷收入作品既有出於成名作家侶倫、謝晨光、張稚子(張稚廬)等,亦不乏被時代遺忘之無名作者。
本書特色:
1. 本書編選原則、方法和體例嚴謹,除參考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體例合編為12卷外,並盡量結合香港獨有的文學特色,兼具廣闊的包容性,亦與目前各地出版的各種文學大系的體例及規模相符,適合圖書館、各相關文學團體及研究機構典藏。
2. 本書編輯委員會、顧問團均為香港知名學者及作家,極具代表性。
3. 本書是研究香港文學的必備工具書。
作者簡介:
謝曉虹,香港科技大學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師。獲第十五屆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2004年度香港中文文學獎小說組冠軍。個人首本小說集《好黑》獲第八屆中文文學雙年獎首獎。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發起人之一。近期作品有合著小說《雙城辭典》、短篇小說集Snow and Shadow(Nicky Harman 翻譯)。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謝曉虹
- 出版社: 香港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5-08-14 ISBN/ISSN:978962074507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23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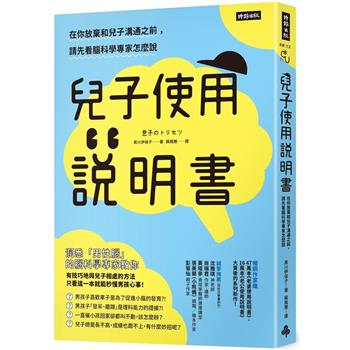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