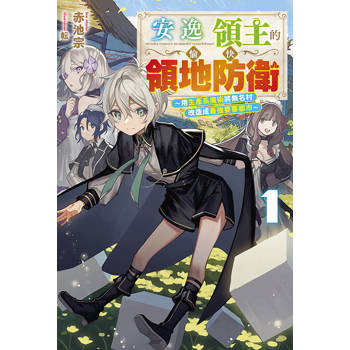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的圖書 |
| |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 出版日期:2016-02-26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48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48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華文文學研究 |
$ 39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
內容簡介
早期香港文學評論向來被論者忽略,本卷致力梳理香港戰前之文學評論發展過程。主題包括二○年代新舊文學之論爭;三○年代初年輕新文學作家嶄露頭角,議論新詩流派,譯介西方文學評論;抗戰開始大批文人從內地南移香港,香港成為臨時文化中心,南來文人各據報刊陣地,開展了民族形式論爭、抗戰文學論爭、反新式風花雪月等多場重要論爭;抗戰時期的和平文藝理論,本卷皆予以收錄,力圖多角度反映香港文學評論全貌。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國球
加拿大多倫多比較文學碩士,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加拿大雅博特大學東亞系訪問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北京大學、台灣清華大學、東華大學訪問學人。著有《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省思》、《鏡花水月──文學理論批評論文集》、《文學香港與李碧華》、《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情迷家國》、《結構中國文學傳統》、《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抒情中國論》等,合編有《文學史》集刊、《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陳教授專長文學史理論研究,曾整編香港文學選本目、發表〈香港的文學選本〉、〈「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以及關香港文學史論文多篇。
陳國球
加拿大多倫多比較文學碩士,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加拿大雅博特大學東亞系訪問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北京大學、台灣清華大學、東華大學訪問學人。著有《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省思》、《鏡花水月──文學理論批評論文集》、《文學香港與李碧華》、《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情迷家國》、《結構中國文學傳統》、《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抒情中國論》等,合編有《文學史》集刊、《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陳教授專長文學史理論研究,曾整編香港文學選本目、發表〈香港的文學選本〉、〈「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以及關香港文學史論文多篇。
目錄
總序/陳國球
凡例
導言/陳國球
第一輯 一九三○年及以前
文壇新與舊
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羅澧銘
學者演講/觀微
聽魯迅君演講後之感想/探秘
藝術與革命/張詩正
最近中國文壇三大派之我觀/周洪
香港的文藝﹝存目﹞/吳灞陵
文體認知
新詩的地位/許夢留
概談國詩的過去及將來/吳光生
談偵探小說/灞陵
短篇小說緒言/杜若
四六駢文之概要﹝存目﹞/何禹笙原著、何惠貽錄刊
南音與鍾德﹝存目﹞/勞夢廬
屈原之小說學﹝存目﹞/其章
最近的新詩﹝存目﹞/雲仙
觀察中歐戲劇史下對於粵劇的貢獻﹝存目﹞/冷紅
作家與作品
中國新文壇幾位女作家/冰蠶
茶花女與蘇曼殊/稚子
談談陶晶孫和李金髮﹝存目﹞/謝晨光
看了「可憐的秋香」以後的感想﹝存目﹞/自强
秋之草紙﹝存目﹞/杜格靈
西方文藝思潮
易卜生(Henrik Ibsen)傳﹝節錄﹞/袁振英
靆靆派/葉觀棪
托爾斯泰主義/袁振英
易卜生底女性主義﹝存目﹞/袁振英
文學的兩大陣線﹝存目﹞/靈谷
論藝術的發生及其効果﹝存目﹞/杜格靈
辛克萊呂維斯﹝存目﹞/佐勳
第二輯 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一年
香港文壇評議
從談風月說到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節錄﹞/石不爛講、楊春柳記
關于「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水人
關於反映香港/森蘭
一個公開的控訴/許菲
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存目﹞/貝茜
香港的文藝界﹝存目﹞/簡又文
文學論爭:抗戰文藝‧和平文藝‧反新式風花雪月
國防文學與戰爭文學/華胥
文藝零感之一——國防文學/王訪秋
口號之爭與創作自由/華胥
抗戰文學中的浪漫主義質素/李育中
新文學與舊形式/施蟄存
再談新文學與舊形式/施蟄存
論新文學與舊形式/林煥平
抗戰文藝與政治/杜埃
也談「抗戰文藝與政治」/黃繩
建立我們的和平救國運動/娜馬
藝術創作的現實(性)和真實(性)/李漢人
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楊剛
「反新式風花雪月」座談會會記──團結‧求進步‧文藝工作者的大聚會/松針
關于文藝大眾化的二三意見﹝存目﹞/黃繩
再斥所謂「和平救國文藝運動」﹝存目﹞/葉靈鳳
略論「懷鄉」文章﹝存目﹞/艾秋
錯誤的「挑戰」——對新風花雪月問題的辯正﹝存目﹞/潔孺
兩地書﹝存目﹞/娜馬、揚帆
文藝理論與思潮
論象徵主義詩歌/隱郎
新藝術領域上底表現主義/黎覺奔
再廣現實主義/李南桌
唯美派的研究﹝節錄﹞/朱伽
革命的藝術﹝存目﹞/林離
黑之學說﹝存目﹞/鷗外鷗
行動主義的文學理論﹝存目﹞/林煥平
精神分析與文學﹝存目﹞/何玄
廣現實主義﹝存目﹞/李南桌
論情感的纖細─詩隨筆之一﹝存目﹞/潔孺
形象化——我將嘗試「形象化」之形象化﹝存目﹞/唐瑯
文體論
抒情的放逐/徐遲
關於詩的二三事/王烙
從緘默到詩朗誦/徐遲
詩之鑑賞/木下
關於詩的定義/路易士
新詩片論/彭耀芬
小品文的閒適觀/文博
魯迅式雜文之再建/杜埃
怎樣在華南寫小說?/王幽谷
怎樣展開香港戲劇運動/陳丹楓
舊體文學存廢問題/劉京
對於詩歌上的一個建議﹝存目﹞/陳白
詩與歌的問題﹝存目﹞/李燕
論近代的報告文學﹝存目﹞/李育中
新聞雜誌對於近代小說的影響﹝存目﹞/劉憮
「真正文學的詩」新解﹝存目﹞/林煥平
抒情無罪﹝存目﹞/陳殘雲
抒情的時代性﹝存目﹞/陳殘雲
詩朗誦─記徐遲「最強音」的朗誦﹝存目﹞/袁水拍
談香港戲劇運動的新方向﹝存目﹞/殊倫
作家與作品
論「現代」詩/劉火子
戴望舒與陳夢家/白廬
評路易士之「不朽的肖像」/蕭明
「不死的榮譽」讀後/黎明起
讀銀狐集/黎明起
散文二種/巡禮人
「囚綠記」/杜文慧
國內藝壇碎論──沈從文的小說/何厭
論幻想的美──徐訏的「鬼戀」/明之
「黑麗拉」讀後──侶倫其人及其小說/夢白
論侶倫及其「黑麗拉」/寒星女士
啞劇的試演──「民族魂魯迅」/馮亦代
嶺海文家列講/萊哈
豹翁述學﹝選錄六則﹞/豹翁
評聖母像前並論王獨清﹝存目﹞/李育中
看了現代劇團公演「油漆未乾」後﹝存目﹞/任穎輝
詩問答﹝存目﹞/杜格靈、李金髮
搬戴望舒們進殮房﹝存目﹞/鷗外鷗
評艾青與田間兩本近作﹝存目﹞/白廬
對於「木蘭從軍」的評議﹝存目﹞/揚帆
莫里哀在中國﹝存目﹞/胡春冰
論人民之歌──「而西班牙歌唱了」讀後感﹝存目﹞/黃繩
古典新論
王漁洋──中國的象徵主義者/風痕
詩人之告哀─司馬遷論/梁之盤
中國文學之虛無主義/何洪流
芸窗漫錄﹝存目﹞/克潛
中國文學之唯美主義﹝存目﹞/何洪流
世界文壇概況
「金色的田疇」──世界史詩談/編者(梁之盤)
現代美國文學專號讀後/李育中
現代捷克斯拉夫文藝思潮略述/堅磨
薛維爾兄妹──現代英詩人介紹/李育中
舊書攤──義大利的黃昏/西夷
從未來主義到革命鬭爭──談瑪雅可夫斯基的詩/慧娜
動亂中的世界文壇報告之一──他們在那裏?/林豐
戰時日本之文化動態/林煥平
近代蘇俄文學的鳥瞰﹝存目﹞/少曼
喬也斯﹝存目﹞/梁之盤
幽默家皮藍得婁評傳﹝存目﹞/比特
德國文藝近況鳥瞰﹝存目﹞/ S.Y.
第二次大戰與世界作家﹝存目﹞/林煥平
海敏威的路──從他的「喪鐘為誰而鳴」看過去﹝存目﹞/林豐
附錄
和平文藝論(四)/李志文
圓寶盒的神話/徐遲
詩論零札/戴望舒
從一個人看他的作品
侶倫著:「黑麗拉」‧「無盡的愛」‧「夜岸」/冬青
凡例
導言/陳國球
第一輯 一九三○年及以前
文壇新與舊
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羅澧銘
學者演講/觀微
聽魯迅君演講後之感想/探秘
藝術與革命/張詩正
最近中國文壇三大派之我觀/周洪
香港的文藝﹝存目﹞/吳灞陵
文體認知
新詩的地位/許夢留
概談國詩的過去及將來/吳光生
談偵探小說/灞陵
短篇小說緒言/杜若
四六駢文之概要﹝存目﹞/何禹笙原著、何惠貽錄刊
南音與鍾德﹝存目﹞/勞夢廬
屈原之小說學﹝存目﹞/其章
最近的新詩﹝存目﹞/雲仙
觀察中歐戲劇史下對於粵劇的貢獻﹝存目﹞/冷紅
作家與作品
中國新文壇幾位女作家/冰蠶
茶花女與蘇曼殊/稚子
談談陶晶孫和李金髮﹝存目﹞/謝晨光
看了「可憐的秋香」以後的感想﹝存目﹞/自强
秋之草紙﹝存目﹞/杜格靈
西方文藝思潮
易卜生(Henrik Ibsen)傳﹝節錄﹞/袁振英
靆靆派/葉觀棪
托爾斯泰主義/袁振英
易卜生底女性主義﹝存目﹞/袁振英
文學的兩大陣線﹝存目﹞/靈谷
論藝術的發生及其効果﹝存目﹞/杜格靈
辛克萊呂維斯﹝存目﹞/佐勳
第二輯 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一年
香港文壇評議
從談風月說到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節錄﹞/石不爛講、楊春柳記
關于「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水人
關於反映香港/森蘭
一個公開的控訴/許菲
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存目﹞/貝茜
香港的文藝界﹝存目﹞/簡又文
文學論爭:抗戰文藝‧和平文藝‧反新式風花雪月
國防文學與戰爭文學/華胥
文藝零感之一——國防文學/王訪秋
口號之爭與創作自由/華胥
抗戰文學中的浪漫主義質素/李育中
新文學與舊形式/施蟄存
再談新文學與舊形式/施蟄存
論新文學與舊形式/林煥平
抗戰文藝與政治/杜埃
也談「抗戰文藝與政治」/黃繩
建立我們的和平救國運動/娜馬
藝術創作的現實(性)和真實(性)/李漢人
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楊剛
「反新式風花雪月」座談會會記──團結‧求進步‧文藝工作者的大聚會/松針
關于文藝大眾化的二三意見﹝存目﹞/黃繩
再斥所謂「和平救國文藝運動」﹝存目﹞/葉靈鳳
略論「懷鄉」文章﹝存目﹞/艾秋
錯誤的「挑戰」——對新風花雪月問題的辯正﹝存目﹞/潔孺
兩地書﹝存目﹞/娜馬、揚帆
文藝理論與思潮
論象徵主義詩歌/隱郎
新藝術領域上底表現主義/黎覺奔
再廣現實主義/李南桌
唯美派的研究﹝節錄﹞/朱伽
革命的藝術﹝存目﹞/林離
黑之學說﹝存目﹞/鷗外鷗
行動主義的文學理論﹝存目﹞/林煥平
精神分析與文學﹝存目﹞/何玄
廣現實主義﹝存目﹞/李南桌
論情感的纖細─詩隨筆之一﹝存目﹞/潔孺
形象化——我將嘗試「形象化」之形象化﹝存目﹞/唐瑯
文體論
抒情的放逐/徐遲
關於詩的二三事/王烙
從緘默到詩朗誦/徐遲
詩之鑑賞/木下
關於詩的定義/路易士
新詩片論/彭耀芬
小品文的閒適觀/文博
魯迅式雜文之再建/杜埃
怎樣在華南寫小說?/王幽谷
怎樣展開香港戲劇運動/陳丹楓
舊體文學存廢問題/劉京
對於詩歌上的一個建議﹝存目﹞/陳白
詩與歌的問題﹝存目﹞/李燕
論近代的報告文學﹝存目﹞/李育中
新聞雜誌對於近代小說的影響﹝存目﹞/劉憮
「真正文學的詩」新解﹝存目﹞/林煥平
抒情無罪﹝存目﹞/陳殘雲
抒情的時代性﹝存目﹞/陳殘雲
詩朗誦─記徐遲「最強音」的朗誦﹝存目﹞/袁水拍
談香港戲劇運動的新方向﹝存目﹞/殊倫
作家與作品
論「現代」詩/劉火子
戴望舒與陳夢家/白廬
評路易士之「不朽的肖像」/蕭明
「不死的榮譽」讀後/黎明起
讀銀狐集/黎明起
散文二種/巡禮人
「囚綠記」/杜文慧
國內藝壇碎論──沈從文的小說/何厭
論幻想的美──徐訏的「鬼戀」/明之
「黑麗拉」讀後──侶倫其人及其小說/夢白
論侶倫及其「黑麗拉」/寒星女士
啞劇的試演──「民族魂魯迅」/馮亦代
嶺海文家列講/萊哈
豹翁述學﹝選錄六則﹞/豹翁
評聖母像前並論王獨清﹝存目﹞/李育中
看了現代劇團公演「油漆未乾」後﹝存目﹞/任穎輝
詩問答﹝存目﹞/杜格靈、李金髮
搬戴望舒們進殮房﹝存目﹞/鷗外鷗
評艾青與田間兩本近作﹝存目﹞/白廬
對於「木蘭從軍」的評議﹝存目﹞/揚帆
莫里哀在中國﹝存目﹞/胡春冰
論人民之歌──「而西班牙歌唱了」讀後感﹝存目﹞/黃繩
古典新論
王漁洋──中國的象徵主義者/風痕
詩人之告哀─司馬遷論/梁之盤
中國文學之虛無主義/何洪流
芸窗漫錄﹝存目﹞/克潛
中國文學之唯美主義﹝存目﹞/何洪流
世界文壇概況
「金色的田疇」──世界史詩談/編者(梁之盤)
現代美國文學專號讀後/李育中
現代捷克斯拉夫文藝思潮略述/堅磨
薛維爾兄妹──現代英詩人介紹/李育中
舊書攤──義大利的黃昏/西夷
從未來主義到革命鬭爭──談瑪雅可夫斯基的詩/慧娜
動亂中的世界文壇報告之一──他們在那裏?/林豐
戰時日本之文化動態/林煥平
近代蘇俄文學的鳥瞰﹝存目﹞/少曼
喬也斯﹝存目﹞/梁之盤
幽默家皮藍得婁評傳﹝存目﹞/比特
德國文藝近況鳥瞰﹝存目﹞/ S.Y.
第二次大戰與世界作家﹝存目﹞/林煥平
海敏威的路──從他的「喪鐘為誰而鳴」看過去﹝存目﹞/林豐
附錄
和平文藝論(四)/李志文
圓寶盒的神話/徐遲
詩論零札/戴望舒
從一個人看他的作品
侶倫著:「黑麗拉」‧「無盡的愛」‧「夜岸」/冬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