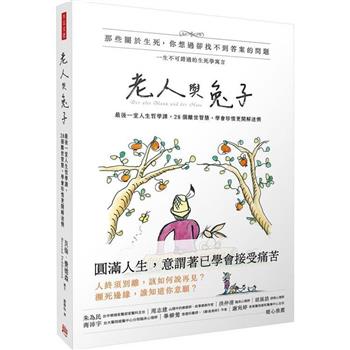二〇〇七年秋,我把曾在不同的學術期刊發表過的四篇論文,經過調整和修改,再加寫了一篇〈導言〉,編成了一本專書,以《胡適與新儒家》為書名,送交臺北中央研究院的出版機構審查。當時該出版機構已採用了作者和審查人的雙向匿名的審查制度,大約二個月後,我收到了第一份匿名的審查報告,對拙書稿幾乎是完全肯定,認為只需略作修改便可以出版。但到了二〇〇八年一月初,我收到了另一份匿名的審查報告,對拙書稿完全予以否定。該報告寫得相當的長,其中的核心論述,端在於舉出胡適曾在其著述中,尤其是在英文著述中,對孔子和中國文化有所肯定,而拙書稿竟把胡適視為「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者,究其實是大錯特錯。本來,按照學界行之有年的慣例,若出現了一正一負的審查意見,還需再送第三位匿名審查人決審。但我細讀了負面報告之後,認為確實打中了要害。於是,我便主動向出版機構提出撤稿,不需再送第三審了。
本來,在撤稿之前,我已在全力撰寫另一本《五論馮友蘭》的專書,在撤稿之後,我便把書稿丟到抽屜中,先把新書撰成再說。誰料新書付梓不久,我便接受了香港理工大學的聘書,離開工作了二十年的中研院近史所。來到香港的前四年,身為參與創建中國文化學系的資深教授,「開荒牛」的負重角色,我被日常繁忙雜多的學術行政工作擠壓得難於喘氣;從未曾在大學專任教職而欠缺教書經驗,又迫使我必須用數倍於別人的時間來準備教案,這不啻是百上加斤。四年過後,新學系的行政教學工作終於走上了正軌,我才從箱底翻出塵封已久的書稿,深入自省昔日失察的緣由。
我在徹底反傳統的社會中生活了將近二十年。二十三歲的那一年,我有幸負笈於當時尚未退出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研究所,在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的教誨薰陶之下,開始從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逐漸變成了當代新儒學的信仰者。我皈依新儒學的經驗,和異教徒轉奉(convert to)基督教的體驗頗有相類之處。由於「聞道」比常人艱難得多,「見道」之後也就把握得比常人更加堅定。愈堅定的信仰,便愈容易形成《莊子‧齊物論》中的「成心」,而有「成心」又必有「成見」。我正是囿於成見,沒有深入省察到「五四」反傳統運動本身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沒有把胡適和「五四」運動的其他主要領袖如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人作適當的區分;同時,我也沒有覺察到胡適的思想和言行之中的矛盾和複雜性,對胡適某些肯定中國文化的言論視而不見。
由於長期在大學和研究機構學習和工作,過眼的聰明人可謂多矣,而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又是我這輩子見過最聰明的三個人。但在他們三人和錢穆先生等港臺新儒學大師的大量著述中,也同樣把胡適和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人,不加區分地並列為鼓吹「打倒孔家店,廢止漢字,一切重估價值,打倒二千年來的學術思想而全盤西化」(錢穆語)的「禍首罪魁」。此一當代學術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公案,似乎又不能完全以「成心」加以解釋。是否因為胡適肯定中國文化的某些微弱聲音,相較於他猛烈攻訐中國文化的大量「過火」兼「過頭」放言高論,無論在「質」和量的兩個方面都渺小得不成比例,因而在摧陷廓清中國文化方面的客觀效果,把他「融會中西」和「充分世界化」的初心遮蔽了?若果真如此,胡適是否也應為錢、唐、牟、徐等人「成心」的形成,負有相當一部分的責任?
反省過後,我便從失足之地站立起來再出發。我的書寫和論述方向,已改為呈現當代新儒學大師馮友蘭、錢穆、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等人,是如何在「觀看」五四反傳統運動,尤其是如何在「觀看」胡適,藉以為當前研究五四運動的眾聲喧嘩,加入另一種新的聲響。我把書名由《胡適與新儒家》,改為《新儒家眼中的胡適》,正是為了與此一改變相適應。除了把原來的四個舊章大幅度調整、刪節和改寫之外,我還另外加寫了四個新的篇章;此一舉措,在壞的方面,讓書中的字數增加了一倍;但在好的方面,也使得書中的「名」和「實」,變得更為相副。此外,在呈現新儒學諸大師的「觀看」「五四」和胡適之時,我也會在適當的地方,加入一些扼要的疏釋,藉以說明胡適的某些引起誤會的言行及其原因。至於昔日囿於「成心」而在行文中針對胡適的一些「失敬」的言詞,凡能被我覺察到的,也都已刪除了。
和十二年前的舊稿相較,本書可以說算是一本新著。此書之所以能撰成及付梓,首先得感謝舊稿的兩位匿名審查人。肯定的審查意見,是我能在摔跤後再站起來的精神支柱。否定的審查意見,對我是一記當頭棒喝。它提醒我治學須突破「成心」的束縛,看問題切忌簡單化和片面化,而只有那些能夠充分地展現其研究對象的矛盾性和複雜性的著述,才更值得我們以一輩子努力去探索和追求。由於必須遵守學術的紀律,我不可能知悉兩位審查人姓名並當面叩謝,但我由衷地希望,希望他(她)們有機會讀到這篇小序,並領受我誠摯的敬意和感謝。
所謂「千虛不如一實」。能夠向自己的研究對象當面請益,相信是任何研究者莫大的福報。我一九八二年七月曾有幸在檀香山和舊金山二次訪問過馮友蘭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八月在臺北內雙溪素書樓上有幸拜謁了錢穆先生。至於在負笈九龍農圃道新亞研究所之時,常侍隨於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講席杖履之後,過蒙三位恩師耳提面命,覺悟開迷,更是沒齒難忘。
本書前後八章,常從不同的對象、不同的視角,處理相似或相近的課題,故在內容上或文字上難免有重複之處;儘管已大力加以刪節,容或仍有「漏網之魚」,隱身於此章或彼章之字裏行間。先師唐先生被問及著書何以重複難免之時,嘗慨乎言:「重複何傷乎?倘真理不重複,則錯誤必重複!」旨哉旨哉!聊以自解。
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毛永波先生的一再優容。本書自二〇一四年簽約之後,因自覺還需更多的時間改寫,我竟再三再四在交稿期限中「食言而肥」,最後還藉退休而自行「失聯」;如果不是毛先生過人的耐性、不斷的溫馨提醒,以及他的多次寬容和永不放棄,本書早已胎死腹中。感謝我在中研院時的研究助理吳燕秋小姐、陳依婷小姐、吳景傑博士、任立瑜先生,尤其是張繼瑩博士和嵇國鳳小姐,如果沒有他們幫忙蒐集、抄錄、查對各種研究資料、輸入電腦文稿以及借書還書等繁雜事務,本書是不可能寫出來的。感謝香港理工大學的導師胡光明博士,全憑他在擔任我的研究助理時,以其精密和嚴謹的校對,讓本書可能出現的錯誤減至最低。感謝陳永發教授、白先勇教授、張洪年教授、何漢威教授、洪長泰教授、馮耀明教授、羅志田教授、葉其忠教授、余敏玲教授、楊翠華教授、羅久蓉教授、楊貞德教授、呂妙芬教授、賴惠敏教授、胡曉真教授、林月惠教授、何冠環教授、陳曉平教授、黎漢基教授、賀照田教授、楊祖漢教授、李瑞全教授、楊君實博士、徐均琴博士、李啟文博士、陸鍵東先生、曹永洋先生以及陳文華先生,感謝他們賜讀全部或部分書稿並惠予寶貴意見。當然,最該感謝的還是內子華瑋和小女君宜,有了她們的一路陪伴,任何荒涼貧脊的文化沙漠,都會變成萬紫千紅的人文樂園。
先慈陳芷君女士和先嚴翟超先生,以九三與百歲之高齡,兩年多前先後在美國三藩市棄養。人子頓失怙恃之哀思,卻未因父母之福壽全歸而稍減。憶及每有成書之日,先父母恆挑燈夜讀,相與講評,引為至樂;而此書出版之稽遲十有二年,竟使先父母未及生前展讀,孤兒心中抱憾,奚可勝言!唯願把本書化作一瓣心香,呈獻給先父母在天之靈。
二〇一九年元宵之夜東邑翟志成自序於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教職員宿舍我樂山房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新儒家眼中的胡適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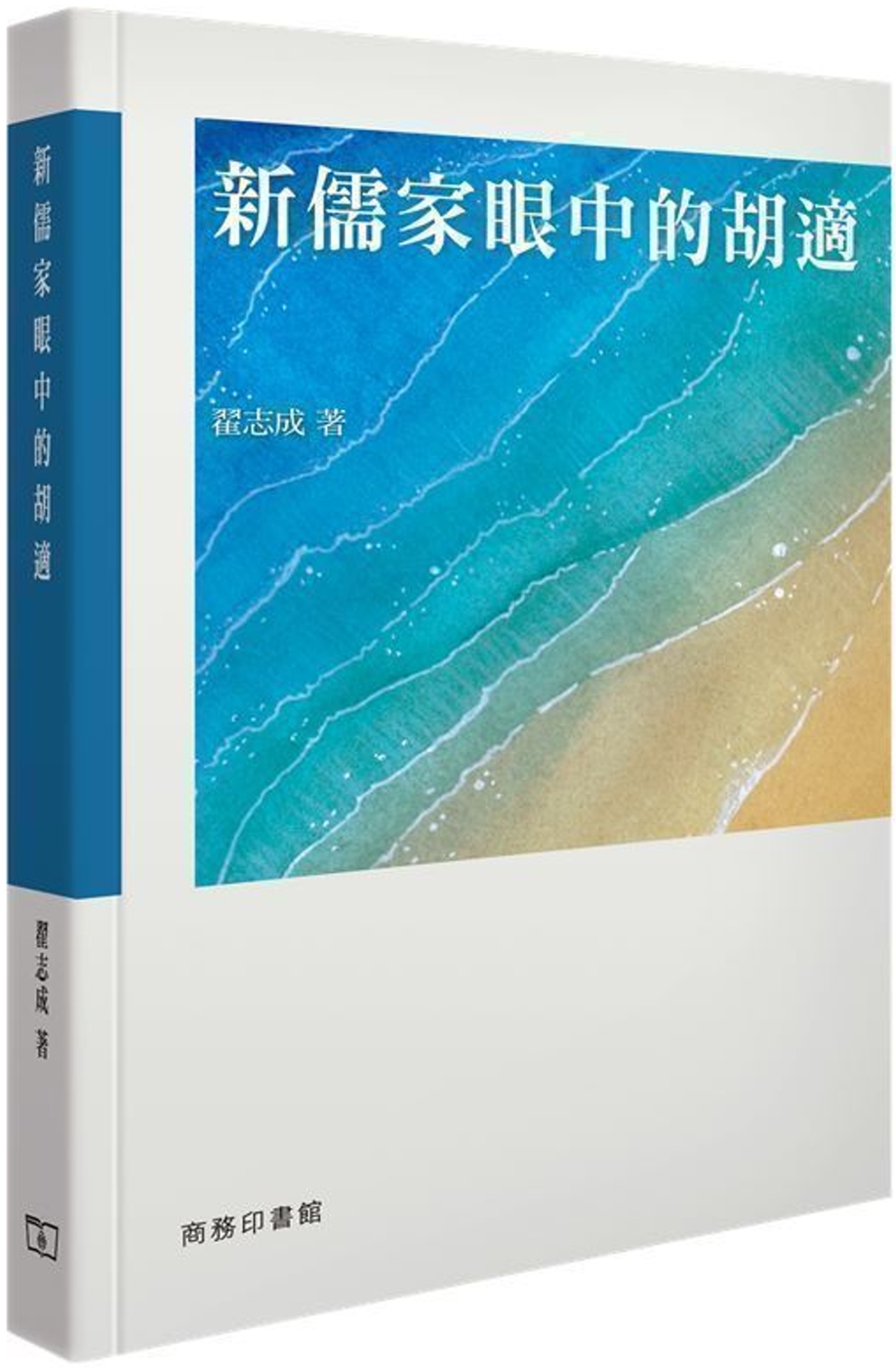 |
新儒家眼中的胡適 作者:翟志成 出版社:商務 出版日期:2020-09-1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34頁 / 15.2 x 22.7 x 2.17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89 |
中國/東方哲學 |
$ 546 |
Others |
$ 558 |
中文書 |
$ 558 |
中國哲學 |
$ 558 |
哲學 |
$ 55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儒家眼中的胡適
本書呈現當代新儒學大師馮友蘭、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等人,是如何在「觀看」五四反傳統運動,尤其如何在「觀看」胡適,作者把他們和胡適,互相設置為參照座標,透過他們和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整體看法的根本分岐,藉以深入剖析當代新儒學與五四反傳統主義,如何一方面互相對立、互相批駁和互相鬥爭,另一方面又互相依存、互相滲透和互相轉化;通過對立面的反襯和照明,當代新儒學和五四反傳統主義彼此的睿智及其理論上的盲點,都變得更為凸顯和更加脈絡分明。
作者簡介:
翟志成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哲學博士(歷史學),曾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教授、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關係學院訪問學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訪問學人,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新亞學報》主編,研究領域涵蓋中國學術文化哲學思想史和中共黨史,著有《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當代新儒學史論》、《五論馮友蘭》、《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等專書,以及中英文學術論文五十多篇。
作者序
二〇〇七年秋,我把曾在不同的學術期刊發表過的四篇論文,經過調整和修改,再加寫了一篇〈導言〉,編成了一本專書,以《胡適與新儒家》為書名,送交臺北中央研究院的出版機構審查。當時該出版機構已採用了作者和審查人的雙向匿名的審查制度,大約二個月後,我收到了第一份匿名的審查報告,對拙書稿幾乎是完全肯定,認為只需略作修改便可以出版。但到了二〇〇八年一月初,我收到了另一份匿名的審查報告,對拙書稿完全予以否定。該報告寫得相當的長,其中的核心論述,端在於舉出胡適曾在其著述中,尤其是在英文著述中,對孔子和中國文化有所肯定...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 錄
自序 ................................................................................................... i
導言 .................................................................................................. v
第一章 救亡思潮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 1
第二章 胡適的馮友蘭情結 .......................................................59
第三章 錢穆與胡適的交涉 .....................................................103
第四章 胡適與熊十力的分歧 ............................
自序 ................................................................................................... i
導言 .................................................................................................. v
第一章 救亡思潮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 1
第二章 胡適的馮友蘭情結 .......................................................59
第三章 錢穆與胡適的交涉 .....................................................103
第四章 胡適與熊十力的分歧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