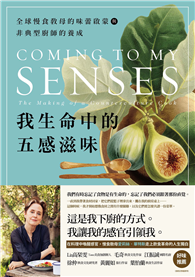透過人物講故事,告訴你日本人世界觀的轉變
三個歷史人物: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
三個重要時期: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戰後昭和期
帶你看日本兩百年來如何重新認識世界、如何給自己定位
三個歷史人物: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
三個重要時期: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戰後昭和期
帶你看日本兩百年來如何重新認識世界、如何給自己定位
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向來被視為日本史的權威學者,他在這本書結合他於七十年代年在普吉得海灣大學(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的一系列“布朗與哈利講座”內容,為讀者了解200年以來日本對於自身、美國及西方世界的觀念轉變,建立起認識的基礎。
本書是詹遜教授的學術研究結晶之一,書中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個歷史人物為主線,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戰後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認識世界及給自己定位,透過人物講故事,從而帶出歷史的重要性。
本書特色
1 作者是日本史的西方研究權威,雖然關於日本人的世界觀的書籍已出版了不少,但此書仍是了解日本對於自身及世界的認識的入門必讀作品。
2 此書是作者七十年代大學演講稿的整理,並加進新的1995年版序言。書中把日本200年的世界觀濃縮在一本小書中,以三個歷史人物為主線,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戰後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認識世界及給自己定位,精簡易讀。
3 作者在書中闡釋日本人以等級論來把世界各國按地位和重要性來排列,透過不同年代人物的事業和觀點,探討等級排列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