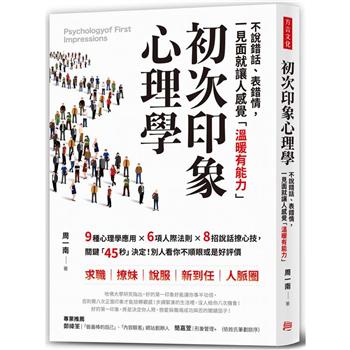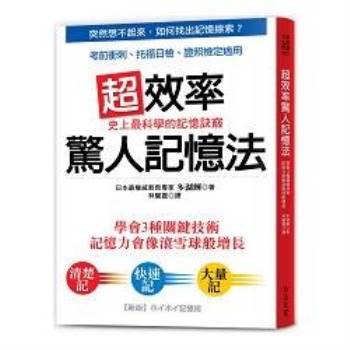有廁出租,價高者得﹗
鴉片戰爭後,絲綢重鎮順德與環球絲綢市場接軌,為了提升養蠶桑葉的質量,高價收購香港糞便作肥料,觸發華藉地產商在港擴建商業公廁,高價招租充當糞便收集站。商業公廁主導其時公廁服務,緩解以公帑及官地建政府公廁的壓力。
香港人口密集,興辦糞廁的難度甚高,地主每以臭氣擾人、物業價值受損而反對政府公廁,地產商建的「屎坑」卻持續服務半個世紀。究竟商人運用甚麼策略化解矛盾?政商在城市基礎建設中潛在甚麼張力?環球絲綢市場怎樣左右公廁服務?本書透過政商共謀公廁商品化,探討社會精英運用土地資源在管治上佔有重要角色,為殖民城市管治注入新形態。
本書特色:
1. 本書把公共廁所放大到社會歷史的大環境中去審視,透過社會的發展、人與人及社會的關係,揭示當中的經濟利益關係及土地分配,分析興建公共廁所的社會經濟因素。
2. 本書由作者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內容建基於歷史檔案資料,研究由2013年前已展開。本書內容將具真確性及歷史價值,值得研究香港歷史人士參考。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80 |
中國歷史 |
$ 316 |
Social Sciences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社會 |
$ 36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莊玉惜
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同時為香港文物保護師學會專業會員,主要從事城市管治、公共衛生、小販政策、客家社團等研究,並著有《街邊有檔報紙檔》及《香港棉紡世家:識變,應變和求變》等。
莊玉惜
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同時為香港文物保護師學會專業會員,主要從事城市管治、公共衛生、小販政策、客家社團等研究,並著有《街邊有檔報紙檔》及《香港棉紡世家:識變,應變和求變》等。
目錄
獻詞 / i
鳴謝 / ii
引言 政治經濟脈絡下的公廁 / 1
第一章 公廁商品化下的城市管治 / 13
三大疑問:衛生現代性、公共角色階級性、公廁服務持續性 / 15
政商互為依存模式的城市管治 / 37
第二章 土地資源壟斷和公共衛生 / 41
地產市場的擴張 / 43
華籍地產商在公共衛生管治的專屬位置 / 47
被商界綁架或不被綁架? / 55
總結 / 61
第三章 公廁供需和城市管治 / 65
城市公共衛生管治邏輯 / 67
華人--歐洲人健康命繫一線 / 72
殖民公廁:治理華人的「空間技術」 / 82
總結 / 87
第四章 商品化的公廁:集糞便收集站、物業項目和公廁於一體 / 93
以糞養廁 / 96
公廁選址的張力 / 104
地產項目:地產商投身公廁市場 / 110
重疊空間:道德空間和財富累積空間 / 117
總結 / 124
第五章 公廁景觀--地產霸權成就商業公廁 / 137
「勢力影響範圍」:解決公廁投訴的政治方法 / 138
相互緊扣的土地利益和權力 / 147
「勢力影響範圍」對政商關係的政治意義 / 161
總結 / 166
第六章 由政商利益同盟看殖民城市管治 / 179
由資源帶動的城市管治 / 182
沉默的共謀模式 / 187
城市管治下的政商張力 / 191
參考書目 / 203
附錄:縮寫一覽表 / 218
鳴謝 / ii
引言 政治經濟脈絡下的公廁 / 1
第一章 公廁商品化下的城市管治 / 13
三大疑問:衛生現代性、公共角色階級性、公廁服務持續性 / 15
政商互為依存模式的城市管治 / 37
第二章 土地資源壟斷和公共衛生 / 41
地產市場的擴張 / 43
華籍地產商在公共衛生管治的專屬位置 / 47
被商界綁架或不被綁架? / 55
總結 / 61
第三章 公廁供需和城市管治 / 65
城市公共衛生管治邏輯 / 67
華人--歐洲人健康命繫一線 / 72
殖民公廁:治理華人的「空間技術」 / 82
總結 / 87
第四章 商品化的公廁:集糞便收集站、物業項目和公廁於一體 / 93
以糞養廁 / 96
公廁選址的張力 / 104
地產項目:地產商投身公廁市場 / 110
重疊空間:道德空間和財富累積空間 / 117
總結 / 124
第五章 公廁景觀--地產霸權成就商業公廁 / 137
「勢力影響範圍」:解決公廁投訴的政治方法 / 138
相互緊扣的土地利益和權力 / 147
「勢力影響範圍」對政商關係的政治意義 / 161
總結 / 166
第六章 由政商利益同盟看殖民城市管治 / 179
由資源帶動的城市管治 / 182
沉默的共謀模式 / 187
城市管治下的政商張力 / 191
參考書目 / 203
附錄:縮寫一覽表 / 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