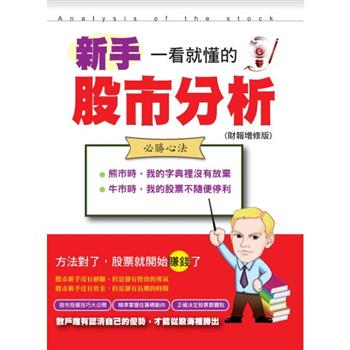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董培新畫說金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20 |
中文書 |
$ 1620 |
金庸武俠小說 |
$ 1620 |
武俠小說 |
$ 1620 |
圖文/插畫書 |
$ 1620 |
休閒生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獨家授權
畫說金庸十五部傳奇小說
新增訂版本 收錄從未出版新畫作
l 董先生憑着為金庸小說及其他文學小說繪圖而得名,在業界甚具名氣,他的畫作因為絕不重繪,所以現時大部分作品的真本已被收藏家購入,不予公開,十分珍貴。
l 本書與台版及內地版不同,重新挑選畫作,並增繪十多幅從未公開的新圖。
本書按小說區分章節及編排圖片,讀者更容易融入小說情節中。
作者簡介:
金庸
原名查良鏞,浙江海寧人,1924年生。曾任報社記者、編輯,電影公司編劇、導演等。1959年在香港創辦《明報》機構,出版報紙、雜誌及書籍,1993年退休。先後撰寫武俠小說15部,開創了中國當代文學新領域,廣受當代讀者歡迎,至今已蔚為全球華人的共同語言,並興起海內外金學研究風氣。
曾獲頒眾多榮銜,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英國政府O.B.E.勳銜及法國最高榮譽「藝術與文學高級騎士」勳章和「騎士勳位」榮譽勳章,劍橋大學、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澳洲墨爾本大學、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等校榮譽院士,北京大學、日本創價大學、臺北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蘇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校名譽教授,並任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文學院兼任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等公職。
其《金庸作品集》分由香港、廣州、臺灣、新加坡 / 馬來西亞四地出版,有英、法、意、希臘、日、韓、泰、越、印尼等多種譯文。
2018年10月30日於香港病逝,享年94歲。
董培新
1942年出生於廣西梧州,在廣州長大。15歲移居香港,同年隨嶺南派高峰弟子蔡大可當學徒,16歲開始以畫插圖為職業,19歲任香港仙鶴港聯電影公司美術主任,是香港早期的電影美術指導,20世紀70年代開始創作漫畫,作品有《波士周時威》、《鞋底秋與爛命倫》、《豪放女》等,高峰期擁有讀者達百萬,是當時香港知名的漫畫家及插畫家。
1958年至1999年間作畫無數,估計超過三十萬張,曾令他自詡:「一生人畫三世畫。」作品發表於香港大部份報章、雜誌,合作過的作家包括倪匡、亦舒、古龍、高陽、臥龍生、諸葛青雲等。1989
年移居加拿大溫哥華,1991年拜嶺南派楊善深為師,研習中國畫,以水墨淋漓潑寫胸中的俠氣豪情,其工筆亦有極為雅氣的格調。
2002年、2003年分別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大會堂舉辦個人畫展。2005年3月,在金庸先生的首肯與鼓勵下,開始金庸小說的國畫創作,並先後在廣州、澳門、香港、溫哥華舉辦「董培新繪金庸」畫展,又於2008年3月在臺北中山紀念館展出。2010年8月,參加成都、上海世博園舉辦的「加拿大著名畫家首次大型畫展」。2010年9月、2013年12月分別於杭州西湖博覽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董培新畫說金庸」畫展。2019年10月於香港尖沙咀海港城.美術館舉辦「俠客雄心.董培新作品展」。
——金庸
董培新先生對金庸小說嗜愛琢磨了幾十年,寢饋功深,了解深刻,創作動力充沛,積蓄既久,一經宣之於筆,自然不同凡響。
——陳萬雄(資深出版人、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前總裁)
董培新的畫作,無論是構圖、線條、神韻,都非常具水準。人物畫,絕不同於畫山水竹鳥,是需要百分之百的真實功夫。很高興現在有個董培新,繼續鑽研於中國水墨人物畫。
——蔡志忠(著名漫畫家)
武俠小說多「經典...
想像中的創作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我們家由廣西梧州遷返廣州居住,落腳地是西關,由三歲至十五歲這段成長期就是在這地方滋長。小時候工人帶着去理髮檔理髮,啊,理髮是開心的事,好多好多公仔書等着你睇,年紀小也不識幾個字,可是英雄人物卻背得滾瓜爛熟,甚麼張飛、關公、南俠展超、北俠歐陽春個個都如數家珍,小朋友間也有些玩物,就是有好多好多英雄人物的公仔紙,下課時男同學間會一起拍公仔紙,老師也不管你,一羣小嘩鬼會玩得不亦樂乎。在這同時喜歡了畫公仔,只是麻煩事來了;畫公仔畫得上癮,書頭、簿頭所有空白地方都畫得...
新版序想像中的創作(董培新)
推薦序一畫一世界,一畫一面貌(陳萬雄)
丹青妙筆繪金庸(陳萬雄)
偶像與同門師兄弟(蔡志忠)
好戲就在後頭(劉天賜)
也說董培新畫說金庸(謝春彥)
繪畫與電影分鏡頭(程小東)
出版說明
書劍恩仇錄
碧血劍
射鵰英雄傳
神鵰俠侶
雪山飛狐
飛狐外傳
白馬嘯西風
鴛鴦刀
倚天屠龍記
連城訣
天龍八部
俠客行
笑傲江湖
鹿鼎記
越女劍
創作過程
董培新創作大事記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