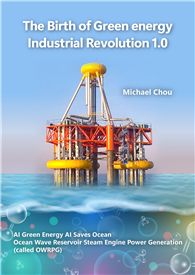新版序
細心的讀者如果看本書附錄的幾篇序言,就知道這部書原本是我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時,給大學生講“通識課程”時寫的講義。這部講義在1993年出了第一版(香港中華書局),2002年經過修訂,又出了第二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經過再次修訂補充之後,出版了第三版(北京中華書局)。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版,這次收入商務印書館的“葛兆光講義系列”時,我又做了一點兒修訂補充,主要是增加一些新資料和新發現。在每篇之後,增補了“文獻選讀”,而在“參考書目”中,也增加了一些新近出版可資參閱的著作。
一部面對大學生(尤其是非文科的大學生)的,應該說是通俗淺近的講義,居然能在差不多三十年裏始終受讀者歡迎,這讓我很吃驚。前不久還有一位讀者特意給我來信,說這本講義很“有用”,僅僅是“有用”這兩個字,就讓我很欣慰了。它還“有用”,就說明如今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還需要對傳統中國經典的閱讀,也還需要對“甚麼才是中國經典”這個問題的解釋,也還需要對“正確理解傳統經典意義”的引導。
關於這些問題,我想,我在2008年版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這裏就不再重複,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前,看一看那篇序言。
2008版序
近來常有一種風氣。有人說到“經”,便有意無意地把它等同“經典”,而提起“中國經典”,就急急忙忙把它轉換成“儒家經典”。我總覺得這種觀念有些偏狹。其實,中國經典絕不是儒家一家經典可以獨佔的,也應當包括其他經典,就像中國傳統絕不是“單數的”傳統,而應當是“複數的”傳統一樣。我一直建議,今天我們重新回看中國的經典和傳統,似乎應當超越單一的儒家學說,也應當關涉古代中國更多的知識、思想和信仰,這樣,一部介紹中國經典的書,就應當涵蓋和包容古代中國更廣泛的重要著作。
簡單地說有兩點:第一,中國經典應當包括佛教經典,也應當包括道教經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實在是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歐洲,以及東方的日、韓,在文化領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國的皇帝,不僅知道“王霸道雜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如宋孝宗、明太祖、清雍正皇帝),絕不只用一種武器。因此,回顧中國文化傳統的時候,僅僅關注儒家的思想和經典,恐怕是過於狹窄了。即使是僅僅說儒家,也包含了相當複雜的內容,比如有偏重“道德自覺”的孟子和偏重“禮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視社會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視心性理氣的新儒家。應當說,在古代中國,關注政治秩序和社會倫理的儒家,關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贖的佛教,關注生命永恆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別承擔着傳統中國的不同責任,共同構成中國複數的文化。第二,也許還不止是儒、道、佛,傳統中國有很多思想、知識和信仰,可能記載在其他著述裏面,“經典”不必限於聖賢、宗教和學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廣泛些?比如歷史學中的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通鑑》之類,是否可以進入經典?西方人從來就把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算成是必讀經典的。重建文化認同和進行傳統溯源,也從來少不了歷史著作,為甚麼不可以把它們叫做“經典”來重新閱讀?至於古代中國支持經典研讀(那算是“大學”)的基礎知識(也叫“小學”),就是文字之學,其中的那些重要著作,《爾雅》是早就成“經”了的,而《說文》呢,更是可以毫不愧疚地列入“經典”之林的。道理很簡單,古人早說過“通經由識字始”,不識字能讀經典嗎?甚至唐詩、宋詞、元曲裏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讓它們擁有“經典”的資格,莎士比亞那些曾被稱為粗鄙的北方人的劇作,不也列入了西方經典之林了嗎?因此,我在這部《中國經典十種》裏面,既選有傳統儒家的經典,也選了佛教、道教的經典,既有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說到經典,還必須補充說明,經典並非天然就是經典,它們都經歷了從普通著述變成神聖經典的過程,這在學術史上叫“經典化”。沒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經典的尺寸和樣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為它寫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覺得它充滿真理,又被反覆解釋,還有的被“欽定”為必讀書,於是,就在歷史中漸漸成了被尊崇和被仰視的經典。因此,如今我們重新閱讀經典,又需要把它放回歷史裏重新理解。所謂“放回歷史裏面”,就是說,這些經典需要先放在那個產生它的時代裏面,重新去理解。就比如《周易》,最初並不是那麼哲學和抽象的,在那個時代可能就是占筮;《史記》在那個文史不分的時代,不必那麼拘泥於歷史學的謹嚴,就是可以有想象和渲染。經典的價值和意義,也是層層積累的,對那些經典裏傳達的思想、原則甚至知識,未必需要亦步亦趨“照辦不走樣”,倒是要審時度勢“活學活用”,用一句理論的話講,就是要“創造性的轉化”。
這部書原來是我在大學裏講通識課程的講義,在理想中,大學應當是理解文化傳統和提倡精神自由的島嶼,閱讀經典也許正是實踐這一理想的重要途徑。布魯姆(Allan Bloom,1930—1992年)在《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曾說,閱讀經典可以使人們了解,從古至今“人類究竟面臨哪些重大問題”,以便人們在共同問題和豐富知識基礎上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聯繫”。不過,這並不意味着聖賢原則是必須遵循的教條,也不意味着古代經典是不可違逆的聖經,畢竟歷史已經翻過了幾千年。因此,對於古代經典,既不必因為它承負着傳統而視其為累贅包袱,也不必因為它象徵着傳統而視其為金科玉律。我對經典的看法很簡單:第一,經典在中國是和我們的文化傳統緊緊相隨的巨大影子,你以為扔開了它,其實在社會風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傳裏面,它總會“借尸還魂”;第二,歷史上的經典只是一個巨大的資源庫,你不打開它,資源不會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會現實和生活環境,是刺激經典知識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經典中的甚麼資源被重新發掘出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背景”召喚甚麼樣的“歷史記憶”;第三,經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釋”的,不大可能純之又純、原汁原味,以為我們今天可以重新捫摸聖賢之心,可以隔千載而不走樣,那是“原教旨”的想象;第四,只有經過解釋和引申,“舊經典”才能成為在今天我們的生活世界中繼續起作用的,呈現出與其他民族不同風格的“新經典”。
我也希望我所詮釋的“舊經典”,能夠成為今天生活中起作用的“新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