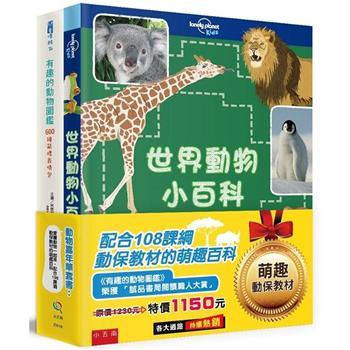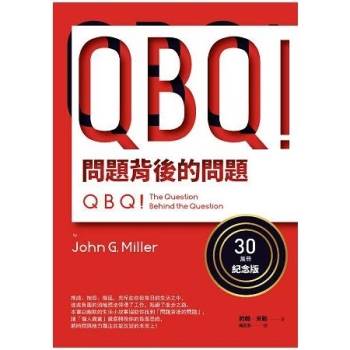梳理中國外交發展史
探索世界秩序重構下的外交政策方向
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並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議,必須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客觀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
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作者希望透過本書,讓讀者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出答案。
本書着重分析世界秩序的歷史與轉變,藉由中國在前現代時期至今在外交上的變化,重點探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着自身條件和世界發展進程之下外交方針的走向。
以歷史角度探討世界秩序與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特別提出幾位國家領導人的外交方針,可從中了解中國各個時期在世界舞台上如何適應及融入,甚至主導世界秩序這一轉變。
本書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世界秩序下的中國外交:歷史分析與轉變過程 (電子書)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世界秩序下的中國外交:歷史分析與轉變過程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郭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郭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目錄
序言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第一章 世界體系、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國家實力的物質基礎
第二章 國際社會、國際道義與國家軟實力
第二部分:中國與世界秩序
第三章 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外交:天下秩序與朝貢體系
第四章 清末外交:天下秩序的衰亡(1840—1911年)
第五章 民國外交:中國外交現代化的起點(1912—1949年)
第六章 共和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到國際社會(1950年至今)
第三部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交:1978—2020
第七章 鄧小平外交:告別革命,「韜光養晦」
第八章 江澤民外交:深化改革,加入世貿
第九章 胡錦濤外交:從「和諧世界」到「有所作為」
第十章 習近平外交:從「有所作為」到「奮發有為」
第十一章:中國外交的進路
後記: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嗎?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第一章 世界體系、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國家實力的物質基礎
第二章 國際社會、國際道義與國家軟實力
第二部分:中國與世界秩序
第三章 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外交:天下秩序與朝貢體系
第四章 清末外交:天下秩序的衰亡(1840—1911年)
第五章 民國外交:中國外交現代化的起點(1912—1949年)
第六章 共和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到國際社會(1950年至今)
第三部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交:1978—2020
第七章 鄧小平外交:告別革命,「韜光養晦」
第八章 江澤民外交:深化改革,加入世貿
第九章 胡錦濤外交:從「和諧世界」到「有所作為」
第十章 習近平外交:從「有所作為」到「奮發有為」
第十一章:中國外交的進路
後記: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嗎?
序
序言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世界秩序卻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產物。兩者如何兼容?或者說,中國如何持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塑造時,減少與其主導者,即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衝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高層和國際關係學者在近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課題。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恰恰是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秩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
關於這一話題的思考,最早湧現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2001年加入世貿,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秩序的全面對接。此後,中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率。西方的學者和分析人士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學術興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中被上訴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決自身的領土完整問題。特別是在台灣問題和貿易問題上,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始終齟齬不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世界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系統性經濟危機;但與此同時,中國以相對穩健的姿態渡過了這場危機。此後,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有識者都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發展模式。歷史並沒有終結。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圍繞中國與美國,進入新一輪的權力轉移階段。中國很難取代美國的地位,但世界秩序發生形變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出了「亞太再平衡」。這裏指的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平衡中國,而是說,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進行博弈與交鋒。
毛澤東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打」,即生存問題;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餓」,即發展問題;在胡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時期,中國面臨的是「不挨罵」,即如何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中國之於整個國際體系的分量從未如此重大。或者說,中國如今在外交上面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如何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如今這個國際關係學庸俗化的時代。在中國當前的思想市場裏,有關中國外交方向的爭論主要被兩種聲音佔據: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論證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中國必勝主義」,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必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勝出,原因不外乎是中國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以及(或者)體制優勢;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勢,必然導致其走向衰敗。這一類「研究」基本不顧事實和邏輯:它們總是預先設定了中國必勝的結果,再尋找證據,由此推出中國「戰勝」美國的必然性。庸俗現實主義派的論說也非常廣為流傳。他們把國際關係中佔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幾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國外交面臨的種種危機上,並推導出「中美必然衝突」這一結論。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庸俗之處在於,他們既不建構理論前提(如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性),也不對「中國外交關係如何發展至今」的問題作實證分析,更沒有提出思考和把握中國外交的總體框架。這種思考方法是危險的。它用一個看似有效的學術概念掩蓋了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現實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人不再基於事實去判斷、分析國際形勢。國際關係的研判變成了對「陰謀論」的揣測,而且揣測得越危言聳聽,越多人贊同。
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中國中心主義」,都很善於操縱公眾的情緒:論證派滿足了非理性民主主義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現實主義派則操弄了人類對未知和外部威脅的恐懼感。隨着外交議題在社交媒體上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娛樂化、庸俗化,中國外交逐漸成為了一個人人都在熱議、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話題。
本書希望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本書希望表達的中心理念是: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並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議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去客觀地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這麼做有助於規避了從中國看世界秩序的智識錯誤,即「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中國中心主義」不僅是知識界、輿論界常犯的智識錯誤,也導致中國在過去無法與世界秩序接軌、發展一度停滯。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歷史上,中國在過去曾兩次錯過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首先,在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卻以天朝自居,主動閉關鎖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期是全球分工體系初步形成的階段,所有參與了這一進程的歐洲國家都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其次,在革命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閉關鎖國,錯過了電器時代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世界進入「超級全球化」,國際分工出現了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的轉移,中國恰好是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才獲得了令人驚嘆的經濟和民生成就。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發展固然離不開自身努力,但更是參與世界秩序的結果。但種種迹象表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已不再如鄧小平時期那樣和諧。一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了「波蘭尼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組織造成了嚴重腐蝕。另一方面,隨着世界即將迎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和5G等科技為標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各國都在為下一個發展風口作競爭準備,而矛頭紛紛指向中國。科技是決定國家發展高度的關鍵要素,但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科技「冷戰」恐怕已經打響。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等國家開始對中國展開了科技競爭乃至封鎖,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對華科技競爭上升為美國國策。日本、歐盟也開始就價值鏈安全和科技安全議題對華警惕。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歷史考驗。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中國都很難脫離世界談封閉式的自主創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漸失穩。當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其基本特徵是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觀底色,構建民主國家範圍內的集體安全,注重以多邊對話機制解決國際衝突,以及鼓勵全球自由貿易。這一秩序也被國際關係學者和外交界看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圍繞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建立了一系列包括聯合國、北約、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深深地嵌入了美國領導建立的體系之中,成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
然而,美國現在卻越來越有放棄領導世界秩序、退回孤立主義的傾向。美國在特朗普主政期間,曾把中國和俄羅斯標籤為「修正主義國家」,即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家。但令人費解的是,對當前世界秩序不滿的不是中國,而恰恰是美國。美國一直對世界貿易組織不滿,希望「另起爐灶」,建立另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組織。繞開聯合國對外發動戰爭,對美國而言已是慣常做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譴責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並不是該公約的簽約國。
一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國家,承擔了維護世界秩序、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但對美國來說,維護世界秩序的成本越來越高,收益卻越來越低。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秩序方面做得越來越多。中國一直以來都強調聯合國的合法性,強調在疫情問題上尊重世衛組織的科學權威,同時也通過「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與中國的國家利益是高度重合的。中國也因此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這種狀況引發了一個悖論:一方面,領導世界秩序的守成國希望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崛起國卻希望保持現狀。這種狀況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基辛格曾說,西方人在談論中國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國際系統,既允許中國永久參與,又不被中國主導?同理,中國在外交上面臨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回答這一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書也無意對此下定論。我們希望做的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文章的同時,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出自己的答案。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世界秩序卻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產物。兩者如何兼容?或者說,中國如何持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塑造時,減少與其主導者,即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衝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高層和國際關係學者在近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課題。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恰恰是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秩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
關於這一話題的思考,最早湧現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2001年加入世貿,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秩序的全面對接。此後,中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率。西方的學者和分析人士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學術興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中被上訴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決自身的領土完整問題。特別是在台灣問題和貿易問題上,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始終齟齬不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世界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系統性經濟危機;但與此同時,中國以相對穩健的姿態渡過了這場危機。此後,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有識者都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發展模式。歷史並沒有終結。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圍繞中國與美國,進入新一輪的權力轉移階段。中國很難取代美國的地位,但世界秩序發生形變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出了「亞太再平衡」。這裏指的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平衡中國,而是說,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進行博弈與交鋒。
毛澤東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打」,即生存問題;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餓」,即發展問題;在胡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時期,中國面臨的是「不挨罵」,即如何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中國之於整個國際體系的分量從未如此重大。或者說,中國如今在外交上面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如何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如今這個國際關係學庸俗化的時代。在中國當前的思想市場裏,有關中國外交方向的爭論主要被兩種聲音佔據: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論證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中國必勝主義」,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必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勝出,原因不外乎是中國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以及(或者)體制優勢;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勢,必然導致其走向衰敗。這一類「研究」基本不顧事實和邏輯:它們總是預先設定了中國必勝的結果,再尋找證據,由此推出中國「戰勝」美國的必然性。庸俗現實主義派的論說也非常廣為流傳。他們把國際關係中佔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幾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國外交面臨的種種危機上,並推導出「中美必然衝突」這一結論。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庸俗之處在於,他們既不建構理論前提(如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性),也不對「中國外交關係如何發展至今」的問題作實證分析,更沒有提出思考和把握中國外交的總體框架。這種思考方法是危險的。它用一個看似有效的學術概念掩蓋了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現實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人不再基於事實去判斷、分析國際形勢。國際關係的研判變成了對「陰謀論」的揣測,而且揣測得越危言聳聽,越多人贊同。
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中國中心主義」,都很善於操縱公眾的情緒:論證派滿足了非理性民主主義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現實主義派則操弄了人類對未知和外部威脅的恐懼感。隨着外交議題在社交媒體上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娛樂化、庸俗化,中國外交逐漸成為了一個人人都在熱議、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話題。
本書希望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本書希望表達的中心理念是: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並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議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去客觀地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這麼做有助於規避了從中國看世界秩序的智識錯誤,即「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中國中心主義」不僅是知識界、輿論界常犯的智識錯誤,也導致中國在過去無法與世界秩序接軌、發展一度停滯。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歷史上,中國在過去曾兩次錯過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首先,在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卻以天朝自居,主動閉關鎖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期是全球分工體系初步形成的階段,所有參與了這一進程的歐洲國家都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其次,在革命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閉關鎖國,錯過了電器時代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世界進入「超級全球化」,國際分工出現了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的轉移,中國恰好是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才獲得了令人驚嘆的經濟和民生成就。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發展固然離不開自身努力,但更是參與世界秩序的結果。但種種迹象表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已不再如鄧小平時期那樣和諧。一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了「波蘭尼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組織造成了嚴重腐蝕。另一方面,隨着世界即將迎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和5G等科技為標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各國都在為下一個發展風口作競爭準備,而矛頭紛紛指向中國。科技是決定國家發展高度的關鍵要素,但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科技「冷戰」恐怕已經打響。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等國家開始對中國展開了科技競爭乃至封鎖,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對華科技競爭上升為美國國策。日本、歐盟也開始就價值鏈安全和科技安全議題對華警惕。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歷史考驗。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中國都很難脫離世界談封閉式的自主創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漸失穩。當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其基本特徵是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觀底色,構建民主國家範圍內的集體安全,注重以多邊對話機制解決國際衝突,以及鼓勵全球自由貿易。這一秩序也被國際關係學者和外交界看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圍繞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建立了一系列包括聯合國、北約、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深深地嵌入了美國領導建立的體系之中,成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
然而,美國現在卻越來越有放棄領導世界秩序、退回孤立主義的傾向。美國在特朗普主政期間,曾把中國和俄羅斯標籤為「修正主義國家」,即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家。但令人費解的是,對當前世界秩序不滿的不是中國,而恰恰是美國。美國一直對世界貿易組織不滿,希望「另起爐灶」,建立另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組織。繞開聯合國對外發動戰爭,對美國而言已是慣常做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譴責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並不是該公約的簽約國。
一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國家,承擔了維護世界秩序、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但對美國來說,維護世界秩序的成本越來越高,收益卻越來越低。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秩序方面做得越來越多。中國一直以來都強調聯合國的合法性,強調在疫情問題上尊重世衛組織的科學權威,同時也通過「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與中國的國家利益是高度重合的。中國也因此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這種狀況引發了一個悖論:一方面,領導世界秩序的守成國希望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崛起國卻希望保持現狀。這種狀況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基辛格曾說,西方人在談論中國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國際系統,既允許中國永久參與,又不被中國主導?同理,中國在外交上面臨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回答這一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書也無意對此下定論。我們希望做的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文章的同時,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出自己的答案。
|